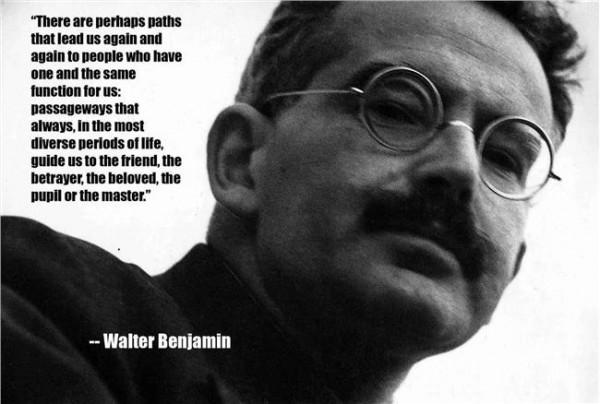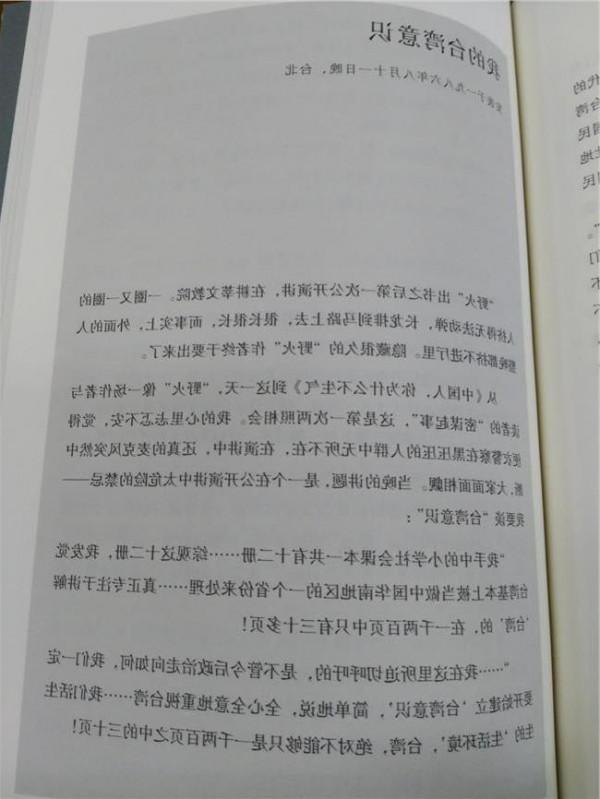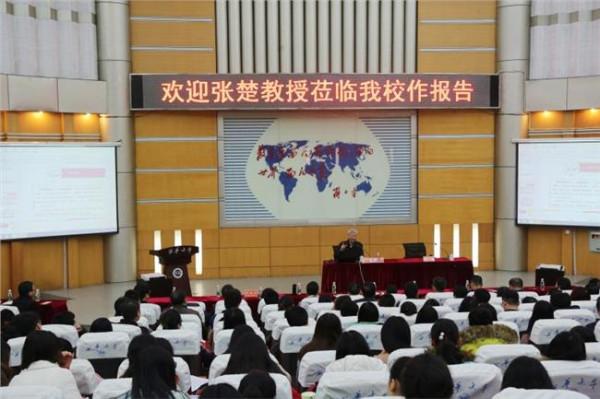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是中国大陆继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之后,第二部以抗争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关于抗争政治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大陆既是一门可以争取到来自国内国外的项目经费的显学;同时又是一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和风险度的险学。既没有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阴阳气场研读明白,也没有把底层社会的草根民众的抗争政治解释到位的应星,一再针对于建嵘的挑战论争,既有同行竞争的显学心理在膨胀;更有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避险心理在发酵。
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一书的导论和第一章中介绍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各种利益诉求日趋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农村社会日益增长的土地抗争和工人阶级的维权行动,还是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频繁发生,大都是出于利益博弈,涉及到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体制的政治诉求。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家大多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足。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性政治活动掩盖起来,或者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
应星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正文之前的“鸣谢”中,另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由于所选取的角度的敏感性,我从收集材料到研究写作再到出版发行,都困难重重。应该说,直面如此严峻而棘手的问题,是需要勇气的。然而,仅仅具有勇气是不够的。有的时候,这种勇气也可能沦落为伪神的煽动、韦伯所谓‘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甚或另一种政治投机。”从全书的行文中可以看出,被应星指认为“伪神的煽动”和“另一种政治投机”的主要目标对象,是比他更加著名的学术同行于建嵘。
在该书导言中,应星自称“本书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目的是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种时弊。其一是“不加反思地把从研究西方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方法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移植派”;其二是“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田野调查,而后根据自己随性的灵感和对中西方理论的凌乱读解来匆匆炮制自己的新概念”的“经验派”。但是,细读该书之后,笔者并没有体验到具体可感并且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场;反而在针对于建嵘的一再挑战中,明显感受到作者在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中疲软畏缩的气场迷失。也就是于建嵘所说的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应星所谓“经验派”的主要目标对象,依然是“炮制”出“以法抗争”、“刚性稳定”之类“新概念”的于建嵘。
被应星称之为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的“气”,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初概念。在老子《道德经》的创世学说中,是道产生了一,也就是原始混沌之气。一产生了二,也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的阴阳二气。由二产生的三,指的是天地阴阳的交配和合之气。“三生万物”,指的是由天地阴阳孕育出的以男主阳、以女主阴、以人为大的万事万物。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儒学,继老子、孔子、孟子、董仲舒之后,进一步抽象概括出了充分吸纳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或者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
在该书第二章中,应星先是承认“气在中国社会的指涉极其繁杂,我在此无法详加辨析”;接下来,他通过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仅仅“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就作为学术灵丹匆匆得出连最为基本的阴阳二气都没有加以区别的“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的气场“续谱”,显然是比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文化的阴阳气场更加抽象空洞、自我矮化的气场迷失。
2004年,于建嵘在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第2期的《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中,第一次提出“以法抗争”的解释性框架。在他看来,“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
他所依据的一部分的实证案例,是笔者于2004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俞梅荪与中国新民权运动》一书中,翔实叙述的四川省自贡市白果村七组失地农民刘正有,代表村民依法维权反受其害的政治觉醒与持续抗争;河北唐山、秦皇岛二市两万多名桃林口水库移民,分别签名要求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政治诉求;福建省福州市和宁德市的失地农民,分别发起万人签名罢免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政治动议。该书第312页引用有于建嵘在唐山市移民代表张友仁与曾任中南海秘书的法律学者俞梅荪四处逃亡的关键时刻,发给笔者的声援邮件:“来信收到了,我完全站在民主和民众一边。你们的信我已转给了有关人士,也许有可能有所作用。”
对于这些并不罕见的抗争案例漠不关心、避而不谈的应星,直到七年之后还在书中依据自己在田野考察中深入研究过的少数案例,削足适履、以偏概全地坚持认为,于建嵘“过分夸大了1990年代以后的这些变化”。在他看来,“草根动员尽管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但这种组织性是名实分离的,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它在进行有限动员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控制着群体行动的限度特别是政治的敏感性和法律的界限。”
从中国传统的阴阳气场的角度来看,于建嵘所说的“以法抗争”,其实就是底层社会的草根民众政治正确或者说是政治挂帅的“存天理,灭人欲”、“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负气抗争。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卡车活活碾死,从而激发唤醒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气势磅礴的公民维权和政治抗争。钱云会案连同笔者的前述案例,足以证明应星极力强调农民维权抗争的“去政治性”,其实是他自己因为缺乏足够勇气,而对于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非法治、泛政治的斗争哲学和政治抗争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气场迷失。应星针对于建嵘一再发起的挑战论争,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