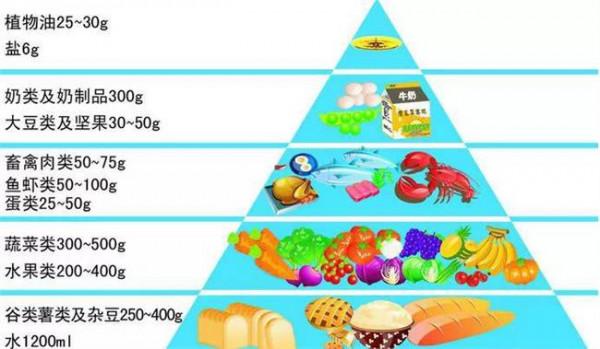入选“国医大师” 一“脉”相承李士懋(图)
在全国第二届“国医大师”评选中,李士懋成功入选。由于全国首届“国医大师”未有河北中医入选,公示期一结束,记者便怀着极大的好奇与景仰前去采访。
不料,初见李老,却颇多让人意外之处。
一未料到,老先生姿态之谦。“国医大师”的评选公示已然结束,记者对李老表示祝贺。李老却说:“既然还未授予,就还不是,况且若我最终未得到这个称号,你们岂不白费。”他自谦“小民而已”。
二未料到,老先生待客之周。进门尚未落座,老先生便招呼学生上茶、端水果。初谈作别,未到午时,他便招手相邀,执意要记者留下吃饭。
三未料到,老先生谈兴之高。本想让他浅介学术心得,但李老却认真地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讲起脉诊。记者听得如坠五里云雾,乃至抱着李老所赠专著出门时,仍心下惶惶,大感惭愧。
好在李老的学生众多,从大学教授、在校学生到中医爱好者,有许多人可以请教并“爆料”。于是一路寻访下来,自称“小民”的李老,在记者眼中已然是“国医大师”风范了。
李士懋,1936年生人,籍贯山东。北京中医学院(今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在大庆油田总医院从医十七载,1979年到河北中医学院任教直至退休。
6月30日,全国第二届“国医大师”拟表彰人选开始为期5天的公示。在公示的30人名单中,今年78岁的李老先生是河北唯一入选者。
省会新石南路一个临街的小中医诊所内,周飞升抱着孩子坐到李士懋对面。
今年5月9日,《燕赵都市报》刊登了一则题为《跨越半个中国的救助》的新闻报道,讲的是5月7日,一名广东人如何将命悬一线患有急性病毒性脑炎的幼子,从当地医院ICU转到石家庄就诊的事。而在交待这次大转诊的原因时,只说在石家庄找到了一名中医专家。其实,这名专家就是李士懋。
“我以前曾在石家庄学过西医临床。孩子发病后在广东当地医院ICU抢救了18天,我都绝望了。后来想起了李老师。”周飞升说,“我向李老求助后,他让在广州的一个徒弟先来诊治,用中药缓解了症状。我看到了希望,他的学生建议我来石家庄,于是就下决心过来了。”周飞升说,孩子5月7日晚住进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医院方面也是李老提前协调好的。
“5月10日请了李老来会诊,会诊完我送李老回家,出门正赶上下雨,等不到出租车。李老走在我前面,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水里,身上都淋湿了。”周飞升回忆说。
5月23日,周飞升带着病情好转的孩子来到诊所。李老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住院费用太高,准备先出院,再接着给孩子治病。“等我到柜台抓药的时候,他从诊室里出来,说你留个电话,我给你找个房子租吧。第二天就给我找到了,就在李老师住的小区。”
“后来李老师又说,你家里负担重,我给你一点钱,当场给了我一笔钱。你别问多少,我说是一笔你就明白了。我要给李老写借条,被训斥了一番。当时我哭了,旁边的护士也哭了。在诊所挂李老的号,他把我的挂号费都退了。”
周飞升说,等孩子彻底康复了,就让他学中医。
拿这事儿向李士懋先生的学生王四平教授求证。王教授说,是啊,老先生为患者垫钱,借给患者钱的事儿常有。王教授是河北中医学院教授,也是李士懋名医传承工作室的主任。
像周飞升一样,因为患有疑难杂症找李士懋诊治的人很多。逢他坐诊的日子,早晨6时就有人到诊所门口来排队。
这一天从上午8时到11时45分,李士懋先生一直坐在诊室为病人切脉开方。若不是下午赶火车去北京开会,他一般都会坐诊到下午一两点钟。看到时间紧,王四平嘱咐诊所莫再放号。这时候已经放了65个号,平时要到七八十号。
其间有重病患者乘车而来,他就出来到车上去看。一个学员说,老先生看病有个原则,病人不能动的他去,病人能来的他等。
李老的诊室墙上挂有一幅字,写的是“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此言出自明末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喻昌。
能体谅病人之苦,也才能视人犹己。李士懋先生对此体会尤甚。
李老的次子年幼时由于脑血管畸形且继发癫痫、智力障碍和功能障碍,生活难以自理。李老夫妇便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地照料。有时屎尿拉在裤子里、被子里,夫妻俩就耐心地清洗。遇上癫痫大发作、发烧,就整夜整日地陪着。
他们照顾、治疗这个不幸的儿子长达三十多年。其间苦痛,非旁人所知。李老将自家书房称作相濡斋,既表夫妻恩爱之
情,也说明了二老执手所度的艰辛与风雨。
田淑霄教授去年6月去世。时至今日,李老的学生还提醒外人,莫在老先生面前提田老师,因每有提及,他便面生悲色,伤心叹息。
独创“三段法”传承 带徒有教无类
李老坐诊,诊断的流程与常规不同。
就医者先从第二、第三诊室开始,各坐诊医生也是李老所带的高徒和学员。他们诊脉开方后,便相继汇集到第一诊室的李老处,等李老再逐一将病人诊断一番,在既开的方子上勾勾画画,作出评语。有添有减,有批有改,李老定方后,病人才可抓药。
而李老批改药方时,或坐或站在他身旁的学徒们,不时见缝插针给病人切脉,再诊断一番。
在大多数方子上,李老看后先用红笔写下一个“可”字,再行批改。跟随李老学习的河北中医学院大四学生小张,也坐在李老诊桌旁。
这个唐山姑娘说,她也常拿出方子给李老评,最高兴的是被评为“佳”,感觉胜过吃大餐。但也有失败的时候,李老曾给她的方子批过三个字——“老鼠屎”。今天说起,已成谈笑,但当时除了尴尬,她还体会到了先生对学员要求之严,用心良苦。
这种批改药方的带徒方法是李老设计的,被他称为“三段教学法”。
业内外皆知,中医传承是一大难题。过去传统的办法是跟师抄方学徒三年,至于徒弟能从抄方中学得多少,一则看老师是否乐于点化,二要看学徒自己是否留心上进。李老改进跟师抄方之法,采取了启发式传承,大致说来分三段进行。
第一阶段便是跟师诊治,大约一年,熟悉老师诊治的基本方法。第二阶段变为独立诊治,除了老师批改病例药方给学生打分外,另还有病人给老师打分。第三阶段是学员互为师傅,互改诊治方案,最后老师定评,指出对错。
李老是国家二、三、四、五批高徒导师,国家名医工作室传承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导师,也是多名国优、省优人才指导老师,不但是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指导老师,还带一批社会学员。有的是初涉岐黄、大学没毕业的新手,有的只是酷爱中医的爱好者,可谓有教无类。
但即便对社会学员,李老一样要求严格。每隔两三个月,便会按照中医系统教学之法,拿题考他们。从经典中医著述到药理,无一遗漏。
有学生告诉记者,原来老先生只在每周的周一、周五坐诊,但是看到这些学员奔波辛苦,遂加了周六一次。而且,李老每周五晚还要为他们讲课,内容涉及脉学、伤寒论、温病学、汗发等多个领域。
谈起“三段教学法”,李老说这也称得上是“PBL”教学法了,“这才抓住了中医传承的‘牛鼻子’,是一条捷径。”这个洋名词来自Problem-Based learning,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译为基于问题的学习。
一段故事,也可见老先生的传承风格。
曾有一名学生,毕业后对中医前途心灰意冷,几欲放弃。朋友提醒需找高人指点,他便慕名前来。见面前,该生适逢重感冒,自己便开了个几十味药的方子,拿去给老先生看,实则想考考老先生是否真的“高人”。李老先生诊脉后,将方子上的药大多划去,只留下七味并调整剂量。他当即抓药煎服,发汗后烧退身爽,十分敬服,坚定了跟师的念头。于是每逢李老坐诊讲课,他都尾随其后。
一年多后,老先生聚徒评方,让大家对同一病人开出自己的方子来,递与他评判。老先生一一看过药方,或摇头,或沉思。后李老又问,还有无方子可看。该学员伸臂大喊:“还有我的。”李老接过一看,当场便说:“快过来坐在凳子上。”
采访中,李老也不无得意地告诉记者,现在就有学员虽只是大四学生,已经快成了诊治开方“免签户”了。
李老鼓励学生发表论文,探究学术。但对写作质量要求极高,甚至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会被他批评。他说:“这些都是要给后人看的,不能错。”对于学生或徒弟开出的药方,他修改起来也是一丝不苟。一味药是用9克还是10克,他都要讲明原因提出解释。他说,用药要因人、因时而异。
“莫道今秋教学忙,明年桃李竞芬芳”。这是去年教师节,李老自写的一副对联,字里行间透着自豪。
看官方介绍李老学术的材料,都说其精妙处在于脉诊学。可中医学中的“脉”,在一般人眼里则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玄异之感。
至于为何对脉学青睐有加,李老自能从经典医学典籍中给出很多解释来。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到《脉经》、《脉诀》、《濒湖脉学》等等,加之从业恩师也多尊崇脉学,一“脉”相承,不难理解。
王四平教授则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李老师的指肚比常人宽厚,用于诊脉有先天优势,接触面大,血管神经丰富,感受到的脉象也就更准确。记者留神去看,果然与常人不同。只是抽烟过多,熏得有些黄。
老先生毫不讳言自己要扛起“脉诊”的大旗。而他也沉浸于脉学之海,陶醉其间。
至于他的脉学之见,又有哪些不同,不妨先从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也就是所谓的四诊说起。
看似平常的四字背后,却有着一番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四诊的顺序说明了其在诊断中的主次地位。但李士懋认为,“望闻问切”是四诊在诊断过程中运用的顺序,而不是重要性的先后排列,继而提出“脉诊在辨证论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甚至将脉诊提高到在四诊中占据五成到九成的重要位置。
与其说这是一种创新,更不如说是一种对传统中医的回溯和坚守。这种坚守中,令皓首穷经的他每有所得,便欣悦异常。
但李老说,他重视脉诊,并不意味着夸大脉诊的作用。对一诊脉便知病情解生死的大夫,他羡慕不已,也曾扮作患者去偷艺。但他发现,这些大夫也多是说了许多症状,其中有一二症状包含其中而已,难以直指病人疾苦。他还说,脉诊的运用,要在望、闻、问的基础上,若舍三诊只凭一诊,无异盲人瞎马。
李老类似的探索和见解还有很多。比如针对西医治疗对脉象的影响,他提出要引起注意,以免误诊、误治。他在自己的著述中附上年轻时受此影响而误诊的病案。心胸之磊落,令人钦佩。
李老说:“自古论脉详且尽矣,本不容吾等无名之辈置喙。但在50余年不断学习、实践中,萌生了些有别于传统的见解,故而斗胆写了出来。”他的多部著述,都是脉学话题。
与李老学术所长相比,其从学为医的经历倒好说多了。
他是原北京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师承秦伯未、任应秋、刘渡舟、赵绍琴、胡希恕、余无言、陈慎吾等老中医。“他们虽没什么学历,也是从全国各地调到北京的,但都是大家。”提及诸位恩师,李老至今崇敬十分。
“开始并无学医的意愿,毕竟高中时学的都是数理化。”李老说,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国家政法系统的干部,他高中上的是高干子弟甚多的北京101中学,1956年中学毕业“秉父命”考取北京中医学院。
父亲让他学中医,是因为家人多受过中医之惠。而且他对中医产生兴趣,也是亲见实例后被折服的。他说,母亲患高血压,当时北京老中医余冠吾先生重用蜈蚣,四服药就好了,且血压几十年稳定。
说起蜈蚣,李老还提到一段轶事。原北大文学教授余伯龄,乃余冠吾之兄,于日寇侵占北京后辞职闭门研医,人称余疯子,因在药方中曾用百条以上蜈蚣而得名。
李老也有其“疯”的一面。他曾以蜈蚣10条为粉,一次吞服,未见有毒性反应。后来,他甚至以1:5蜈蚣液静点,以身试药,连续三日,分别为30、60、100毫升,无任何毒性反应。后来李老用药,也曾有过四五十条蜈蚣的实例。有人说,李士懋胆够大。
如此胆魄之人,面对长期以来中医所临境况,却有些无奈和纠结。
李老坦承,给他带来困惑的是中西医结合。他认为,50多年实践下来,二者结合得如何姑且不论,中医失去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倒是实情。
“症结在于,原则上高喊继承发扬中医特色,但实际干起来仍是以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改造中医那一套。喊的与干的两张皮,岂不哀哉。”李老说,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根本看不到中医特色。
“至于动物实验,必须造病理模型,中医治疗是以证为核心,证的判断须望闻问切,一个老鼠满脸毛,如何望?小爪子就那么一点,如何切?吱吱乱叫,如何问?脱离了四诊,哪来的证?”李老的话令人捧腹,也透着无奈。
他说,若不按这个模式去做,莫说学位、职称、获奖等,恐怕连个论文也发表不了。“这好比旧社会妇女裹足,怕脚大了丑煞人,连个婆家也找不上,只能把好端端的脚裹成残废。”
于是为了科研立项、授艺带徒、评聘职称等世俗之事,李老自嘲自己也不得不进行“裹脚”。年近退休,他重拾外语,苦学西医基础和科研方法学,求助西医老师去做种种实验分析。李老说自己真是“大感郁闷,心神俱疲”。几经折腾,李老发现,自己的优势还是在中医,与其迎合“潮流”,莫若坚持自己。
科学是多元的,发展道路也应是多元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中曾说:“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此言道出了二者根本不同之所在。
回归传统中医的李老,自谓铁杆中医,意为尊崇传统经典,不被西化乃至异化。
这才是他所熟悉的世界,充满阴阳和气血,追求天人合一,平衡中正。
这是他毕生追索的方向——溯本求源,平脉辨证。
虽年近八旬,可现在李老仍每天早晨四时左右起床,苦读经典,参悟辨证之道。他说,以古为师,努力领悟;以古为友,平等探讨;以古为徒,敢于评说;以古为敌,勇于否定,建立自己的见解。
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伴驾鹤西去后,他一人独住,拒绝后辈照料,只为清静读书、写作。他说,把一生窃有所悟处写出来,既是对中医的情缘,亦免死而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