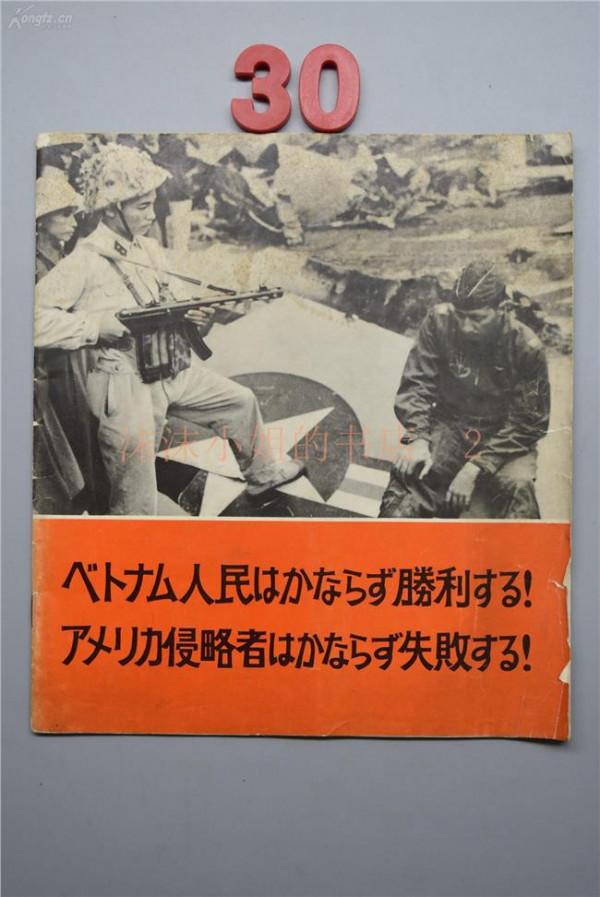毛泽东告诫侄子:不学胡志明 任何时候不下罪己诏
其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封无一例外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制度维系着。这种制度的实质就在于一党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垄断着全国的政权,党内又实行民主集中制,以集中统一全党的意志,领袖群体尤其是最高领袖拥有着绝对的权力。
一旦这种权力机制没有了,共产党的政权也就难以维系了。最高领袖要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还要实行个人崇拜,不断地神化最高领袖。
当党内存在权力较量和政见分歧,最高领袖的权力还不巩固的时候,这时候他就需要通过权力斗争,要别人做出检讨,以统一全党意志,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进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而最高领袖本人是不能做出检讨的,因为他是最高的权威和真理的化身,一旦认错就不利于巩固他的权力,就有损于他的形象。
其实在这种体制中,政治人物的利益都是紧密相联的,呈现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不但毛泽东本人要极力维护这种权力格局,就是其他领导人也要自觉地维护这种权力格局。1961年12月21日,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有100余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传达了毛泽东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毛泽东显然也原则谈到他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
但邓没有在这个场合传达毛泽东的这一看法。邓之所以没有传达,也许是惧于毛泽东的独裁,他想明哲保身,但笔者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出于他很强的党性:他要维护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要维护毛的个人权威。这我们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可以看出来。
1957年毛号召党外人士进行帮助党进行整风时,邓等人的态度就显行十分抵制。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引蛇出洞,进行“反右”时,邓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执行者。1979年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运动期间,社会的民主化运动开始升温,邓为了不让这股潮流发展下去,进而危及到中共的一党专政,就及时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很快就把西单“民主墙”取缔了,把这场运动压了下去。
在1989年的那场巨大的民主运动中,邓更是动用了几十万军队,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把它镇压下去,从而保住中共一党专政的地位。
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他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然而,中国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古代帝王很多,但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都“亡国”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给的,具有神圣性,但同时皇帝又必须“以德配天”,如果他荒淫无道、实行暴政,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资格,人民就有可以起来推翻他。
这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使他们在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必须出来反省忏悔,否则就会危及到自身的统治。
另一方面皇帝权力的神圣性又意味着“朕即天下”,他们的权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用当心下了罪己诏后就会失去合法性,就会失去政权。
相反,通过下罪己诏还得够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帮助他们渡过统治危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最高领袖的权力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产生只是出于维护这个集权统治的需要,只是出于不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
为了维护最高领袖的权力,除了要靠不断的权力斗争外,还要实行个人崇拜,对他进行不断的神化,把他塑造为真理的化身。一旦最高领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真理化身的地位就丧失了,他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就要下台,沦为可悲的下场。
一辈子不检讨自己错误的毛泽东,却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一次罕见的检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58年,毛泽东开始发动了“大跃进”。这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唯意志论的狂热运动,严重地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效果,相反,但从这年的年底开始,它所带来的紧张局面就开始局部地暴露出来。
这时候,即使已经难以接触现实的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他就着手做“降温”的工作,搞了半年的纠“左”。然而,1959年7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纠“左”变成了反右,而且一路反到基层,继续发动“大跃进”,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0年夏天,全国性的紧张局面开始暴露出来。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着手开始对国民经济和政策进行调整。然而,这一次的努力又因为国际斗争的新情况而无法落实。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发生了第一次全面交锋,赫鲁晓夫对中共转攻不成,恼羞成怒,会后就通知中国要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合同。
消息传到北戴河会议上,激起了党内的义愤。大家憋着一口气,要为国争光,妨碍了调整方针的落实。②到了到1960年底,“大跃进”这辆战车已经耗尽了力量,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全国性的灾荒已经弥漫开来,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反思,倡导实事求是,号召调查研究,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重大的调整。
在这期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几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下了《十年总结》,明显地流露出想转弯的思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批转甘肃省委报告的批示。
他在这份批示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启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他写道:“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
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渡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毛泽东接着写道:“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定。
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7年,成为14年才能改变。
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③6月毛写《十年总结》时只发给与会者,没有向下传达,这次,毛泽东的自我批评连同甘肃省委的报告一同下发全党。
为了统一全党的共识,为了使经济调整顺利进行下去,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着名的七千人大会。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空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有所交待。1962年1月30日下午,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并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然而,在这个极为罕见的毛泽东所作的“检讨”中,他也只是泛泛地提一下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没有具体讲到自己犯了哪些错误,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三面红旗”更是没有提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他进一步说道:“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的讲话引起了毛的极大不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困难时期,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三年以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他又说,发生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便很欣赏并加以赞扬。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大意)罗瑞卿回答说:我作不出来。
七千人大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首先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的乌托邦追求。毛恋恋不忘他的乌托邦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付出代价在所不惜,遇到困难也不在话下。正是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问题和形势的观察和判断。1961年的经济调整刚取得一定效果,毛就开始流露出来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思想。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
”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到这几年的问题。他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1961年,在毛泽东的允许和批准下,国家对工业、商业、手工业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从之前“极左”政策的很大程度地退却了下来,初步缓解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基本上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尤其是他亲自组织《农业六十条》的制定,从1958年‘一大二公’的乌托邦理想退下来。
……尽管人民公社仍然保留了‘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的内容,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但从一定意义上说,经过一路的退却,1958年的那种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
”④然而,1961年的退却是策略性的,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肯定“三面红旗”。在毛看来,一定程度的经济调整是必要的,但它又是有底线的,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到底了,再退就是方向、道路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会会上,他出于对经济调整的不满,又开始发动了反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但同时,他还是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仍然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整经济上。从经济调整时期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国的经济体制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因此,这一时期也一直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局面,这也为毛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