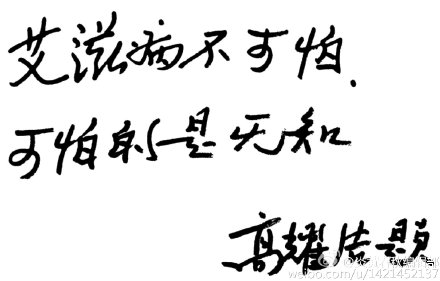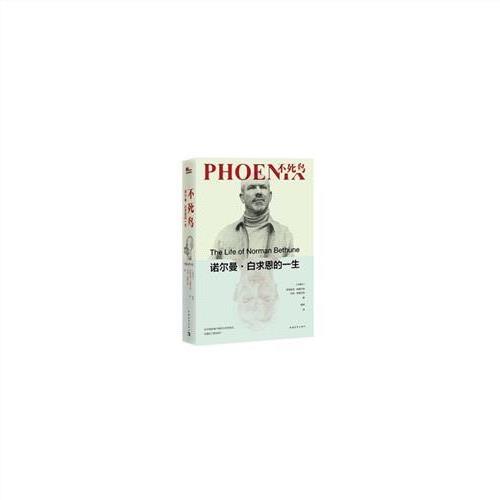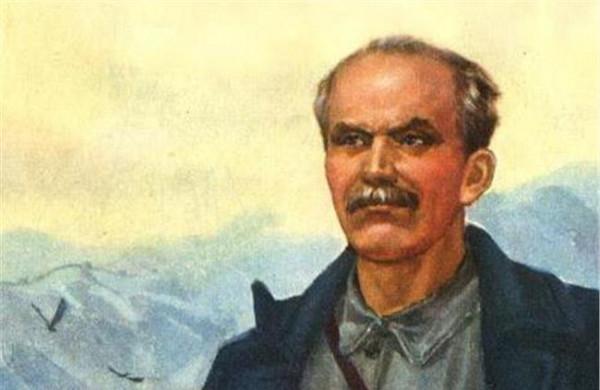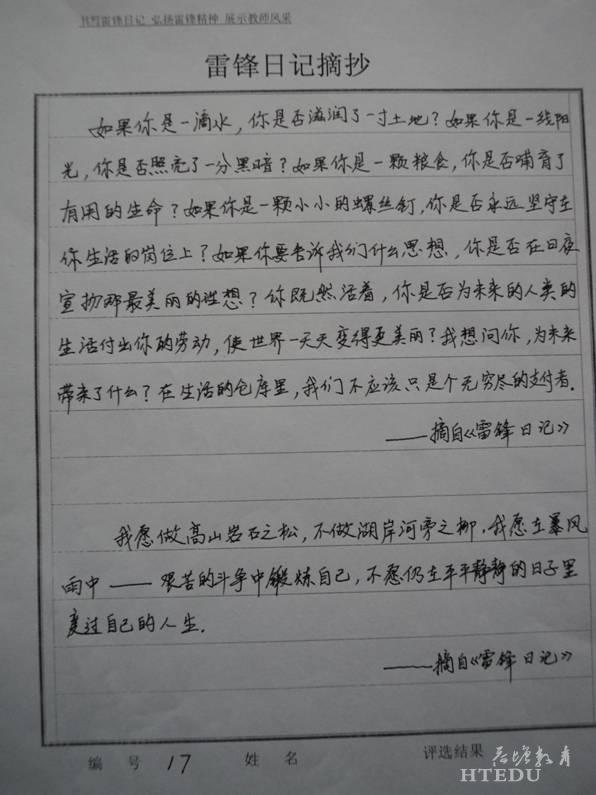李一氓夫人 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 …… 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
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
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
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
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
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
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
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
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一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
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
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
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
他对分配到郭沫若领导下的和平大会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
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
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因而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时,我建议他是否向上面作点解释和检讨。
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直到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
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革命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了名的。
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
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
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蒐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
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相当的收获。
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
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
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有的人甚至议论说,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可谓空前绝后,就是说,像他那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古籍知识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人来主持古籍整理,不但当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
这是人们对他生前的赞许和死后的惋惜。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总是"青出于蓝",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开创之功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只是由于我纯属外行,这方面虽也经常谈到,但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在现实中真正看到了一位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思想常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老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