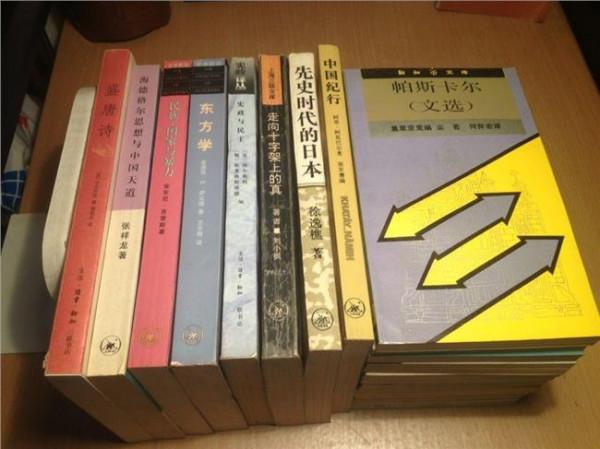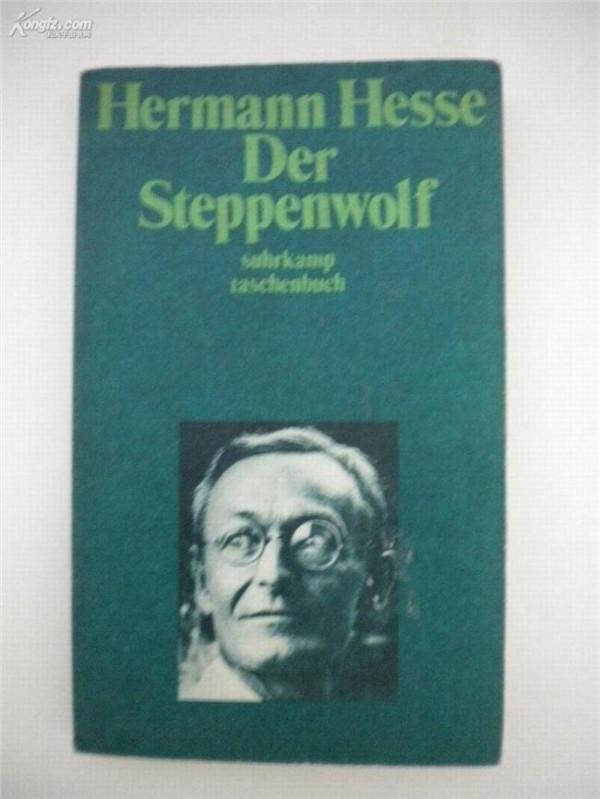谢林福德 51谢林 黑格尔 荷尔德林之闺蜜同盟的心灵斗争与悲剧宿命
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少年时代的“闺蜜同盟”绝不是愉快的命运安排,中庸性格的黑格尔受到的打击最小,或者说他是闺蜜同盟的唯一受益者,我对他社会活动的盖棺定论是,他能从每段友谊里收获最多利润,而他的朋友们从来不能从他身上得到多少好处。
倒不是因为他小气自私,黑格尔很重视友情,他给谢林和歌德等人写的“情书”简直肉麻到令人作呕,朋友们沾不到他的光,一是因为成名太晚,他果然像雅典娜的猫头鹰一样,到黄昏时才开始展翅翱翔,以迎合他自己对人生价值的预言:生命在世界与自我的统一中达到圆满 – 永恒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环。
就像拿破仑的命运一样,在实现自我价值的瞬间陨落,我认为这未必不是最完美的人生,天才和凡人都不必太重视养生,前者不确定他们能不能活到明天;凡人活过的100年或20年之间只存在着已取消理性之内的时间差异性的量而非程度的不同,而人的价值体现为创造和自我认识的程度深浅。
二是因为黑格尔是个事事依赖朋友,不善于直面人生之惨淡的人,从推荐工作到介绍对象都由朋友一手包办,他自己几乎毫无主见,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旁人的保护和资助中度过。
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许不那么光彩,但这种不动声色,即使不小心被打动而后仍能抱着疑惧的心情敬而远之的消极个性,却能使他免于革命思想的毒害,正因为他没主见,什么都想相信,才能从不同种欲望的持续不断的冲突斗争中发现矛盾的本性,再经由矛盾律与经验主义的调和创造出辩证法的成熟形式,他的精神哲学就建立在这种朝三暮四,早起革命傍晚信教的自我与本我的对立统一之上,他才能真正明白那对立其实是自我的衍生物,这又不
同于谢林的哲学,使他从对谢林的迷恋转向为彻底扬弃,因为对黑格尔来说,一切进入意识的对象都无非是为了将之扬弃,否定与超越,以实现自我最终与世界精神的融合。黑格尔在三人小组中天分最低成就却最大,他与叔本华的命运使我们确信,是性格而不是才识促成某一种哲学体系的诞生,正如叔本华因物质富足导致心灵永恒的空虚与不幸,从而否定理性,厌恶真理,想要抛弃哲学,他的哲学就注定是悲观论和对理性主义的反抗;黑格尔成功的秘诀则是由于他的死不开窍,一上来他就被同屋的荷尔德林和谢林各自非凡的创造力震住了,将二者视为偶像和无法超越的对手,他的消极心态避免了三人小组的内部竞争,并且由于艺术心灵与哲学心灵之间的深刻对立,他也根本不可能受到二人形而上的影响和塑造,他自己也承认,“在心灵的幼年阶段必须抹去自我”,所以他对谢林哲学和法国大革命的热爱都只是源于盲目的激情,它不是理性的产物,不受到原则的规范,像所有无知青年改造世界的豪迈一样,当幻觉破灭,他就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到保守主义的现实中去。
显然只有这样一颗深陷矛盾,没有在心性未定的青年时代过早地建立原则的“晚熟”的心灵,才能在意志和肉体都无愧于一个堂堂男子汉以后,创建出以辩证唯心主义为内核的大一统学术体系(主要包括哲学,神学,历史学,物理学或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艺术或美学,语言学等几乎是当时全部已知高级学科)。
荷尔德林可倒霉了,他是天生的诗人,拥有三人中最纯真的性情和浪
漫主义的典型人格,这一人格不幸为法国大革命的疯狂和迷误所催化,加上黑格尔那种对革命精神似懂非懂的刻意迎合(他像那个时代所有爱慕虚荣的年轻人一样,只是为了追求时尚而歌颂革命!),使这位善良的无辜青年在虚幻的浪漫爱情里越陷越深,最终心灵崩溃至无可救药,黑格尔也被朋友的不幸所触动,转而抛弃浪漫主义,日趋走向保守,或许他还将荷尔德林那颗最非凡的诗性心灵的崩溃当做自己哲学系统里,意志之自我消灭并圆满的一个实践证明吧!
其实他的朋友们若稍加留意就能在黑格尔的年轻时代发现他对浪漫主义的抗拒,他成名后对艺术心灵做出的权威解释正是对青年直观体验的改造,即否认自然景观拥有在心灵之外的艺术价值,他不会被缺乏精神的死的景观震撼,而这精神是只有人的心灵才能够赋予,并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的,他的结论难道不是对艺术的感性直觉的正面否定吗?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谈到他与同时代最伟大艺术天才歌德的友情,认为这是艺术心灵与哲学心灵相交融的证据,我却觉得两人的忠诚和相互吹捧不过是基于最现实的考虑,是歌德提拔了他,宣传他的才华,帮他找工作,资助他生活费,这无非是受歌德本人“爱才癖”作用的,并非是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认同的一般善举,如果我们能相信艾克曼博士的私人记录,歌德对黑格尔在聚会上的发言并无多少好感,他甚至有点儿不耐烦黑格尔拙劣的文才和对辩证法的滥用,歌德甚至亲口批评过黑格尔的语言表达能力。
歌德的文学艺术往往是对其哲学思想的诗性表达,这才是他能打动黑格尔的心理原因,他的《光学》也是对黑格尔保守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意识地赞助与迎合,加上对黑
格尔事业上的栽培,平日亦难得一见,这段友谊才能历久弥新,善始善终,它实在不能作为艺术与哲学可以在心灵中“兼容”的证据。艺术大师与科学巨匠之间的深交是极度危险的(其危险超过学院大师与统治者间的私人交往),甚至两种对立意识产生的同一种哲学的代表之间也不可深交,所以黑格尔才被谢林单方面宣布“分手”,以谢林思想之深邃浩瀚尚且以为黑格尔的体系与他如出一辙,可见这两颗心灵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尽管最后情谊还是保住了,却绝口不谈哲学。
即使荷尔德林不曾精神崩溃,他也不可能保住同注定走向保守的黑格尔的友情,因为打垮诗人的能量是由浪漫心灵同现实的冲突造成的,冲突不可避免,他必将在黑格尔毫无征兆的哲学觉醒的刺激下更为彻底地毁灭。我们同意黑格尔,奥古斯丁,保罗的瞬间彻悟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退一步讲,若黑格尔的心灵飞跃没有发生,他那内敛,精致却始终不能在精神外部自我实现的原本具有强大爆发力的灵魂,仍将造成荷尔德林的困惑不解,使他无法承受这一巨大的心理落差,就是说,诗人心灵的破碎是性格的必然,不可能被物质偶然性或人的任性改变。
最后的结局是谢林的全部哲学灵性亦被黑格尔对欧洲学术的彻底统治所消灭,至此三人小组被历史经验证明为纯粹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