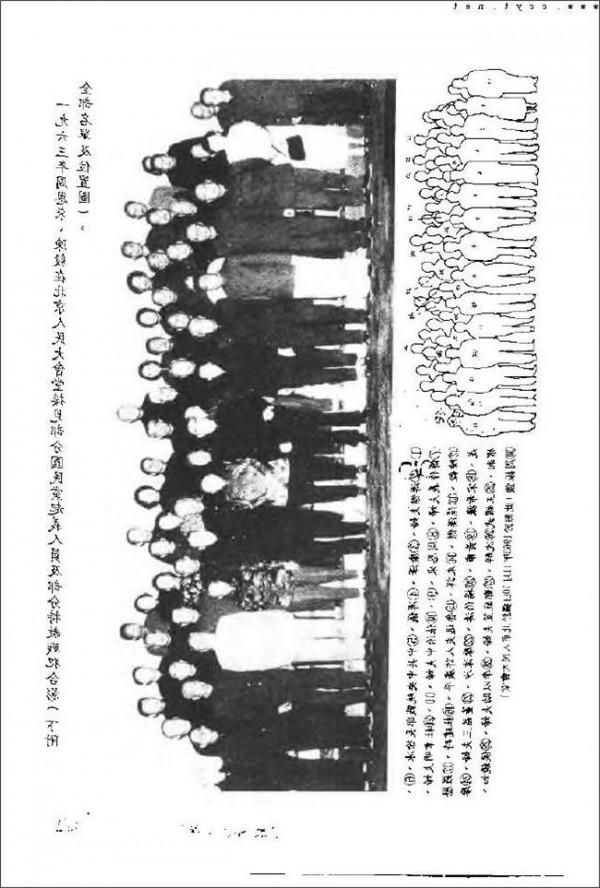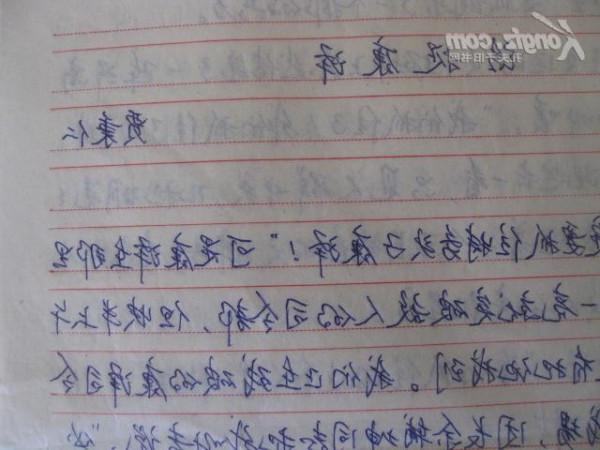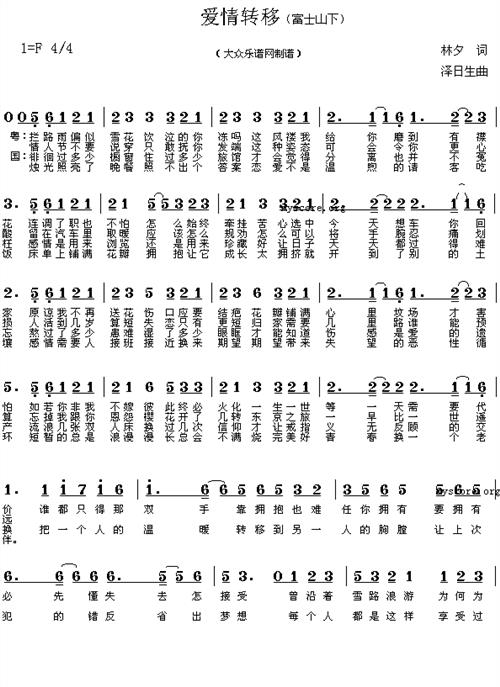康泽康生 康泽在襄樊战役被俘前后的回忆一(康泽自述)
六月三十日晚十一时过,华中剿匪总部来电给我说:「白总司令将于明日(七月一日)下午一时到老河口,希该司令官率同重要幕僚人员及行政专员等事前到达,准备举行会议,并加强飞机场一带之警戒为要。」夜间三时左右接到一六三旅报告,老河口东北的黑龙集(距老河口约六十华里)有解放军约六七千人活动,同时石花街方面(距老河口约五十华里)亦有情况。
据此判断,解放军有包围老河口的企图,除向华中总部急电报告外,并建议白总司令不要到老河口来,如有指示,请用电报。
白崇禧接到我的电报后,即不来老河口了。 七月一日傍晚,解放军接近老河口,我令一六三旅,向谷城撤退,当晚撤退完毕。 七月二日晚,解放军自东西两面向谷城进退,并由襄河东岸分数处渡河,抄断退路,一六三旅被截为数段,而分股向西南地区逃窜,至七月三日仍未与襄阳司令部取得联系。
七月四日,解放军继续南进,有进攻襄樊之势。
同时,我接到华中总部命令,令我在襄樊固守待援。我于奉到这项命令后,作兵力部署,检查库存粮弹。弹药尚不成问题,而粮食则大成问题,临时在附近迅速抢购若干弥补。 七月四日晚七时,解放军一部,开始向樊城攻击,与守军第一六四旅对战约两小时退去。
我当时判断,此系试探性质的序战,并指示一六四旅继续沉着固守。黎明前解放军一部再向樊城发起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又退去。
守军死伤共约十余人。估计解放军的死伤,较守军为大。因之,我即利用此估计的事实,指出利用阵地之利。一六四旅曾因此增高了沉着固守的信心。 七月五日,解放军仍在上半夜黄昏后、下半夜黎明前向樊城攻击,对战约两小时,又被守军击退。
因此,我对一六四旅的信心,与一六四旅本身的信心,均与日增高。 七月六日晚上,解放军除了在樊城发动两次攻势外,并于薄暮开始向襄阳西门外山地守备区攻击,万山和瑟琶山于当晚被解放军占领。
七月七日晚,樊城方面,解放军仍有两次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左右后,仍复退去。 七月八日,华中总部令我将樊城兵力转移,增强襄阳山地守备区的力量,并派空军于中午十二时在上空掩护渡河。
而一六四旅转移行动,颇为迟缓,所以落暮前未能接防完毕进入阵地,而解放军则于晚七时又开始向山地守备区各阵地攻击,与瑟琶山连接、对襄阳城西门有瞰制作用的真武山,即于此际被解放军占领;不一会儿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失守。
我知道凤凰山和无名高地两阵地是全山地守备区的脊梁,如果不派总预备队去收回,整个山地守备区,即将崩溃。
晚十点钟,凤凰山及无名高地的两党阵地,均已夺回。拂晓,解放军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被四八八团击退。 由九日到十二日,解放军每晚两次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均被四八八团击退,山地守备区,赖以稳固。
七月九日,华中总部来电,令我派兵收复真武山,并于中午派空军掩护。我令一六四旅执行此一任务,但一六四旅结果未能将真武山收复。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来电,问我将山地兵力转移城内,凭城垣固守何如?我覆电说,瑟琶山、真武山、岘山虽已失陷,但其余大部山区阵地仍在我手,倘全行放弃,则西门、南门及西南关全在羊怙山、虎头山及真武山的敌人火力瞰制中,于我更形不利。
七月十四日晨,蒋介石又来电话说,襄阳城垣坚固,山地兵力仍以转移到城内固守为宜。我感到这是蒋介石比较肯定的指示;同时,我又鉴于解放军从七月十二日以后,已未再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其它各阵地亦甚沉寂。
我当时估计,解放军有放弃对山地的攻击而径攻襄阳城或截断我城内与山地守备区联络的企图。我与郭勋祺、易谦、胡学熙及周建陶(视察组组长、战地视察官)等研究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山地守备区各部队于十四日中午十二时零分转移,按四八八团、一○四旅及一六四旅之次序互相掩护。
由南门入城,约在下午三时转移完毕。黄昏时解放军突向西门外的同济医院攻击。晚八时过,同济医院 失守,西门陷于暴露。
在山地各部队悉数转移入城后,各部队长以兵力集结,更具信心。郭勋祺向我建议,并自告奋勇说:「几个旅都调入城内,需要设一个城防指挥官,统一指挥,我愿来讨这个差事。
」我当即下了派他做城防指挥官的命令。他又向我要求说:「还请给我杀人权,允许我『先斩后奏』。」因此,我又下了一个手令:「在守城作战中,敢有贪生怕死擅自放弃阵地者,该指挥官得根据情形,即予枪决,然后补报。
」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想到,为了减轻一○四旅的负担,并使各部队任务明确,以免混乱起见,城防部署需要重行调整。我即写就要点。郭勋祺于接到我提示的要点以后,来对我说:「不能调整,时间来不及。
」于是我就把重行调整的意图放弃了。中午,我到鼓楼(即昭明楼)一○四旅及炮兵指挥所去看了一看,然后又转到视察组所住的襄阳旅馆和周建陶下象棋,以心绪不闲,未及终局就没有下了。
黄昏(约下午七时过),解放军开始在西门及南门攻击,双方对战,炮火相当猛烈。八时左右,一六四旅旅长刘玉杰来电话报告说:「好象敌人已经进了城了呀。」 解放军攻破襄阳城尽力死守已成孤军 不久判明,解放军是已经入城了。
城内四处发生枪声,喊杀之声震耳,守备体系已被打乱了。于是即作加强司令部守备的准备。梦想利用司令部周围的砖墙及四角的高碉和伏地堡,作死守计,以等待援兵。此时,各部队溃兵、司令部住在外边的人员和眷属,以及专员公署、县政府等的员兵,均纷欲逃入司令部。
郭勋祺为免司令部内的壅塞和杂乱,已令将前后左右各门关闭,并堆上沙包。易谦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向我建议,趁此混乱之际,走出司令部,利用水鬼,泅过襄河逃走。
我当时一方面认为,四面被围,逃出的可能极小;另一方面认为,我一出走,司令部核心工事,即刻发生动摇,不如死守司令部,尚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未采纳他的意见。他就去了。
他和视察组组长周建陶似即混出司令部,照他向我建议的行事。我以事已至此,未阻止他们。 我为避免流弹,从办公室转到碉堡。这时,城内各处的枪声和喊杀声,仍继续未停,而以鼓楼一带为最激烈。
鼓楼是一○四旅和炮兵的指挥所,最初尚和我通电话,约在晚十点左右,电话也断了,但仍在继续抵抗。我希望鼓楼和司令部这两个核心工事,互为犄角,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郭勋祺向我建议说:「我们固守着司令部,等到明天再看。
」我当时鉴于事已至此,也只有如此了。因此,点头同意;而我内心则怪他没有照我的指示调整部署,以致一处被突破,全城即发生混乱。夜十二时左右,鼓楼一带枪望及喊杀声渐趋沉寂,估计解放军或已占领该处,惟解放军尚未向司令部进攻。
因此,更以为司令部尚可固守。当将此种精况——襄阳城已被解放军攻破,及决心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等待援兵,向蒋介石及白崇禧报告,并请迅派援兵。 七月十六日黎明,我上到司令部高碉顶上向四面瞭望,间或听到稀疏的步枪声,并看到服装不同的人在远处城墙上行走,我即感到所有城门已被解放军占领,所有各部队似均已被解决,只剩下司令部核心工事了。
上午,接到蒋介石来电,大意说,他已饬顾祝同调派援兵。
并说:「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练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我看到这个电报,一方面觉得,他也许知道我不相信白崇禧的固守待援,所以叫顾祝同(当时已任参谋总长)调派援兵,也许真正有援兵来了;同时又感到,他这个电文,使我获得兴奋和安慰。
因此,我亲覆一电,大意说:「我决竭智尽力,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惟望援兵能迅速到达。」接着又接到白崇禧先后两个电报。第一电的大意是,叫我集结兵力,将攻入城内之敌驱逐。
我覆电说:「现已无此力量,切盼援兵早日到达。」第二电的大意说:「据闻退守核心工事,足见忠勇。」我当时看到这个电报,格外生气,觉得:说叫我固守待援,固守了十余日,而援兵尚无到达之期,以后叫谁相信这类狗屁命令!
中午接到宋新民(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当时因事请假到汉口)来电,大意说:「我到总部打听的结果,所派援兵原说在十六日从汉口出发,现在又要改到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
此间有关各方面,均担心缓不济急。」我接到这一个电报,觉得援兵要在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已经救援不及了。因之,颇为绝望。中午还吃了一顿饭。下午三点左右,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行政专员李朗生,一同来见我。
胡学熙向我说:「现在已经不能到外面挑水,司令部里已经没有水吃了!粮食和弹药也维持不了多久的时间。」董益三对我说:「现在固守在司令部理不是办法,应该派人出去办交涉。」我说:「双方短兵相接,即或派人,如何能派的出去?」他说:「派出去的人,先拿白旗摇一摇,对方就不会开火。
」我当时对他说的话很不顺耳,因此,我说:「我决心死在这里!」李朗生接着又向我说:「在司令部里固守,我看是很困难,不如利用今天黄昏时突围。
」我说:「你看怎样能够突出去呢?」他说:「敌人现在注意攻城,一定不注意外面山地的防守,我们利用今天黄昏的时候,从南门一带出城,向山地上走,只要上了山,这个山地很广,我们就容易走脱了。
」我当时相当同意他的意见,只需要有比较可行的方法。因此,我告诉他说:「你们去和郭副司令官研究一下,再由我做最后决定。」此时,我是在核心工事的坑道里,于是他们就到郭勋祺所住的高碉去了。 不一会儿,郭勋祺出来对我说:「现在只有固守,没有别的话可说。
」我当时对郭勋祺的态度表示完全同意。他又向我建议说:「妳这里不好,还是到高碉里第二层会好些,那里的墙厚些。」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我就转入高碉里去了。
我叫我的副官张子瑜,把我的自卫左轮手枪递给我,备必要时用。郭勋祺看到了,马上从我手上夺了去,并说:「不必!不必!这支枪还是由张副官带在身上好。」又问话了别的几句,我吩咐张副官到我办公室里把我的日记本烧掉,以免万一失落到敌军手里。
另外,我把一部分未处理的信和两套换洗的内衬衣裤,装在皮包里,教卫士张用之保管。这是我万一有机会突围时的准备。 此时的司令部防守的指挥责任,由郭勋祺对我负责,并指定了两个助手,一是第三处副处长舒子辉;二是勤务营长李光模。
所控制的部队,除了二十三旅教导队比较完整外,宪兵连和勤务营,都有很多逃亡或隔离在司令部外面了。检点可用兵力,已只二百左右,而壅塞在司令部的人员,有司令部的职员以及其眷属、专员公署及县政府人员,以及各部溃散官兵等,使得司令部的会议厅、办公室及核心工事里的坑道,均被塞满。
我当时曾感到,这样对于作战有极大的妨碍,但已不能把他们驱逐出去。
在碉堡中受伤被俘从此开始战犯生涯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右,解放军向司令部发起第一次攻击,未能攻入,但饭厅、厨房、办公室及译电室等处,均已中了很多炮弹,我所在的高碉,也直接中了炮弹数枚,最高一层(即第五层)的守兵,有死有伤,因之他们就向下面移动。
约半小时后,解放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击,我所在的高碉,又直接中了炮弹数发,四层、三层的守兵,续有死伤,他们纷纷下移。
解放军似乎已进了司令部前院。枪声和喊杀声愈更逼近。我所在中央高碉第二层的守兵,有的重弹倒地。原来董益三和胡学熙,均和我在这一层,此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们了。我转眼看到从射击孔扔进来一颗手榴弹,正落在我的面前,轰然一声,在我面前爆炸。
我被震倒在地,我当时又挣起来,摸一摸我的四肢,尚未残缺。因之,我又靠墙坐下。此时,楼上的官兵,纷纷从上面下来,向坑道里逃避,我又看到有第二枚手榴弹扔在我面前,无法驱避,又轰然一声,我被震倒地。
我不知我是否受伤,我只彷佛听到枪声和喊杀声越逼越近。不知经过了若干时间,枪声和喊杀声渐趋沉寂。我不知是怎样出了碉堡而被抬到一个街檐下,有医生在给我洗涤和上药,我又听到郭勋祺的声音,彷佛他在附近说:「哎呀!
受了伤了,要请你们好生医治哟!」给我上药的人答复说:「请放心,我们一定是好生医治的!」我身上原来所穿的衣裤,好象是被医生用剪刀剪成几块拉下去的。上了药之后,我又被抬走,不知道是向什么方向,但我已经知道是被俘了,一切都完了,将来不知是怎样。这是当时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