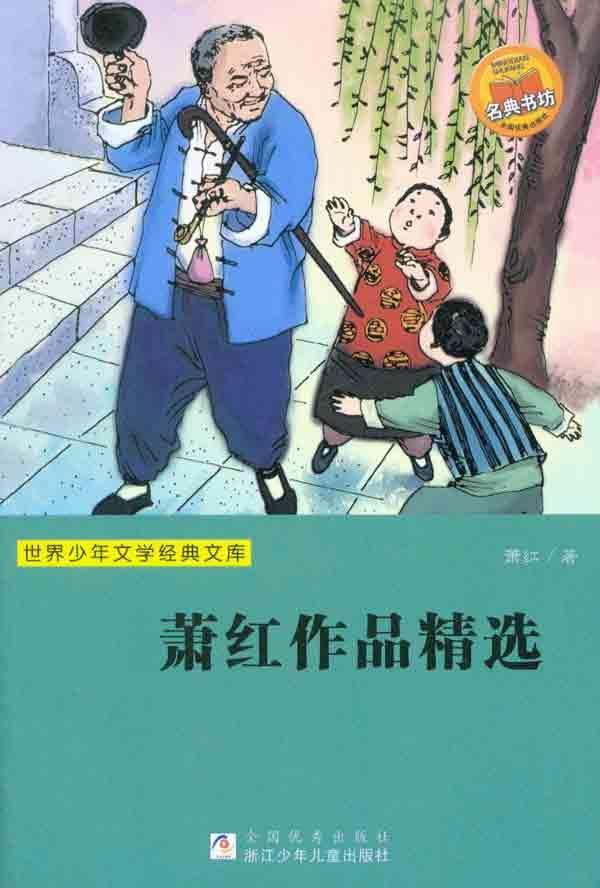萧珊的死 萧珊死前的话:“血还是不要输了吧?”
巴金步履蹒跚地来到中山医院太平间。
刚才,他从家里来医院的半路上,好象又走进一个噩梦的境界。脑际始终闪动着萧珊那双充满哀怨的眼睛。她似乎在冥冥中对他说:“我去了,你可怎么办?”
“蕴珍,你说些什么呀?你好好的为什么就能说去就去了呢?”他好象仍在与她对话。
在萧珊入住医院的几天里,他多次来到她的病榻前。有时他劝她吃饭,有时他什么事也没有,却依依地不肯离开她。萧珊总是不住地劝他:“回去吧,这里的空气不好。你坐在这里,我的心里反而不安。”
他固执地说:“没关系,蕴珍,和你呆在一起,我心情会好些的。”
她似乎也看出巴金心里在留恋自己,所以萧珊就再也不多说话。她只是稍稍闭了眼睛,然后把她那只有点发凉的手放在巴金的手里,让他紧紧地攥着。
“听说你要到广州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来?”巴金在路上匆忙地走着,他的思绪仍然围绕着萧珊俨如电影画面一般地展开。他好象又看到一片燃烧的战火,那是抗战暴发后的某一天,那时巴金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派遣,将前去广州去筹办一家分社。就在巴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和萧珊在上海一家咖啡厅里又见了一面。
那次见面给他的印象是既匆忙又紧张,因为车票是次日凌晨的,他和萧珊见面以后,还要回到他的临时住处去打点行李。而春夜又是那么匆促,巴金不希望让萧珊为了给自己送别,过迟地返回家里。那样的话他担心萧珊会遭到家人的怨尤。
巴金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之所以又想起了这段往事,就因为当时他与萧珊分手时,也象今天这种心情一样。彼此都有种恋恋之感。谁也不知此一分手,今后究竟会不会再次见面了。
“蕴珍,你只管放心好了,我到广州不会时间太长,只要把那边的工作安排好,我还是要回来的。”巴金坐在幽幽的灯影里,默默凝视对面这漂亮女友忧戚的眼睛。他顿时洞穿了对方的心灵,巴金发现她也象自己一样,对于这次分手看得十分重。那是因为自从1936年那个早春的上午他与萧珊结识以来,眨眼之间已经过了两年。
在这两年当中,他与她由不相识到发展彼此心通的朋友,其间确实历经了几多风雨和几多坎坷。他感到萧珊就象他喜欢的白兰树一样,散发着淡淡的花香,虽然并不浓烈,然而却时时嗅得到她那淡雅的清香,让巴金感到满足和怡然。
巴金所喜欢的就是象萧珊这样的姑娘。他在上海滩上闯荡,去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留学,身边当然也不乏异性的追求者,然而巴金都一概敬而远之,他回避和疏远时髦浪漫的女性,巴金需要寻找的是一位与他性格相近的女性作伴侣。
他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都市浪漫女性,甚至讨厌那些为势为财而不惜一切的女子。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快到三十岁了,仍然不想在上海安家结婚的原因。如今萧珊就俨然一位从天外飞到身边的知音者,巴金除了感到这位在女中读书的姑娘比自己小13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多么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啊!然而那时他必须要服从出版社社长吴朗西的指派,在战争逼近江南的时候前往广州。
萧珊的眼睛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她啜饮着杯盏中的苦咖啡,感到口里没有一丝甜味,苦涩的滋味让她心里平添了几分愁苦。她知道巴金在此时离开上海的危险,因为日本军队时时在威胁着莺飞草长的江南大地。她无法猜测一旦战火燃烧到上海或广州,她们究竟会不会再有相会的时机了。
想到这一层,萧珊的眼睛湿润了,她说:“李先生,不管今生我们是不是还能见面。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了!............”
“哦?......”巴金没有想到她会说这样感伤的话。听着从街上不时随风飘来的歌曲,他心境中也平添了几分愁苦。那是一部什么电影中的插曲,演唱者那如泣如诉的声音,让他听来颇有几分愁楚与悲凉。他也清楚在战争时期,这种分手也许就意味着生离死别,然而巴金无法抗拒命运,他想了许久,终于对她点了点头,郑重地说:“蕴珍,你千万别这样说,其实我们现在还只是一般的朋友。
我能回来当然更好,如果我们不能见面,你还有你自己选择前途的权力呀!”
“不不!”大出巴金的意料之外,平时看来十分单纯的萧珊,这时竟然现出了与她年龄极不相符的决然神态。她忽然紧紧抓住了巴金的手,发自内心地说道:“李大哥,你不能这样说,虽然我们还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我的心里已经再也装不下任何别人了。我想,你如果从广州回来,我想请求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到我家里去一次!.........”
“去你家里?”他感到很意外。
她却郑重地凝视着他,显而易见姑娘对此事已经想了多时,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对,见见我的姆妈。这样,咱们的事儿也就成了!............”
“哦?”巴金没有说话,可是他心里此刻却正在掀起万丈波澜。自从意外与萧珊邂逅以来,他只要与她见面,心情就会处于从没有过的兴奋之中。巴金知道他从心里喜欢萧珊,也看出这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姑娘,同样从心底深深地爱着自己。
然而,当初巴金与萧珊见面,仅仅是出于作者对读者的关切。决不会想到他与一位小读者会有一天发生超越读者与作者关系的情愫。而今当他第一次听到少女发自内心的表白时,心里才不由得暗暗一惊,他意识到自己终于遭遇了爱情!
“爸爸,在这边............”当巴金正在心里出现这种时空差异的意识流的时候,全然淡忘了他已经随着女儿小林和女婿祝鸿生等亲友来到了他熟悉的中山医院。巴金抬头一看,又看见了那间朝阳的病室,里面却是空荡荡的。
妻子生前住过的那张临靠窗子的床上,再也不见了他那熟悉的萧珊了。雪白的床被已被齐整整的折叠起来,让巴金见了眼里酸酸的。他蓦然记起就在昨天上午,她还在那张床铺上对他唉叹着:“药费这样贵,将来如何得了呀?.........”
“这个,蕴珍,这个你就不必管好了。你现在治病要紧......”巴金知道萧珊是一位非常勤俭的女人。即便“文革”之前他的稿费比较充足的时候,每当出版社寄来了版税,她都要小心地存到银行里去。那时候巴金和萧珊已经住进位于武康路上的那幢独门独院小楼里。
夫妻俩楼上楼下的生活着,每月的生活用费,萧珊都要做到精打细算。她不希望把巴金的稿酬花到一些无用的地方去,她始终把家庭生活控制到相当于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上。而她到一家杂志社里去作编辑工作,也是从来不索取分文报酬的。巴金喜欢萧珊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他知道她是一个只顾奉献而不求索取的女人。
“我不管...............可是,将来,你到哪儿弄那么多钱呢?”萧珊望着护士们不断把一些吊针和输血器械送到自己的床前来,心里就感到万分揪痛。她发现自从自己手术以后,几乎每天都要输血和输氧。巴金对她的病情如此关心,甚至到了不惜别一切代价为她治病的地步,这就更加让萧珊心里不安了。
她十分清楚自从1966年以来,随着巴金失去了安静的写作环境,他从前因写作而积存下的一些稿费,都被造反派冻结在银行里。她没有工资,巴金也不过只被允许每月从冻结的存款里支出一点微薄的生活费。萧珊生病以后几乎把全家多年积蓄的一点生活费,都全然花尽了。她也知道6月里巴金从上海回奉贤干校后,向“工宣队”提出的要从他冻结的稿费中支出一百元钱的要求,也被束之高阁地加以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