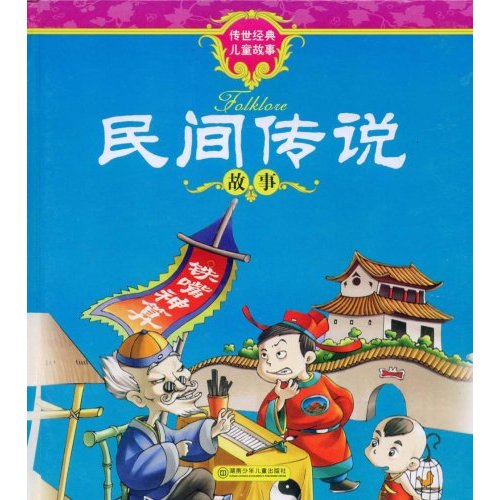陈思和民间 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
一、民间在都市文化建构中的表现形态
“民间”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1〕, 在任何国家形态的社会环境里都存在着以国家权力为中心来分近疏的社会文化层次,与权力中心相对的一端为民间,如果以金字塔形来描绘这两者关系,则底层的一面就是民间,它与塔尖之间不仅包容了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塔底部分也涵盖了塔尖部分,故而民间也包容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民间自身含有的藏污纳垢、有容乃大的特点。
在专制形态的社会里,塔尖与塔底之间的社会文化层次被大大地简化,在某些极端时期会出现极权统治者直接面对民间社会。
但是现代都市的文化建构则相反,它是以不断制造社会文化层面的层次性和不断消解政治权力话语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为特征,所以民间往往被遮蔽在多层次的文化形态之下,难以展示其完整的面目。
在现代都市文化形态下,生活其间的居民不像农民那样拥有固有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以民风民俗的历史遗物来唤起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记忆,都市居民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下始终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下,像上海这样有百年历史的大都市,其居民拥有四代以上居住史的家庭恐怕就不多,所谓“都市”的历史,常常给人一种流动无常、充满偶然性的印象,而与传统民间相关的原始性、自在性、历史延续性等特征都荡然无存,至多是从宗法制传统社会携带过来的旧生活痕迹,如民间帮会的某些特点,并不具备新的文化因素。
因此在都市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中,关于“民间”的传统含义(如一些民俗性的生活习性),只是一种依稀的记忆性存在,即都市居民的家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今天还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都市文化建构并没有实际上的建设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都市文化这座金字塔形的“底”,只是一种呈现为“虚拟”状态的价值立场。
笔者在《民间的浮沉》中曾把中国抗战以前的民间概括成三个文化局面:旧体制崩溃后散失到民间的的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新兴的商品文化市场制造出来的都市流行文化以及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农民所固在的文化传统。这里除了第三种以外,前两种所包含的民间意义都含有“虚拟”的成份。
譬如学者陈寅恪,自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2〕,在庙堂、 广场两不入的状况下滞留民间,默默守护着文化传统;同样的例子还有钱钟书,其在五十年代以后虽然侧身庙堂,仍能三缄其口,以管窥天、以锥插地,埋首于中西文化大境界里。
这或可说都属于第一种。再者,所谓民国旧派(鸳鸯蝴蝶派)文学,其前身为显赫的知识分子精英集团南社,但光复以后未能恢复其在庙堂的地位,于是锐气一败再败,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击下,他们退出了文化的主导位置,却转移到刚刚兴起的都市传媒领域,从事报业、出版、电影以及通俗小说的写作,居然也培养起一些堪称大家的后起之秀。
这或可说属于第二种。应该说这些文化现象都属于都市民间文化的最初形态,但是民间对它们的真实意义,只是当时主流文化——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和五四新文化以外的一种立场而不是价值取向本身,他们所寄托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并非属于现代都市民间自身的话语传统。
在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庙堂与民间以对应关系构成自足循环体系,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道统)借助庙堂而波及民间,两者是沟通的。民间虽然有自在的文化传统(小传统),但仍然以庙堂文化(大传统)为主导文化,因此在古代社会里,国家主流文化艺术传统与民间自在的民风民俗传统一起建构了当时的民间文化形态,(孔子整理《诗经》分风、雅、颂三层次,从民风民谣到贵族生活再到祭祖颂神,从物质追求到形上追求,可以看作是当时民间文化形态的最完整的构成形式)。
但是这种文化的自足循环体系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本世纪以来,庙堂、广场、民间三分“天下”因无法圆通而呈分裂状〔3〕, “道统”已随着传统庙堂的崩溃而瓦解,知识分子在庙堂外另设广场,替天行道地承担起启蒙民间的责任,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日益式徽,与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越离越远,它们即使散失在民间天地也不可能真正反映民间和代表民间,所以只能是一种“虚拟”的民间价值取向。
理解现代都市民间的价值取向虚拟性有助于我们区别以宗法制社会为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态,当我们在考察和表现农村文化生活时,会以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伦理形态作为民间文化存在的依据;但在考察和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时,显然不能移用这些实物考察的方法。
过去有许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些区别,对都市民间形态的考察总是局限在对黑社会、旧风俗、没落世家等陈旧生活现象的范围,使都市文化中的民间含义变得非常陈腐可笑。其实在现代都市社会里,由于民间的价值取向虚拟化,它的范围就更加扩大了,因为它不需要以家族或种族的文化传统作为背景,其表现场景也相应地由集体转向了个人,现代都市居民的私人空间的扩大,隐私权益得到保障,民间价值的虚拟特征在个人性的文化形态里得到加强。
过去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应的民间往往是通过“家族”、“宗族”的形态来体现的,文化价值是以集体记忆的符号来表现,具有较稳定的历史价值;而在现代都市里,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应的是个人,当然个人主义在文化上也可能表现出某些雷同现象,如年轻人喜欢在迪斯科舞厅里寻找消遣,如果说在今天农村边缘地区残留的民间节庆舞蹈形式具有民族集体记忆的历史符号,那么在迪斯科舞厅中的狂舞背后并没有什么稳定的历史符号存在,不过是一种个人性的选择。
迪斯科舞当然是非官方化的娱乐,它属于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但它的“民间价值”是虚拟的。
这种虚拟的不稳定的都市民间价值形态,只是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的现代化过程还未最后完成,现代都市文化的背后还缺乏强大稳定的市民阶级意识来支撑。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对中国市民阶级在历史与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总是抱过于乐观的态度。
比如说,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较好时期,但是否因此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民间社会呢?显然没有,三十年代与当时国家权力中心分庭抗礼的主要力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及其背后潜在的政党力量,民间只是被动地为多方政治力量所争取的对象。
同样,也有的研究者不无忧虑地指出中产阶级文化的保守性可能会在当代都市文化建设中产生负面影响,笔者以为当代都市文化建设中会有各种负面效应存在,但还是不要轻易地归咎于中产阶级社会,一个本身还没有具备完整形态的社会怎么会已经“预支”了它的负面文化影响呢?中产阶级虽然是个很时髦的词,但距离今天的现实毕竟还有些遥远,不如对中国现代都市的民间形态的研究也许更能反映我们所面对的都市文化的实际状况。
所以,民间在都市文化构成中的虚拟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类似市民阶级、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学分类概念,更不是类似西方中世纪自由城邦制度下的“市民社会”,它是笔者根据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变化而用来象征文化形态的分类符号。
这里所指的庙堂、广场和民间,都不是指实际的社会结构,而是近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从权力中心位置放逐出去以后所选择的文化立场,知识分子既然身在权力中心之外,不必以庙堂为唯一的价值中心,只是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建立多元的知识价值体系,以知识立本,在学术传统中安身立命,促进社会改革和文明步伐。
这便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既然这种岗位是专业性而非政治性的,它只能依据民间的立场来实行。
虽然对都市人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再也找不到像农村残留的纯然自在形态的民间文化,但它的虚拟形态依然存在于都市中,据本文前面所借用的金字塔底的比喻,在都市中我们能找到的只是介于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虚拟状态的民间之间的各种都市文化形态,在每一类都市文化中都存在着两极的成分:一方面是对权力控制的容忍与依附,另一方面是对权力中心的游移与消解。
从都市通俗文化思潮泛起到大众传媒的盛兴、从知识分子的民间学术活动与创作活动到教育、出版体制以及各种文化市场机制的改革,都包含了上述两种成分的融合和冲突。
二、现代都市通俗小说与民间立场
前面已经论述过,本世纪初形成的现代都市通俗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有些不同特点,在古代通俗文学可以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本世纪社会转型以后,这种通俗文学的价值取向已经与都市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发生了分离。但它仍然是属于都市民间的一种形态,尤其在通俗小说领域,它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国家权力形态与民间政治形态的结合。
首先应该说明,都市通俗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从理论的界定上说,真正来自民间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它的集体性创作的原则,决定了民间文学作者呈无名状态,即使个别作家的名字有幸保留下来,多半也是以整理者的身份而非创作者的身份;还有,它的非书面性的原则,民间文学作品是依靠民众口头代代相传中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的,真正的民间作品不可能有标准的文本,它一旦被文人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也就结束了民间性〔4〕。
当然这只是西方学术界的一种较传统的界定,依这些标准来衡量,都市通俗小说不过是文人利用民众可能接受的方式(包括语言、形式、审美趣味等)写出来的文学性读物,根本不能算是民间文学。如果从本文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界定来看,两者的区别还不仅在于这些外在的标志,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化形态的标志在于它真正贯通了民众的生活意义,表现出生命形态在自由自在状态下的生气,这种生气不可能产生在权力制度的支配之下(非庙堂性),也不可能产生在思想道德的约束之下(非广场性),当然它也不可能产生在真空似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往往在被动地包容外在文化形态对它的侵犯的同时,努力用审美形态来表现自身的顽强生存意志。
在今天的现代都市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民间审美价值的可能,一些优秀的作家只能把审美的触角伸向都市以外,在一种虚拟的民间状态中召回民间的正义力量。
这在张承志的哲合忍耶宗教和张炜的“融入野地”哲学里都充分反映出来。但我们回到历史的状况下考察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正视民初以来都市通俗小说所含有的民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