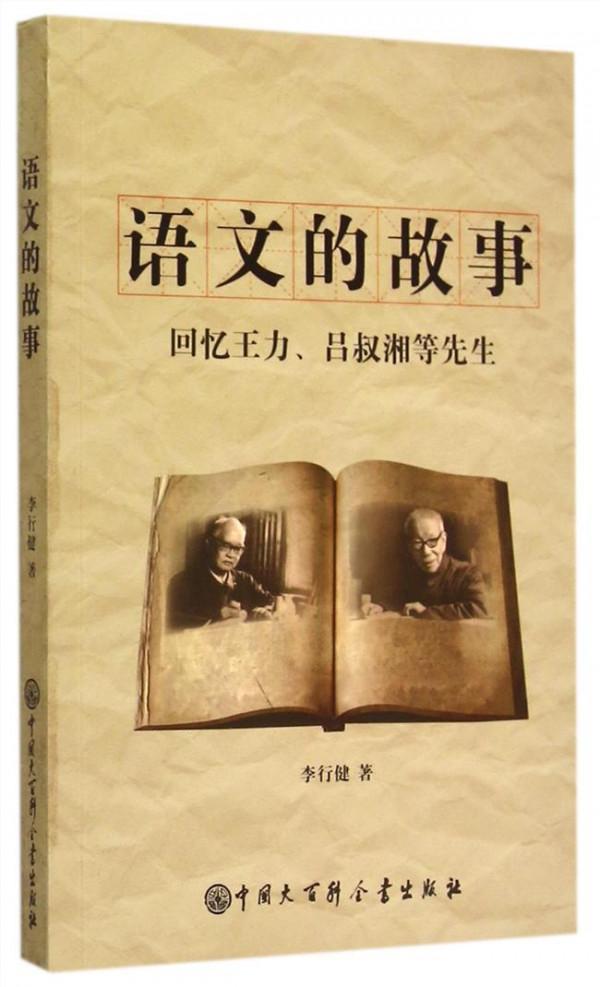王力吕叔湘 我所景仰的王力先生与吕叔湘先生
我的一生有幸拜见到中国语言界老一辈的许多大师,他们的人品学识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我,他们曾经在学术上教导我指引我,也曾在各方面关心我,帮助我。朱德熙先生与林焘先生是我当研究生的导师,他们逝世后,我参加了一些追悼活动,发表了纪念文章。我也曾有幸拜见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接受了他们的教导,我想把对这两位大师的点滴回忆写出来,这些回忆已经珍贵地保存在我心中很久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力先生是在燕南园60号,王先生家里。当时,我们几个新来的学语言的研究生一起去见王先生,我们在厅里坐好等着先生,一会儿,楼梯响,王先生下楼来,我们一一拜见先生。我当时心情忐忑不安,但王先生问完我的名字说:“刘兰英,和郭兰英一个名字,好记。”才让我稍稍放松。从此,王先生就记住了我的名字,以后的多次面谒,先生都能马上叫出我的名字。
我研究生的毕业考试,由王先生、朱德熙先生与林焘先生组成主考小组,进行口试。我的老师对于我这个基础差而能用功赶上来的学生是很鼓励的,我记得其中有一道题是就一个语法结构,谈各家的不同分析(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我谈到王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的分析,先生还点了头。
文化革命中,先生受到许多的冲击,我都是听说的。但有一次我受命到北大中文系借什么资料(反正是运动所需要的),当时中文系还在文史楼,我从办公室拿了资料出来,正好撞见王先生从厕所出来,当时,他头戴一顶破草帽,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中山服,还拿着一把笤帚。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王先生!”先生什么反应也没有,瞪了我一眼,转身又回厕所了。我当时想他肯定没有认出我是谁,也没有听见我叫他。
76年天安门事件后,我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与十多个同事们一起组成“童怀周”(共同怀念周总理的意思)整理编辑了《天安门革命诗抄》诗集、《人民的悼念》画册,我给王先生、林先生、朱先生各寄了一套。之后,有一天,我去看王先生,王先生见到我很高兴,对他的夫人大声(师母有点耳背)说:“她是刘兰英,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
”聊天中,王先生居然提起那次在中文系的尴尬相遇,他说:“我那时是牛鬼蛇神,你不该叫我‘先生’,让人听到或看到就麻烦了。
”原来先生怕我受牵连,所以,不回答,赶快走开了。我想当时王先生自己在磨难中,还如此地爱护着自己的学生,考虑得那么周到,真令人感动。以后,我多次去先生家里,与先生及师母都很融洽,我们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王力与王季思两位王先生担任了顾问,我记得当我请王力先生当顾问时,他欣然接受,还开玩笑说:“连你们这个,我已经当了12个顾问了,顾问就是顾来问的,你们要问什么就问吧。
”他还为我们的词典题了书名,开始,我拿宣纸去,先生当场赐字了,但过不了几天,我收到先生的信,说:“兰英同志:宣纸不好写,现在另纸写了寄上。此候,教安。王力1979、9、6、”(见附件1)。先生是这么热情地、认真地帮助学生,对学生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1986年学校派我到日本做短期访问,等我回京,王先生已经仙逝了。我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了王先生家,厅里挂着王先生的遗像,我默默地鞠躬流泪。王师母接待我,详细地给我讲述王先生住院治疗的情况,痛诉了不少遗憾与伤心,我听着一面劝慰一面流泪,直到很晚才离开。当时,正下着雨,我在凄风苦雨,痛思疾念中匆匆赶回家,大病了一场。
1978年,我们与上外、北外的汉语教研室共同发起召开外语院校汉语教学研讨会,我们给几位老先生写信,请他们赐教,我们接到了王力、吕叔湘、朱光潜、叶圣陶、张志公等语言界著名学者的回信,对于外语院校的汉语教学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这些意见我们在会上都好好的学习了。1993年第5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由我主编的汉语专号刊登了这些书面发言,我当时把刊物与稿酬一一给各位先生寄去了,有的是寄给了他们的孩子。王力先生的我送到他家里,当面给了王师母夏蔚霞先生。
吕叔湘先生是我很早就仰慕的大师之一,但无缘当面请教,我记得在北大时,吕先生曾来过多次,但旁边总有许多的人,我这个人为人低调,不是向前挤而总是朝后退的,所以,无缘面识吕先生。工作之后,我也没有机会向吕先生当面请教。想不到1984年12月,社科院在我们二外进修的一位同志来找我,说吕先生看到了我们编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要我同吕先生联系,并把吕先生家的地址告诉了我。
当时,我们编辑《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成员们商量要转入四化,搞科研,要我拟一个科研题目。我提出分册出《中国古代文学》,采取先编容易的、影响大、有新意的,所以,先编名句分册,并先搞古代诗词曲的名句。1982年《古代诗词曲名句选》问世,当时这种类型的书很少,社会反响很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50多万册,并获中南地区优秀图书设想奖。
正如刘叶秋先生在《诗句如海,源头何来》的跋中指出:“它既是一种工具书,又是一本文学欣赏的普及读物,编撰的设想是很好的,可算是有益的尝试。”没有想到吕先生也看到了这本书。
我遵照地址先写了一封信,请先生对我们这本书加以指教,表示要去当面请教。一周后先生回信了:“兰英同志:去年12月26日信早已收读。编一本大型的引用诗文词典是很有需要的,不知道你们有几位参加,编辑条例已否定妥?我觉得这样一本词典,如果要它发挥作用,第一要收得博而不滥,第二要有很好的索引。
这种词典应当是为读者服务而不是为作者服务的,所以,不应该分类排列而应按年代和作者排列。此外,我一时想不出什么意见。如只是为此事,不敢劳驾枉顾,但赐访终归是欢迎的。
此复,即颂教安。吕叔湘85、1、5”(见附件2)。我接到回信后就去看吕先生,接待我的是吕师母,她告诉我先生到所里去了。我当时给先生留了一个条,就告辞了。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吕先生的信:“兰英同志;枉顾失迎为歉。
请先打电话约一时间。我的电话是50、2484,敬礼!吕叔湘1、25”(见附件3)。我按要求先打电话,后去,终于见到了吕先生,能当面听先生的指教,这是我久已盼望的。先生第一次接待我,好象对我并不陌生,先生知道我是北京大学现代汉语研究生毕业,先生看到了我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词曲名句选》一书。先生亲切地指导我们的编写工作:
吕先生认为一个字不知道,可以查字典,一个词不会,可以查词典,而一个句子不会解释,找不到出处,就很难查了,以句为单位的辞书太少,他鼓励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编一本以句为单位的辞书。他说:“收条要多,要指明出处,但解释要精练,不能多,要有很好的编排与索引,方便查找。
”吕先生的关怀,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吕先生的教导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当时,我们应该在先生的指导下,组织一批人编写这本词典。但后来这种名句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不少在规模、体例、内容上都是后来居上。
而我们又忙于编〈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的其他分册,一直没有按吕先生的教导去做,也就不敢再与先生联系,但我心里一直记着先生的教导。等我们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词典》五卷本交稿后,我就立即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编写这种词典,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们编写的〈中国古代名言隽语大词典〉。
书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这本书离吕先生的要求可能差得很远,当时先生身体又很不好,我不敢打搅,也就没有把书寄给先生。1998年与先生遗体告别时,我痛悔自己辜负了先生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