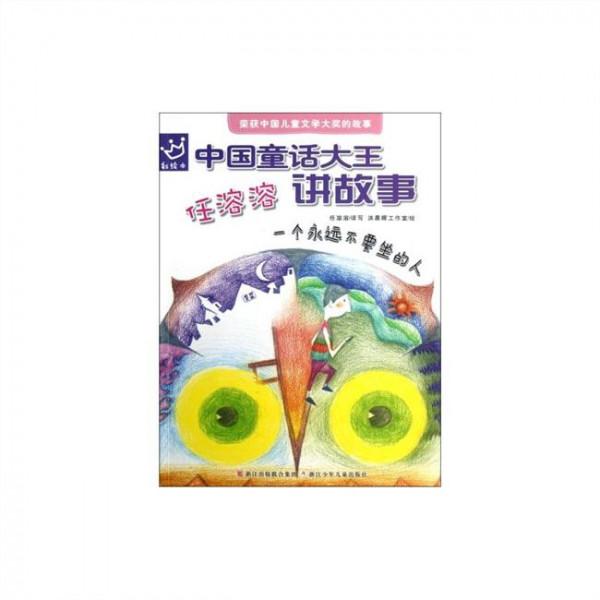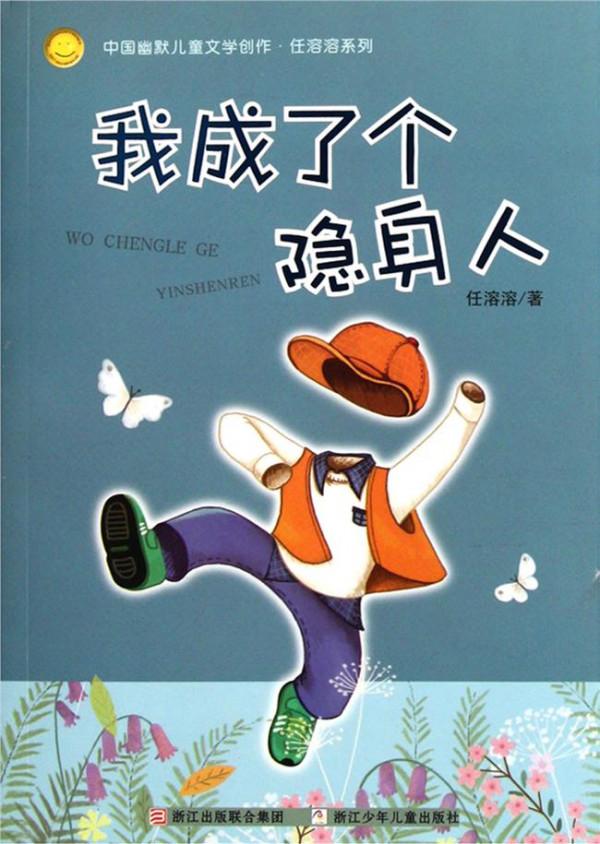任溶溶出生地 任溶溶:我天生应是儿童文学工作者
殷健灵:今年您已经88岁,若是从22岁翻译外国儿童文学开始算起,至今已有66个年头了。88和66,是两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数字。但您好像并不喜欢过生日,更不喜欢开创作研讨会之类。这是为什么呢?
任溶溶:你问我为什么怕开研讨会,我就是怕惊扰朋友,怕大家为了让我高兴,说我好话,当着面称赞我。我更怕热闹后的寂寞。
殷健灵:2003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首次设立杰出贡献奖,就把这个奖授予了您。记得在授奖仪式上,一向乐呵呵的您在致答辞时哭了,这让我很震惊,也很感动。对您来说,儿童文学意味着什么?您在译写儿童文学之外,还做了很多事。
译过历史书,做过文字改革工作,编过《外国文艺》,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和译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编发了那么多您给《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写的随笔,从中知晓了文化界的很多人和事。读您的文章,总感觉是面对深阔而宽广的海洋。但您最喜欢的,大概还是和儿童文学为伍?
任溶溶:那次我哭,是因为激动,是因为怀念一直爱护我的陈伯吹前辈。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我是1947年因偶然机会进入了儿童文学界。我先说说这之前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自小爱读书,5岁进私塾,识了许多字,就开始看连环画,读旧式章回小说。并非我特别聪明,识那么多字,我读书完全是读故事,读得懂多少就多少。
《西游记》我绝对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读过,我想大多数人也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急于看故事而已。我进小学一年级已经会用文言作文。我小时候在广州,讲广州话,不讲国语,白话文不见得比文言文学得更好。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文心》,还有翻译作品《木偶奇遇记》《宝岛》。
抗战爆发后,我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开办的雷士德中学上学,高年级同学里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介绍我们读进步书籍。我初中就读了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深受影响,以后很多事情都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想。我爱上了新文学,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文字改革运动,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接下来,我就做这个工作,读大量的中外语言学书籍,也大量阅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读大学时,觉得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用不着老师教,但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有老师指点,于是选择了中国文学系。
也因为我读语言学的书,对学外文很有兴趣。中学时代英文基础很好,后来爱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加上老同学草婴俄文学得呱呱叫,又使我产生了学俄文的兴趣,学了俄文。
我在1947年投入儿童文学前,就是这样读书的。如果不是碰巧走上了儿童文学道路,我会做什么工作呢?
我想我会做翻译工作,事实上那时候已在译美国斯坦贝克的《罐头工厂街》,在译儿童文学后,也译过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的长诗。编《外国文艺》时,译过日本小说和剧本,“文革”期间译过历史书《北非史》,学术译文与儿童书的译文完全不同,是那种学者味道的文字。可以说,要我译成什么样子都能做到。
我想我也可能会是个语文工作者。事实上我做了多年的文字改革工作。而且我是个广东人,在文改前辈王益同志鼓励下,我曾长期钻研广州话。“文革”期间,我没事做,就收集广州话词汇,编过广州话词汇,可惜“文革”一结束就忙于别的事,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完。我现在还想把它做完。
我想我还会做别的事,例如写剧本。我早就把左拉的《酒馆》改编成剧本;我会当编辑,在进上海少儿出版社之前,我就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编《文化学习》杂志。对了,我是当过编辑的,在少儿社、译文社,我都当编辑。
可是我天生应是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根据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项工作,儿童文学也需要我这样的工作者。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是新兴的文学,是大文学中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需要人才。我做这个工作真是如鱼得水。
殷健灵:说一个或许并不准确的数据:解放后17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共出版了翻译作品426 种,而您个人就翻译了30多种。您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前几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则是由丹麦首相哈斯穆斯亲自授权的惟一的官方中文版本。翻译了这么多作品,您最喜欢哪部作品、哪个作家?
记得您说过,翻译这么多经典的世界儿童文学作品,不单单是给小读者读的,还想给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我想,如果没有您的这些译作,我们这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后辈作家可能会失去很多宝贵的经验。
任溶溶:1945年我给《新文学》杂志译了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是土耳其儿童小说《黏土做的炸肉片》,但它只是碰巧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品,我当时只当做普通小说翻译。直到1947年为儿童杂志译稿,我才明确地找儿童文学作品译。一看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就投入了,可见儿童文学作品多么吸引我!
我爱儿童文学,是我爱文学的延续。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是重视儿童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但前途无量。我一向称儿童文学为新兴的文学。正因为历史短,古典儿童文学数量有限,且质量也很难与大文学比拟,有人把儿童文学看做“小儿科”,看不上眼,可能与此有关。但儿童文学的大作品将陆续出现,出现在未来,这就需要有大作家出现。
我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有苏联的马尔夏克、意大利的罗大里、英国的达尔、瑞典的林格伦等。他们已经留下来一些经典作品,但远远不够。
我希望各国儿童文学作家写出好作品,让儿童文学这个新兴文学繁荣起来。
我醉心于儿童文学,当然希望为我国儿童介绍些好书,满足他们的需要,让大家知道国外有什么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借鉴。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我自己正是通过阅读和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学会创作的。我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
首先学会取材,我发现生活中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就用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译了许多名家作品,也学了许多手法,我也可以创作啊!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国际关系改变无书可译时,就尝试创作,写的最多的是儿童诗。我写的每首儿童诗都有生活来源,或是童年回忆,或是几个孩子的生活趣事。正因为我对外国儿童文学比较熟悉,才会有信心,认为自己写得可以。我想我译的东西对同行也会有借鉴作用的。
殷健灵:翻译界后继乏人,更不用说儿童文学专业翻译了。而您却掌握了英文、俄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四门外语,后两门还是在“文革”十年无聊时学的。您在翻译时,多用口语,关于前人说的“信达雅”,用在儿童文学翻译上,您是怎么看的?对当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您有什么建议吗?
任溶溶:翻译界一直谈论的“信达雅”问题,我想理应由理论家来讨论,我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我的中国话说出来,但求“信”,原文“雅”,我也雅,原文不“雅”,我也不雅,作者要读者懂得他的话,自然“达”,那么我也达,这也是“信”。
我翻译的如此而已。依我了解,“信达雅”的说法是翻译界前辈严复提出的。他那时候翻译用文言,我们知道,文言是很讲究的,用文言翻译外国话,不像我们今天用口语翻译外国话那么方便,因此要考虑译文——文言的译文让大家看得懂,即“达”;又要保持文言的雅,但严老先生很了不起的是坚守一个“信”字。我觉得我今天翻译,一个“信”字足矣。
说到口语翻译,我的普通话是可以的。我童年在广州,只说广州话,1938年回上海,不会上海话,也不会国语。真是多谢拉丁化新文字,我是通过它学上海话和国语的。为了迅速扫除文盲,当时拉丁化新文字不但有北方话(即普通话)拉丁化新文字,还有江南话(即上海话)和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
我既然做这个工作,自然通过拉丁化新文字学上海话和普通话,都学会了。进一步,我还想让我的普通话更提高,带有京味,于是大听相声。侯宝林来上海演出,我天天去听。
我曾做到去北方馆子吃涮羊肉,北京人称我为“老乡”。我当时普通话如何好,从早年写的《天才杂技演员》等童话中可以看出来。只是后来“文革”期间我编广州话词汇,一直用广州话思考问题,广州话回潮了。如今年老,母语(广州话)回归,普通话就说不好,带广东腔了,真可惜。不过文字上,我的普通话还是规范的。
我前面说到外国儿童文学很重要,应该有长期关注外国儿童文学、不断引进外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译者。但过去是我发现好作家的作品就译,译了就出版,可如今不行了,发现了好作品先要买版权,那就得通过出版社。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者又往往顾不上儿童文学。
因此,我只希望出版翻译作品的各少儿社重用译文编辑,让他们关注国外重要儿童文学奖项和儿童读物出版情况,找好书看。不要只注意畅销书。畅销书也有好书,但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畅销。明年国际安徒生奖又要颁奖了,候选人名单已经发布,他们的作品就可以注意一下。明年得奖者的作品更要看看吧?这是我关心的一件事。
殷健灵:您创造了著名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他们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除了大家熟知的童话和儿童诗,您还写过小说。您认为,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需要哪些天分和储备?
任溶溶:我写过小说,都写国外的事情。如《我是个黑人孩子》《变戏法的人》《亨夫雷家一个“快活”的人》等。当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努力创作就是了,有几分热发几分光,优秀不优秀,先别管他。
殷健灵:您写的儿童诗里,大家喜欢《爸爸的老师》,但您自己偏爱《强强穿衣裳》。强强穿一件衣服就玩一会儿,一天过去了,鞋子还没穿上,妈妈已经在叫他脱衣服睡觉了。像这一类“有意味的没意思(nonsense)”的东西,您是怎么看的?
任溶溶:外国儿童文学很注重nonsense,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以为这nonsense乃是一种童趣,只是大人觉得没有意思而已。
殷健灵:您一生都在做孩子,是您妈妈永远的孩子。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见您,便是听您在和朋友们聊妈妈,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白头发爷爷像孩子一样说“妈妈”两个字;近年,又读到您怀念妈妈的随笔,特别感动。您小时候家境优裕,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成年后也遭遇过变故挫折,但哪怕是“文革”里受过的苦,您现在说起来也不以为苦。
这样一种达观乐天的品质,是天性呢,还是来自“修炼”?您在耄耋之年,仍旧译写活跃,现在您想得最多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