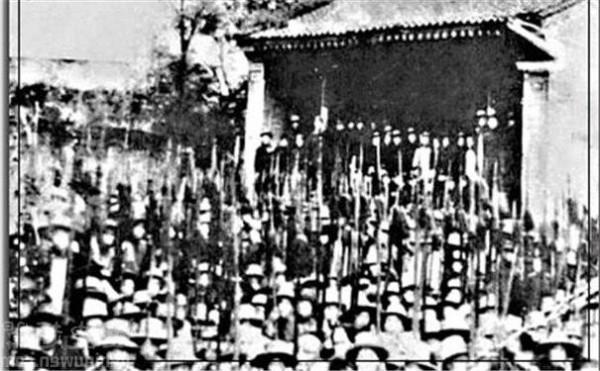【日本人如何评价邓世昌】英雄还是莽夫?小记致远舰的最后二十分钟
日本人对邓世昌的冲锋并不看好 说白白损失了一条军舰,北洋水师是勇者过勇,怯者过怯,当然也许是日本人不了解致远快要沉没的情形1894年9月17日午后3时10分后,一艘业已严重倾斜,浑身窜着猛烈火焰的军舰冲出了本方队列,以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冲向了敌舰。
与此同时,敌舰正拼命地向它倾泻炮火——最终,这艘军舰没有完成它最后的航程,于二十分钟后的3时30分左右抱憾沉没于大东沟冰冷的黄海海水之中——从那一刻起,国人记住了这艘军舰的名字叫“致远”、她的舰长叫邓世昌、还有一条在最后时刻试图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阳”。
一百多年的岁月过去,“致远”舰、邓世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犹以五十年代拍摄的电影《甲午风云》中塑造的邓世昌形象最为深入人心。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邓世昌是英雄: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一个叫林廉藩的退役台湾海军将军来到威海。自此,这个公认的为方伯谦翻案的急先锋就得意的到处散布:
他已建议威海市政府拆除当时已经树立了十年的邓世昌铜像,原因是邓世昌驾舰冲向吉野等日舰的行为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典型的蛮干,更不配称为“民族英雄”,在他看来:方伯谦“牵乱队伍、临阵脱逃、撞沉友舰”的行为那才是“聪明谙练”,至于邓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来形容。
更有甚者,出现了将方伯谦临阵脱逃的责任也归结于邓世昌的“卤莽”,认为正是因为邓世昌毫无意义的“自杀行为”压垮了方伯谦最后一根脆弱的神经,导致他彻底吓破了胆命令“济远”舰转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进一步,将“牵乱队伍”的罪名扣在了邓世昌的头上,称由于“致远”突然离开队伍,导致同小队的“经远”舰最后失去支援,陷入日舰围攻而最终战沉;
“济远”、“广甲”的逃跑亦是看“致远”沉没后的连锁反应而已,所以方伯谦固然有临阵逃脱的责任,可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他,而在邓世昌!仿佛只要邓世昌不“贸然”冲出队列的话,北洋水师后续的一系列不利后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这个逻辑看,邓世昌简直是北洋海军战败大东沟的第一大罪人了。
国防大学教授马骏大校也来推波助澜,在他的新书《晚清军事揭秘》中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邓世昌:大骂邓世昌带狗上舰是违纪行为,要剥下邓世昌“虚伪”的脸皮而后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邓世昌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军舰快被击沉的时候指挥战舰向‘吉野号'撞去。被‘吉野号'的鱼雷击沉。他和他的狗一齐被淹死了。这就怪了,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带着狗来干什么?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们呆的时间还不短。
看来我们的邓世昌将军平时经常在军舰上遛狗了。而且别人都不以为诧,反以为是风雅。不知道现在的******们到哪里开会的时候牵着两条狗去,恐怕官职马上就要丢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里却见怪不怪。(“剥下丁汝昌、邓世昌虚伪的脸皮”、马骏《晚清军事揭秘》P173-174页)
虽说马教授此言是因对海军文化的不了解、不知道猫、狗等动物作为军舰的吉祥物拥有悠久历史而发的随意言论,但是其很显然也受到坊间对邓世昌那些微词的影响,内心对这些指责颇有认同。更由于他国防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论出现在了正式出版的个人著作中,造成的扩散范围就不可谓不广、影响不可谓不大。
目前为止对邓世昌的微词大多空洞无力,找不到任何实证为依托,笔者对此不屑一驳。不过,英勇和卤莽两个词有原则性的区别,所以笔者决定重新梳理一下“致远”舰最后二十分钟的航迹,希望借此勾勒出一个更加真实的邓世昌形象。
当“致远”舰开始她的最后二十分钟航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当时大东沟海战的态势有所了解。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于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在前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中,采用小队乱战战术的北洋海军以“超勇”号撞击巡洋舰沉没、“扬威”号撞击巡洋舰重伤为代价重创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舰,并使日本联合舰队的队型几度出现混乱。
关键的转折点在下午15时10分,日舰“扶桑”号射出一发240毫米炮弹,正中“定远”号没有装甲防护的舰首军医院处,弹头内填充的下濑火药引发了熊熊烈火,浓烟遮蔽了两个双联装305毫米主炮炮台的视线,严重影响了“定远”的还击能力,“敌舰‘定远’亦被我军发射的炮弹击中舰腹(舰体)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出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松岛舰之勇战》)。为了自救,“定远”不得不停止了射击。
趁“定远”还击无力的机会,日舰更是加紧对“定远”倾泻火力:“本队对定远逼进至4000乃至3000米距离,开始极力猛烈射击,其前部的大火火势更烈,黑烟不断喷出,已经出现进退不得的窘状。”“著名的东洋第一坚舰‘定远’号舰腹被击中,似遭到了大破坏,失去了自由运转的能力,其舰速大大减慢。
此时,我舰队前方各舰(第一游击队的四艘巡洋舰)见是敌军旗舰,不失时机地奔驰而来,一齐向‘定远’进逼,猛烈发炮。‘定远’舰舰内起火,火焰弥漫了半边天空。‘定远’舰上人员皆停止了发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势猛烈,没有被扑灭的迹象——”(《扶桑舰之勇战》)
情势无疑十分危急,纵然“定远”舰拥有厚重的铁甲防护,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让日本人继续攻击下去,“定远”即便不被击沉,也迟早会被烧成一具空壳子。而在这个时候,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受伤起火的“致远”舰冲了出来,和“镇远”舰一起挡在了“定远”舰的前面。
身为铁甲舰的“镇远”好歹皮糙肉厚,面对日本人的弹雨尚能勉强应对;可身为穹甲巡洋舰的“致远”却没有那么结实的身板,在短短数分钟内,没有任何竖甲防护的舰壳很快被日方的弹雨打得百孔千疮。随着大量的海水涌入,舰身开始向右舷倾斜,达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很显然,这样的舰况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虽然“致远”的损管人员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随抽随灌,甚至不能坚持到返航旅顺,军舰必然沉没的命运就此决定。对性格刚烈的管带邓世昌来说,在军舰无可挽救的情况下,白白地沉没显然不是他所要的选择,他的选择是牺牲本舰,与敌舰放手一搏!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远”接下来的行动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伤的“致远”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撞去,希望与这艘日本联合舰队最精锐的舰艇同归于尽,依据是邓世昌在决断的时候曾说“倭船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邓管带有此“击沉‘吉野’”的动机,而当时据称“致远”的炮弹储备业已耗尽,那么不少研究者就想当然的认为“致远”冲出的目的是为了撞沉“吉野”。
参加过海战的洋员马吉芬也宣称:“该舰(指‘致远’)的管带是最为英勇甚至有时有些顽固的邓世昌,他下定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向一艘敌人最大的军舰冲锋,准备实行撞击。”所以在历次表现甲午战争的影视作品中表现的场景都是“致远”勇撞“吉野”的镜头。
不过,笔者认为,仅仅凭借邓世昌要击沉“倭船‘吉野’”,就将“致远”冲向日舰理解为“撞沉”明显有点想当然了。根据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考证:根据北洋海军小队乱战的战术,贴近敌舰近战邓世昌此举应该被解释为尽量逼近敌舰,在本舰油尽灯枯之前向“吉野”等军舰发射鱼雷来达到“同归于尽”的目的。
况且参照“致远”的姊妹舰“靖远”的弹药消耗率,就算邓世昌猛打猛冲,也不大可能出现在激战两个小时后就把数百发大中口径炮弹(致远级军舰约能携带210毫米炮弹150发、150毫米炮弹200发)悉数打光的情形。所以,让邓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无疑还是本舰不可救药的伤情所致。
“致远”向第一游击队发起攻击的全过程被中日双方和第三方所目击,虽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远舰的最后时刻——
日本海军军令部在回复“三景舰”总设计师——法国人白劳易有关甲午海战诸多问题的信函初稿对“致远”舰的最后行程是这么描述的:“午后2时30分许,‘致远’后部起火,3时许,向右舷倾斜,其左舷螺旋桨一半在水面上旋转,仍继续航行,午后3时30分许,向右舷倾覆沉没。”
而在正式稿的回复白劳易函中有所修正:“‘致远’午后2时30分左右起火,3时30分左右明显向右舷倾斜,仍然继续航进,至33分沉没期间,可看到其螺旋桨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转。”虽然时间有数分钟的偏差,但是致远的最后时刻勾勒得十分清楚。
作为当事者,身处第一游击队的“高千穗”号巡洋舰提交的报告则简单得多(一游其余三舰的报告大抵如此):“下午3时25分,2桅1烟囱的敌舰(‘致远’或‘靖远’)向右舷倾斜,仍然继续航进。3时30分沉没。”
之所以如此简单甚至含糊,陈悦先生认为盖是因为第一游击队四舰此刻都在向这艘不要命的中国军舰拼命射击(鉴于日方记录海战爆发前已将鱼雷大部分抛入大海,所以影视作品中日舰向“致远”发射鱼雷的场面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倾泻的弹药甚为密集,下濑火药激起了大量黄色的瓦斯烟雾显然阻碍了战场的能见度,以至于第一游击队的四艘巡洋舰都未能目睹“致远”舰沉没的清晰过程。
在北洋海军方面,在“定远”上的洋员汉纳根目睹了“致远”冲击的全过程,在战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致远’与‘经远’全力冲向日本游击队,此辈可谓勇敢,其行为可谓锐意果断。‘致远’号计划对敌舰进行近战,‘经远’号亦然,此二舰真不愧为姊妹舰。然而尚未抵达日本(第一)游击队,因遭日方舷炮猛烈射击,‘致远’沉没,‘经远’燃起大火。”
身处“镇远”舰上的洋员马吉芬的描述则更为详尽、更富有感情、甚至还带一点美国人惯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夸张:“由于我方的机动能力较差而造成了队型的混乱,在此期间,‘致远’穿过我舰舰尾与‘来远’等右翼幸存舰艇会合。‘平远’与‘广丙’现在已加入战斗,威胁着‘赤城’与‘西京丸’。
‘松岛’号挂出信号,于是第一游击队向处于危险状况下的2艘军舰运动以掩护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致远’号英勇地,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卤莽地向第一游击队的阵列冲去……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无人能确知,但显然它被1枚重炮弹——大约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线。
总之不管怎样,它开始严重倾斜,显然是受到了重创……一阵重炮和机关炮弹的弹幕扫过他的军舰,倾斜更加严重了,就在即将撞上敌舰之际,他的船倾覆了,军舰从舰首开始下沉,舰体随着沉没逐渐右倾,而它的螺旋桨还在空中转动。所有舰员与舰同沉……”(《Yankee of the Yalu》 E.P.Dutton & Co.,Inc.1968)
除了双方之外,身为第三方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船员詹姆斯-艾伦在海岸的高山上也目击了“致远”从冲锋到沉没的全过程:“在后来的战斗中,中国的另一艘最好的舰只‘致远’也遭到不幸。它显然是在长时间内遇到困难,不断用抽水机奋力抽水,因为我们看到水从该舰的两侧流入海。
它英勇战斗,得不到援助;它甲板上的大炮和舰首的大炮不停地射击,直到它沉没为止。最后,它的船首完全淹没在海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那转动的螺旋桨,渐渐地沉没在海中。”(“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续编)
众多的目击记录将“致远”的最后航程勾勒得血肉丰满,这已然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存在。因此,标新立异者们没有能力否认邓大人的这一行为,所以只能从勇气的另一个极端莽撞来挑毛病。那么,从当时的战场情形看,邓大人以下“致远”舰官兵的行为到底是英勇还是卤莽?
孰为英雄?孰为莽夫?
“卤莽”,从词义上解释为:说话做事不经过考虑,行事轻率。而在大东沟海战中“致远”早在14时30分左右已经中弹起火,15时10分掩护“定远”更受了不可挽救的重创。邓世昌并非在军舰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为呈匹夫之勇贸然冲向日舰,而是在军舰已经无法挽救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更加英勇、壮烈的死法而已。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身为军人,当以战死沙场为最高荣誉。为了本方能获得最终的胜利或者脱困而自我牺牲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不乏比邓世昌更“卤莽”、更“不自量力”的存在。
智利海军的普拉特舰长指挥老旧的、机帆并用的木壳炮舰“埃斯梅拉达”号面对远比它强大的秘鲁铁甲舰“胡阿斯卡”号毫不畏惧,与之进行了一场英勇却毫无悬念的战斗,普拉特舰长本人阵亡于向“胡阿斯卡”号发起的跳帮作战中,老朽的“埃斯梅拉达”号最终也被“胡阿斯卡”号击沉。
但是该舰和普拉特舰长的牺牲在赢得了对手尊敬的同时让孔德尔舰长指挥的僚舰“科瓦东加”号免于秘鲁铁甲舰的灭顶之灾。因为普拉特舰长的勇敢,他成了智利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普拉特舰长”成了智利海军传承至今的英雄舰名,他在发起跳帮作战之前的最后遗言“Al abordaje muchachos”(西班牙语“跟我来,小伙子们”)也成了智利海军高昂的战斗意志的写照;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萤火虫”号舰长杰拉德-鲁普少校面对吨位六倍于本舰的德国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自知无路可退,遂破釜沉舟地以全速向德舰撞击后沉没。
该舰的勇敢精神甚至感动了“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舰长海耶上校,在下令全力救起三十一名“萤火虫”号幸存官兵的同时破天荒地通过红十字会建议英国方面授予鲁普少校英国军人的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HX.
84护航船队唯一的护航舰艇,由商船改装而来的辅助巡洋舰“贾维斯湾”号遭遇了强大的德国装甲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后为了保护身后的近四十艘商船的安全,这艘弱小的辅助巡洋舰在舰长费根海军上校的指挥下拼尽全力地冲向这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以“贾维斯湾”号的牺牲挽救了HX.
84护航船队的大部分商船(最后只有五艘商船被“舍尔海军上将”号击沉),更是赢得了商船海员对英国皇家海军的信任,费根上校也毫无疑问的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些失败的“卤莽”之人获得的是对手的尊重、本国的最高荣誉和本国民众的敬仰,那某些好事之人又有什么理由去对邓世昌的“卤莽”说三道四呢?
那么,林廉藩所认为的“聪明谙练”在海战史上的类似表现一般会是什么后果呢?除了那个在大东沟海战中满场乱跑的“黄鼠狼”方伯谦(用一个时髦词形容就是“方跑跑”),PQ-17护航船队在得知恐怖的德舰“提尔皮茨”号出动的情报后,护航舰艇不战而逃,撇下了三十七艘无助的商船遭受德国飞机和潜艇的立体式屠杀,这一跑不但让二十四艘商船沉入冰冷的北冰洋,更是让“贾维斯湾”号的牺牲换来的海员对海军的信任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可以说,此战不但损失惨重,而且影响恶劣。
写到这里笔者觉得到了收笔的时候了,即便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海军,也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即便最终力量不济而战败,也没有理由被唾弃!在危机时刻向敌人发起决死突击的邓世昌是“英雄”还是“莽夫”,想必此时此刻各位读者心里应该有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