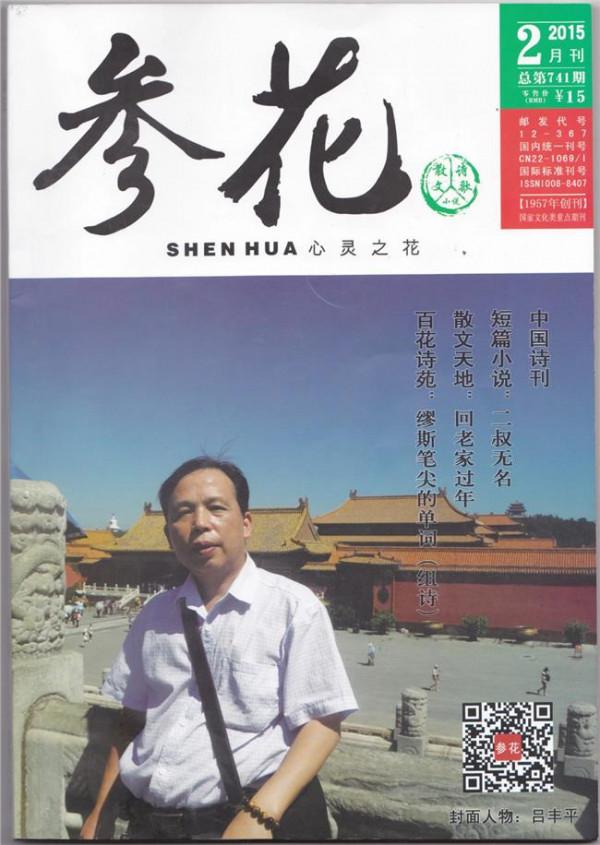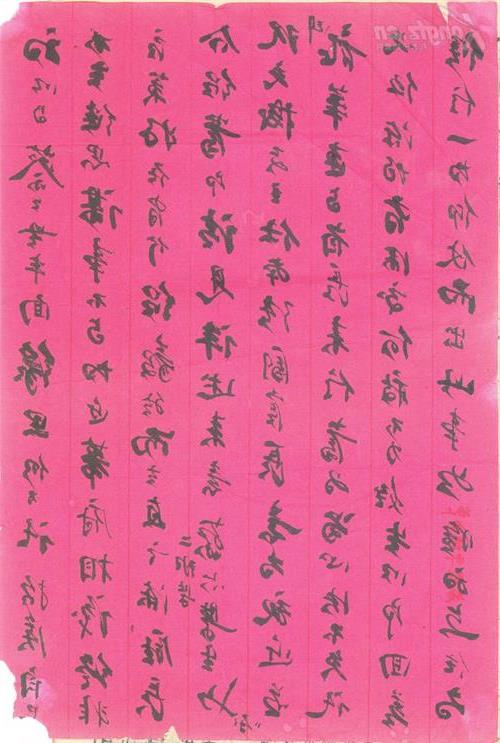赵烈文语录 读曾国藩与赵烈文私人谈话录
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有一部《能静居日记》,不仅记录了当时大量重要人物与著名历史事件,而且记录了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大量私下谈话。通过他们的交谈,不仅可以走进曾国藩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窥探和触摸他的内心世界,更可以认识和了解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曾国藩,是了解曾国藩和他那个时代的绝好信息,其他任何材料包括曾国藩家书和日记都无法替代。
他们具体谈了什么呢?因《能静居日记》篇幅实在太多,内容实在太丰富,断难一一介绍,所以只能做个大致归类,并择其要者而言之。本文辑录的,主要是他们两人谈论学问文章方面的内容。
一、著书立说必须“采铜于山”
不管做学问,还是写文章,曾国藩有一个显明观点,就是必须坚持原创精神。文章写不出新意,不如不写;做学问没有自己的观点,不如不做,否则会把自己降格为抄写员,而成不了学者和作家。另外曾国藩还认为,著书立说都由点滴积累而成,没有丰厚积累,最终不能成为大家。这些都是千古至论。
怎么才能坚持原创精神呢?赵烈文做了很好的补充。他认为,写文章也好,做学问也好,都必须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要像顾炎武先生那样“采铜于山”。所谓“采铜于山”,就是写书也像铸钱一样,必须亲自到野外把铜矿石采回来提炼原料,而不能买旧钱当废铜铸钱。
买旧钱当废铜铸出来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了,岂不两失?《日知录》就是顾炎武“采铜于山”铸造的杰作。正因如此,所以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书还在不断重印,而那些买旧钱翻铸的粗恶东西早就被历史淘汰了。
原 文
下午谒帅久谭,帅方患喉疾……
今日帅言:“学问之道,必当心有所得,著书之法,必当未经人道。近世儒者,掇食陈文,复无分别条理,是抄胥耳,不如饱食高卧之为愈矣。”此言即亭林先生所云采铜于山之说。——同治元年二月四日《能静居日记》
涤师来久谭,言:“古均(古同‘韵’)之说,亭林先生首创,而字之音读一一印证,后人虽加至十三、十七、十九、二十一部,不为无见,然总不能出其范围。譬广厦已成,徒就其中分隔间架,不足以云缔构明矣。”论至公允。
又言:“著书须成片段,否则一知半解,终不能为大成。然说经又只能就己见之奇创者存之,若章解句说,必蹈前人牙慧,是抄胥耳。”
又言:“朱子大儒,然未必能做事。”
余言:“朱子系立言之人。立言、立功本是二辙,兼之者鲜。故其身虽不用,而至明祖其说即大行,以迄本朝典章制度,莫不原本朱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即王佐才也。”
余又言:“士生二、三千年后,去古太远,中间作者不可胜数,往往得一创说,而阅古人文集,辄已先道。故虽亭林先生自言采铜于山,尚不能十成把稳,况余人乎?”——同治六年五月四日《能静居日记》
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同治六年五月六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赵烈文向他请教《仪礼》中为什么多有觐飨之仪,曾国藩马上老实承认自己解释不了。
其实要回答赵烈文的疑问并不难。
作为主要记载士大夫之间礼仪的《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一本汇集,由于出书时间早(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成书于秦统一六国之前,但赵烈文看到的是黄刻宋本《仪礼》——笔者注),在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又非常多,久而久之,在某个版本中间杂着一些君臣之间的礼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曾国藩就是要实打实地回答说不知道,绝不不懂装懂、误人误己,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天的闲谈中,曾国藩还对魏源的著作主动加以评论。他认为魏著《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不完美,写得最好的是《圣武记》,文集最差。
但赵烈文没有接过这一话头。当天的谈话于是戛然而止。
是赵烈文没有读过魏源的著作不敢置喙,还是对曾国藩的评论不予认同,但又不好驳老师的面子?
后一点显然不是赵氏风格,完全可以排除。
笔者认真查阅《能静居日记》后,证实笔者的判断果然不谬。
在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日的日记里,赵烈文虽曾将《诗古微》列为待访书目,但此后并没有阅读方面的记录;《书古微》和《魏源文集》更是没有出现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只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古微堂诗》,时间分别是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和光绪二年(1876)七月二十一日。
他对《古微堂诗》评价极高,称之为“有韵之文,非复诗格。历境虽多,而以奇肆为擅长,射可穿札,力能屈铁,从来骚坛无此龙象。”读《圣武记》时,赵烈文做了约五百字读书笔记,也是比较欣赏的。
两人对《圣武记》的看法既然一样,曾国藩提到的魏氏其他几种著作赵烈文又没有读过,他当然不会接话了。这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表现吧!
笔者言犹未尽,还想说几句不算题外的题外话。
作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因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便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许多人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和《书古微》两书中,他不仅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而且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
他还觉得古文《尚书》是否存在都值得大大怀疑,“六经”更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魏源摆脱“章解句说”而直求经文,并以微言大义为经术政事理论张本的治学方式,按理说与前文写到的曾氏观点不谋而合,曾国藩怎么会觉得魏氏的《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不完美呢?因笔者学识有限,所以不得而知。
但曾国藩充分肯定魏氏的《圣武记》一书,笔者就能完全理解。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痛心疾首的魏源希望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同时也是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国人抗击强敌的士气,于是发愤撰写了《圣武记》一书并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通过叙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来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进行对照,用意可谓相当良苦。
对这样的感愤时事又不乏实用之作,讲究实用又具有强烈报国情怀的曾国藩当然欣赏有加了。
原 文
亭午,涤师复来谭,余询《仪礼》称士礼,而觐飨之仪杂出,何故?
师言:“此说不能解。”
又言:“魏默深诗、书古微皆不尽善,其著作当推《圣武记》,文集为最下云云。”——同治六年五月六日《能静居日记》
三、方苞的《望溪集》特别让人读不下去
对同一位作者的不同作品有喜欢和不喜欢,对于不同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自然更有喜欢和不喜欢。比如对桐城派两位散文名家姚鼐和方苞,曾国藩和赵烈文便都喜欢前者而鄙薄后者。他们对方苞写的墓志铭尤其有看法,说好似官府出具的履历证明材料,一点读头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二日赵烈文第一次读《望溪集》时,曾写下一段《读后感》,说:方苞给人写墓碑文章,常常不相信死者家属提供的材料,落笔时于是俱为疑惑不定之辞。赵烈文对此非常不理解,感叹说:人家请方苞为先人写墓志铭,无非是借重他的文名,方苞行文时却不相信死者家属的说法,写出来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写谀墓虚文固然可耻,但像官府出具履历证明材料一样写墓志铭,也是非常可笑的。
可见赵烈文对方苞的墓碑文章十分看不惯。
原 文
涤师来久谭,见余题子密藏册诗极赏叹,因言:“今人作诗宜法韩、苏,则才气易展,盖排奡不受束缚,则习气鲜也。”又言:“本朝古文当首推姬传先生。”
余言:“《望溪集》文既平衍,而理尤沾滞,殊不令人喜看。其与人作志铭如州县取保状,尤可笑。”
师亦云然。——同治六年五月十日《能静居日记》
四、谦虚中有自信,自信中有谦虚
说曾国藩是一个谦虚的人,肯定会得到不少人认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与赵烈文谈天说地时,他有时也会表现出相当自信的一面,如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与赵烈文聊天时,曾国藩就毫不谦虚地说出了这种大话:“现在我常常反问自己,在古代诗人中,如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人,也不敢谦让多少,但总是没有闲暇,不能用笔墨抒写出来。
平生只有这件事,心中未免感到遗憾。”可能是赵烈文难得见老师这么张狂,于是马上建议他编辑出版自己的文集,曾国藩却又谦虚起来,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真是谦虚中有自信,自信中有谦虚。
原 文
师又云:“人生无论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足下胸襟大过于人,盍善抒其性灵,弗为尘土所淹没。”
余曰:“诚然。观人之事,不如观人之言,故古史记言多于记动。降至《史》、《汉》,犹知其义,纪、传中多描写人之声音笑貌,遂使千载之下,几无遁影,所以足称良史。师曷不以平生所撰示人,俾如余辈早为结集,否则千载以形迹相求,失公之神矣。”
师逊言:“无所有。”——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能静居日记》
五、没有成为文章学问家是曾国藩的终身遗憾
曾国藩不仅对自己的诗歌天赋很自信,而且在散文写作方面,也有相同的自许。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曾国藩到赵烈文处久谈时,就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曾国藩一生勤于学习,刻苦钻研,不仅年轻时如此,而且其后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时,也从未停止学习。曾国藩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博得了后人相当高的评价。尤其是他写的公文,既平实简练、情理交融,又能与实际相结合,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不少人仿效的榜样。
例如咸丰四年曾国藩督湘军自衡州出动,迎战太平军时发布的檄文《讨粤匪檄》,虽只一千余字,却一气呵成,气势磅礴,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政策讲得明明白白,可谓文理兼优。
还有后来他写的奏折、书缄无不美妙绝伦,读后令人难忘。只是身陷官场,迷恋政治,曾国藩才不能继续他的文人事业,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和遗憾。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曾国藩逝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还如此写道:“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原 文
下午,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今日复番视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者之见,客气多耳。然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
六、士气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带兵打仗的统帅,曾国藩和赵烈文闲谈时,当然少不了探讨军事理论。如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曾国藩一开口就说起了兵事。
从曾国藩和赵烈文这番谈话里,读者会有趣发现,对于战争中武器与人的关系,曾国藩和赵烈文都认为人是第一位的。而在人的问题上,他们又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士兵的斗志和将领的谋略作用不可忽视,认为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他们的军事思想,不仅与《孙子兵法》中的“攻心伐谋”思想相暗合,而且对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就怪不得毛泽东会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了。
原 文
下午复入内谭。
师论兵事,言:“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
余云:“言兵事归之于气,至矣,而气又根之于心。故偶然之成败,损益甚微,而谋定之战,一失算即将馁于上,士馁于下。何则?其心已夺,而气不得不馁也。兵志所云,攻心伐谋,又曰折冲于樽俎,皆武之精至者也。”——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能静居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