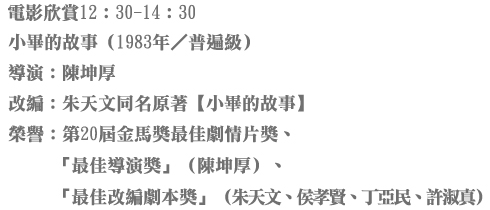朱天文眷村 朱天文笔下的眷村书写研究
朱天文对父辈的书写脱离了宏大历史叙事,更多的是从人性角度来反思个体在大历史变动时期的无奈感。如父亲和母亲极具传奇色彩的逃婚真实地反映了作为国民党下层军官在台所遭遇的尴尬命运。初来台湾时,很多老兵在大陆已有妻小,他们原本以为在台湾只是暂时的停靠,但遥遥无期的回乡路最终蜕变为望断天涯的不归路。
归期无望后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个人实际问题,而本省女子在当时又不允许和这些老兵结合。故而在关于“老兵”的书写中,就出现了一些年近中年但仍未成家的变态者,以及本省女子和外省军人“私奔”的传奇故事。
父辈面对归乡无望的现实,能做的只是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调整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压力,甚至通过宗教的力量来淡化历史留给个体的伤痛。
朱天文曾为父辈当初的选择感到不解,为父辈们的逐渐被疏离感到不平,进而在书写中,对于父亲生前的描绘尽量用平和且生活化的语言,用冷静的客观态度来讲述平凡的家族故事。在父亲逝世后,朱氏姐妹面对父亲角色的缺失,面对父亲在岛内所遭遇的不公平,她们的怨怼之气则难以抑制。
朱天文在《童年往事》中,通过阿哈父亲在死时留下的自传文字表达了相似的情感倾向: “初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计划住三四年就要回去的,所以不愿意买家具,暂时只买一些竹器,竹床竹椅竹桌,打算走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丢掉不要了。
”而阿哈的祖母,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她每天都叫阿哈吃饭,却经常迷路; 她讨厌所居住的日式榻榻米的宿舍,人们像小兽一般爬来爬去; 她很怀念家乡的那张雕镂着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栏杆木床,感觉恍如昨日; 她不时神秘地拎着包裹让阿哈陪她回大陆; 在阿哈考上凤山中学之际,她迫不及待地要阿哈回大陆拜祖先祠堂……这里时空的交错重叠,让人芜杂莫辨。
事实上,对家族命运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对“原乡”追寻的终极关怀。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关于个体家族的历史追寻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反思和赢取未来希望的决心。这种家族书写中的漂泊和无依感正契合了上世纪80、90 年代台湾社会的现实,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整体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对家族存在的书写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二、对眷村生活的二度回望
朱天文的创作中也有对眷村的二度回望。眷村作为作家童年生活的故乡,由于其特殊的封闭性导致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被压抑而急于逃离的心态。然而离开眷村后,面对即将到来的眷村拆迁和后现代情境下都市生活的异化,朱氏姐妹也感到极度的焦虑和惶恐,因而又开始怀念起那特有的以“眷村文化”为载体的“浓浓的眷村味儿”。
这种宣扬“敬老爱幼,善尽睦邻”之责的传统文化,在离乱逆境中相携支持的温馨情谊,形塑了眷村子弟热爱生活、乐于助人、勇敢上进的品格及子承父业、报效国家的自诩与精神。
朱天文小说《伊甸不再》讲述了名叫甄素兰的眷村女子逃离眷村在都市堕落而最终自杀的故事。小说第一部分“甄素兰”讲述甄素兰在眷村时期的生活。当时的眷村弥漫着令人烦躁和压抑的气氛。甄素兰的母亲整天穿着一袭布袋装行走在村子的大马路上,她由于素兰的父亲风流成性而患上精神分裂症。
素兰的父亲高大帅气风流但对家庭极端的不负责任。书中叙述: “父亲和母亲终日吵架,家里冷锅冷灶,衣服没人洗,后院的蔷薇花给霸王草淹没了”。姐姐生活在完全没有自我的世界里,弟弟像父亲一样的成长。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极度的压抑和不安。而这种现象却是当时眷村生活的真实存在。
《风柜来的人》中的青年颜涣清也忍受不了家中沉闷而压抑的气氛选择离开村子。他受不了父亲终日躺在椅子上,母亲疲惫地操劳,而自己又无所事事靠打弹子看电影打发日子。尽管因为后来与人发生争执而被迫离开,但此前的厌倦之意已非常明显。
正如朱天文所感慨的那样: “她所熟悉的兄弟姊妹们,基于各种奇怪难言的原因,没有一人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书念得好的,家里也愿意借债支持的就出国深造,念不出的就用跑船的方式离开; 大女孩子念不来书的,拜越战之赐,好多嫁了美军得以出国。
”眷村子弟幼年时对眷村的挚爱多半来自父辈口耳相传的被夸大了的家族故事和传说,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父辈关于“大中华”的传说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
颜涣清这种成长期所表现出的茫然不知所措,其实也是眷村青年青春叛逆时期的一种表征,他们渴望逃离家庭在社会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但现实的残酷又使他们懵懵懂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故而产生低迷、茫然、无助、失望但仍掺杂着希望的复杂的心理体验。
三、成长题材的眷村书写
以眷村为背景的成长小说也是朱氏创作中的优秀之作。朱天文最开始走上文坛,亦是从其带有自传性质的青春小说开始。她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里面交织着主人公青春期的叛逆和单纯,以及渴望融入社会的迫切愿望。她笔下众多成长期的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动后在行为和性格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大多是朝着向善、符合社会传统道德所规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