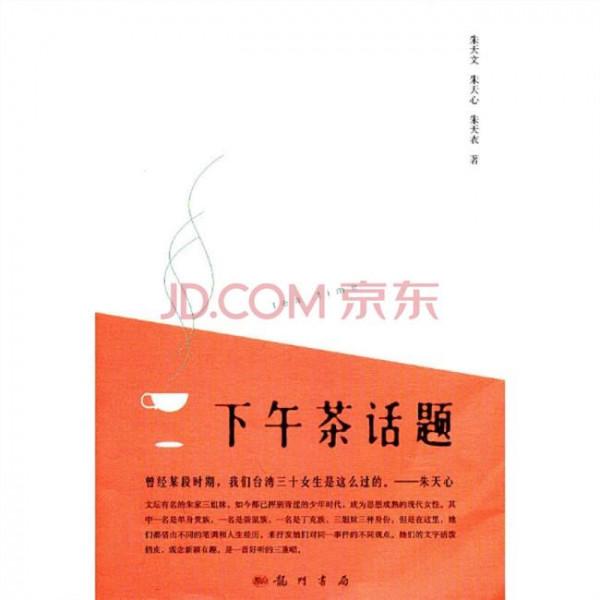朱天文天涯 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小说家族走出的三姐妹
随着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作品,以及朱天心的《击壤歌》近期在大陆的出版,这对姐妹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关注。其实,朱家还有一个小妹朱天衣。在台湾,朱家三姐妹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她们独特的家学,一家人充满文学追求的生活情趣与品味,与胡兰成的师承关系,以及她们在台湾文学、影视上的成就,无一不让人津津乐道。
成长在书堆中 朱氏三姐妹出生在眷村,那艰苦的岁月,却为她们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台湾的空气总是潮呼呼的,头发一下就湿成条贴在脸上。1949年,朱西宁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他祖籍山东,曾出任国民党陆军上尉、上校参谋。朱西宁到达台湾后住在眷村――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的聚居区,并在这里认识了妻子刘慕沙,生下了3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
朱家所住的眷村和所有眷村一样,全村共用一部电话,纳凉的老人摇着蒲扇,打着赤脚的孩子在毒辣的太阳下抽打陀螺,还有人支起炉子,剥了蛇皮煮蛇汤……在这一幕幕眷村最常见的景象中,1956年的夏天,朱天文出生了。
朱天文幼时爱哭闹,每日都要父母轮流哄抱。轮到朱西宁,便把朱天文放在床上劝她不要哭:“我们商量一下好罢,咱们都是见过世面的……”朱天文的哭声仍穿过用棍子支起的木窗,传到屋外的篱笆上。
两年后,朱天心出生,然后是朱天衣。朱家狭小的房间里有一张竹床,客厅兼作饭间,里面摆着一张用炮弹箱改成的饭桌。
三姐妹就在这里长大。 朱西宁除在军中任职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作家身份。朱西宁是台北文坛的领袖之一,妻子刘幕沙是翻译家,尤以翻译日本文学名家作品闻名。这对夫妇并不宽敞的家里几乎成了“朱家沙龙”,文人穿梭往返其中。
朱氏三姐妹自幼便在书堆里自在长大,耳濡目染、所见所闻的,都是做文章的人和做文章的事。 到了夏天,屋内闷热,朱西宁便将灯泡牵到屋外,藤椅扶手上架块洗衣板便开始写作。儿时,朱天文最爱读父亲的小说,晚上迷迷糊糊地睡在蚊帐里,总看到父亲伏在灯前写稿。
朱天文最喜欢的时刻是父亲抱着她背诵《古诗十九首》和《琵琶行》,等再长大一点,她便开始给妹妹朱天心讲故事。 台风带来的下雨天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幸福时刻,父母在家中整理以前的信件,两人一面回忆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一面简单地打发了午餐。
一家人围坐在烘有尿布的火炉边,刘幕沙大声地朗读朱西宁的小说。妈妈的声音、爸爸的小说和门外的雨声成了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
和其他眷村小孩一样,三姐妹最不理解清明节。这一天,她们看着本省人带着贡品在祖先坟前举行祭拜仪式。可眷村的人是在自家后院烧纸钱,由于不知道家乡人生死下落,纸钱上不能确切写明烧给谁,只能烧作一堆。
多年后,朱天心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们》中写道:“曾认真回想并思索,的确为什么他们(眷村子弟)没有将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 那时三姐妹并不明白大人的情绪,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
多年后,他们一家搬出眷村,姐妹们相继长大,大多眷村已不复存在,姐妹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眷村,眷村已成了她们的一部分。朱天文因写一位眷村男孩小毕的故事结识侯孝贤,朱天心所写《想我的眷村兄弟们》表达了“可不可以我不认同这里、讨厌这里,但我还是可以住在这里”的心情,道出无数外省人心中的迷茫。
这部作品获奖无数,她对在台湾的外省人的关注延续到今天,成为她心中不散的乡愁。
朱家的放羊式教育 朱天衣的丈夫谢材俊曾说:“即使是至亲父女而且同业??情感深厚杳远(这一点我至今视为奇迹),且晚饭桌上无话不谈……” 虽然家中藏书甚多,但父亲并不刻意要求三姐妹读书,只任她们随意翻读。
如今朱天文回忆起父母时说:“父母不管你,也没有让你写东西,不理你的课业,也不叫我们去上补习班,总之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高一暑假,在家里没事干的朱天文写了处女作《强说的愁》,开始四处投稿,且一投就中。
朱家爱养宠物,在眷村,其他妈妈都在做手工补贴家用,而刘幕沙则养了一大堆不事生产的猫狗。三姐妹的饭盒带回家,刘幕沙先给狗舔一舔再洗,以致饭盒上常有狗啃的痕迹,姐妹们常气得要翻脸。
刘幕沙时常感叹自己是位失格的妈妈,说自己养女儿像是放羊,女儿的裙子破了也注意不到,朱天心只好用订书机把裙子订起来才能去上学。平时刘幕沙骑着单车接女儿放学,遇上下坡的路便大叫:“冲啊!
”就是这位天性活泼善感的朱太太,用自己翻译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稿费喂饱了全家人,还有一群猫狗。 大姐朱天文像爸爸朱西宁,待人宽容。二妹朱天心嫉恶如仇,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待人。
七十多岁的刘幕沙现在仍在写稿,偶尔看看电视,朱天心便鞭策妈妈要做得更好。小妹天衣最像妈妈,一样迷糊又无厘头,保持了对生命原始的热爱。本与两位姐姐一样从事文学创作,但中途改去唱歌、学京剧,后来教小朋友写作,一教二十年,收入贡献给朱家人最关爱的流浪狗。
她现在最爱做的事是回家陪妈妈牵手逛菜场,以及带着使命感做出好吃的食物,喂饱全家人。在朱天衣心中,写作是一生志愿,得用生活、生命来供养,两位姐姐都是,但她没有办法做到。
她甚至叛逆地想:“为什么我要走一样的路?” 大陆作家阿城曾说:“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 刘幕沙、朱天文和朱天心现在仍笔耕不辍。朱天文每日将自己关在书房穿着睡衣在书桌前写作阅读。三十年间,家人很少踏足她的书房,每次进去不超过二十秒。朱天心及丈夫唐诺在一间便宜的咖啡馆中,每日朝九晚五写足8小时。
至今刘幕沙仍和朱天文以及朱天心住在一起。刘慕沙常在入夜后到屋后走,望着每个房间灯光里埋首创作的剪影,只觉真是气势很旺的一座“小说车间”。 师从胡兰成 胡兰成的出现让朱氏一家从“张迷”集体变成胡兰成的粉丝。
朱西宁酷爱张爱玲的小说,并时常与她通信。在他的影响下,一家子着了魔似的,全都是“张迷”。他所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部分,98位中国现代小说家,张爱玲排在第一位,他用“万古常空,一朝风月”表达对这位女作家的崇敬。
直到有一天朱西宁听说胡兰成来台教书,为了写张爱玲的传记,他便登门拜访。 当时朱天文心想,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她便随父亲登门拜访胡兰成,但真见到了,朱天文心里却一片茫然。
当日朱西宁随身带着一瓶竹叶青作为见面礼,两人交谈甚欢,胡兰成回赠朱天文一枚日本包袱,并夸耀说,这包袱本有两枚,一枚送与日本一位显赫的官员,另一枚赠与天文小姐。
朱天文看着不说话。拜访完后,朱西宁异常澎湃,写信给张爱玲,殷殷报知见面经过,作热心调解人,盼望张爱玲若来台湾可以和胡兰成重聚。张爱玲很长时间后才回了一封信,希望朱西宁不要写她的传记,并未提及胡兰成,自此书信遂断。
而见过胡兰成的朱天文写信给朋友说非常失望,“那显官又与我什么相干!”还说胡兰成脸上没有张爱玲所描写的特征。等到一年后,朱天文顺手之间抄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看之下竟欲罢不能。
后来,朱天文评价胡兰成说:“先生将世间什么大事情拿到手上,全是闲情逸致,即与张爱玲断绝,亦只出去走了一遭,回来继续写《山河岁月》,怎么能够,叫人很气愤,又奈何不得,只好大哭一场。”又说:“张爱玲的文字好,然先生的感染力大。”
人们的确可以在朱天文早期的短篇小说里读到如张爱玲般的苍凉感,这点其实也贯穿在了其后来的全部作品里。比起朱天心,朱天文的心是冷冷的,而某种相似的城市书写状态,也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朱家姐妹与张爱玲相联,早期三姐妹一度被人们定义为闺阁作家。
回看朱天文较早的小说集《乔太守新记》、《传说》;散文集《淡江记》等,都是清新的校园风,也都是那个年纪的她所能感受、经历到的种种情感体验。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胡兰成。
与其说胡兰成带给朱氏姐妹知识,倒不如说带给她们的是志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的这句诗曾被朱天文拿来讲与胡兰成的这段相识,“虽然你眼前在做一件很小的事,但心胸却望得远远的,望向天空的尽头。我想这样的视野是胡兰成留给我们的最大资产。
”与胡兰成结识后,朱天文的作品里多了另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就是志气。 大概还是王德威,最先把朱天心描绘成“老灵魂”,意思是她年纪轻轻已经喜欢思考一些终极的事情。朱天心对现世有种难以割舍的关心和愤怒。
正如阿城说道:“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有一种强悍的敏感。”朱天心用小说记录所看到的更为残酷的世界,显露出对于台湾社会大环境的焦虑和思考。 但是,朱天文难道就不是“老灵魂”么?27岁为再版的《乔太守新记》写序时,她就感叹说,花是会凋谢的,人也要老的。
而这种前文所提及的苍凉感,在她之后的作品里,被一再体现。姑且把《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算成是她的近作吧。
这样说真是勉强,因为前两本书的写就,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巫言》朱天文写了8年,《荒人手记》与《世纪末的华丽》中间也隔了4年。之所以把这3本书划归到一起,是因为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胡兰成曾经打算写一本叫《女人论》的书,从女娲写起,打算写到林黛玉、晴雯以及民国诸女子,谁知写了个开头他就去世了。
那时朱天文便发愿,“总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论》续完。”文学评论家黄树森在1996年时就敏锐地观察到,《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里都是朱天文的末世情结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也是对胡兰成《女人论》的回应。
只是他恐怕没想到,这之后又有了《巫言》,这是朱天文自己也没想到的。 在《荒人手记》的最后一页里,朱天文写道,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
而《巫言》同时也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这本在不少读者看来很有阅读挑战的一本书,早已不再是年轻时一味讲故事的朱天文,里面技巧性,里面的镜像化,里面的高密度,里面努力要用自己作品举起自己的试验壮举,都是让人叹畏的。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唐诺搬出的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搬卡尔维诺出来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去拿此对二人做比较,而是拜托大家,真的不要每次提及朱天文,都还要再提张爱玲罢了。
在今年4月号的《印刻》杂志上,朱天文洋洋洒洒写下的散文《愿未央》,是目前可见的她的最新作品。这篇回忆胡兰成的散文,被杂志主编初安民认为是台湾近十年里最好的一篇散文。
里面的一句话大概也是对朱天文今后创作的一种期许。她说,志不尽,愿未央,天下事犹未晚也。而朱天心说:“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
但我觉得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现在朱天心正在准备写台湾几十年间的剧烈动荡,她说:“这个题材没写完,就不能退休。” ■ 朱天文近期出版作品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 (2010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传说》是朱天文早年作品,收有朱天文的成名作《乔太守新记》;《炎夏之都》中朱天文童年记忆、家族往事、父辈的家国之思跃然纸上;《世纪末的华丽》中的同名作品是朱天文的代表作;而散文集《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中,收录了朱天文30年间的60篇代表作品。
《荒人手记》 (2009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4年,朱天文创作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一举夺得台湾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首奖。
告别了少女青涩的朱天文,以这部小说跻身台湾文学大家之列。在《荒人手记》中,朱天文从自己狭小的少女情怀中走出,在这种变化中仍可以寻得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子:敏锐的感官、细腻的分析、极力打磨的文字之美。
这本小说没有主要的故事线索,全以一男性同性恋者的口吻,倾诉这一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 《巫言》 (200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天文用了博物志式的写作方法。
小说繁复庞杂,语言密度很大,其中贯穿各种“冷知识”:牛仔裤设计史、一级方程式赛车、电子舞曲……如朱天文所说:“我着迷于官能物质世界,对于每一种细节都有天生的敏感和了解的欲望”。
《巫言》发表后在台湾引发了“小说为何物”的争议。 朱天心近期出版作品 《击壤歌》 (2010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风起时我又会有大志”。30多年前,大多数台湾的文学青年都能背诵这个句子,它出自朱天心的《击壤歌》,当时风靡台湾校园,头一年重版十余次。
头五年在台湾销售30万册,至今仍年年再版。连老师胡兰成也说,天心是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晃晃。与姐姐一样写校园题材,但在朱天心笔下,却让人感受到未来的硬气和英气,荡起一股无名的大志。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2010年1月,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这是已步入中年的朱天心关于中年人感情的小说。朱天心坦言选择“中年女子失落的情感”这样的题材是因为毕业30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
她说:“大家看上去都是女强人并自信满满,但不知为何,偶尔也会惶神,像谜一样。”在小说中,女主角因无法接受人到中年所遭遇的感情落差,将丈夫推入河中。朱天心很想了解自己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随着朱家姐妹的作品在大陆陆续出版,近两年大陆读者中,多了不少“朱迷”。 朱天文每日伏案写作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