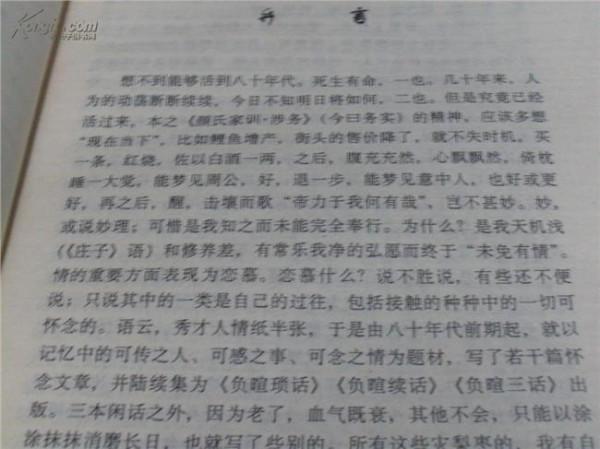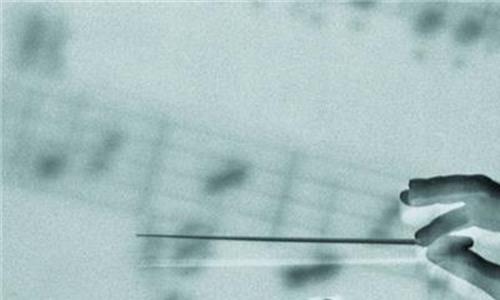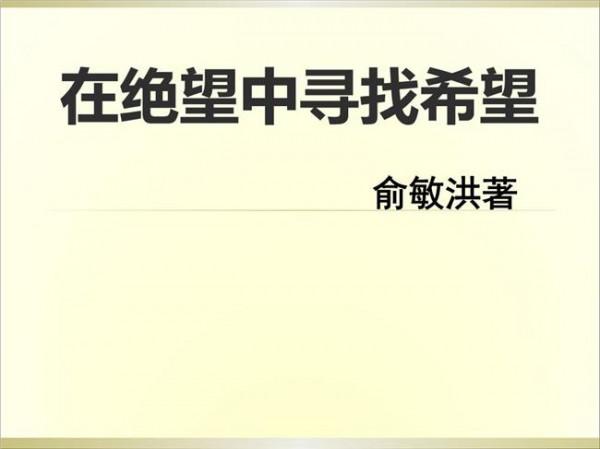张中行的故事 流年碎影中寻找张中行与沙滩的故事
沙滩其实是与古河道有关的地名,大致包括今天五四大街、沙滩前后街到北池子北口等交织而成的一片区域。原本皇城根儿下的这片地方无以名世,但是1898年北大的建立,尤其蔡元培先生“开门办学”的方针实施之后,却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所。
当张中行于1931年进入北大时,北大在沙滩的校区分为三处:红楼的一院、马神庙的二院、北河沿的三院。入校伊始,张中行就和每一处校区都有了瓜葛。瓜葛最深的当然是即将求学的红楼文学院,其次就是在北河沿三院(法学院)住过近一年的男生宿舍。至于马神庙的二院,则只是投考报名和考后发榜的所在,看似瓜葛最浅,却不料,这里恰恰又成为他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此是后话。
对于初入北京的青年张中行来说,沙滩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但随着漫长一生的缓缓吐纳,他熟悉了沙滩的每一处角落。更重要的是,这块地面上曾经过往的男女老少,这里曾有过的悲欣冷暖,在这里流逝的青年、中年、老年段段时光,都伴随着“沙滩”这个地名逐渐渗入了他的精神、气质和血液。于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自有了一片“沙滩”,这是属于张中行的沙滩。
沙滩红楼,是奠定张中行一生学术根基、价值追求和人生信念的地方。在他晚年的绝世文章中,饱含着浓浓的北大情怀,最典型的是红楼“家风”、红楼精神和红楼传统。
余生也晚,当有幸于2000年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位于沙滩后街55号)的时候,我只能听一些年长同事为我描绘先生前几年如何端坐办公室一隅,独自看报的场景。也就是说,直到去世的前几年,行公瘦高颀长的身影还在沙滩一带出没。此时距离他1931年踏入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校门,已是倏忽又七十载了。
《负暄琐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氏怀旧散文的“开山”力作。起首的几篇就是《红楼点滴》(一、二、三),标示着老先生对于自己红楼出身的怀念和自豪。对于红楼的精神,他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自由散漫的一面。用今天的眼光看,老北大教学管理或者是考勤管理不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有时教师上完一学期课竟发现底下听课的没有一个真正选课,都是旁听生。张中行认为,这种随便是老北大不变的“家风”。
其次,北大还有严正的一面。在教师之间、在师生之间,提倡坚持己见,维护真理,维护每个人表达各自见解的权利。与此相应,对任何人的任何思想也都可以表示怀疑和追根问底。张中行对此表述为“红楼的传统”。基于以上两点就有了第三种精神,容忍。“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
关于老北大这些精神内涵,也许今天听起来都已经不新鲜。但真正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和件件琐事,将这种精神生气淋漓地展示给现实社会,张中行是先行者。他的“人文怀旧”散文曾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反响。
北大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说:“80年代后期,张中行出版《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大家都叫好。这好,一半属于张先生的生花妙笔,另一半则应归结为老北大人物的气韵生动。”的确,在红楼求学的四年,张中行获取的不仅仅是一张北大的文凭,更多的是红楼人物、红楼家风、红楼传统所挟带的神韵和气质。在沙滩行走的这段时光,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价值追求和人生信念。
-其实,中国现代史上还有很多赫赫有名者都曾在沙滩一带活动过,如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柔石、曹靖华等。当然,还应加上一个文学虚拟人物———“林道静”。
要说红楼精神中对张中行影响最深的,还应当说是“宽容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有了这样一种修养和气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多年以来,他一直不愿就“余永泽”这个他认为的“文学形象”进行任何辩护。他坚持认为,那是别人小说创作的自由,而非刻意诽谤。同时,在他的众多回忆散文中,对沙滩红楼特有的“宽容”精神情有独钟,着墨尤多。
因为红楼求学环境的“包容和宽松”,导致大量旁听生蜂拥而至。张中行对此表示非常赞许,“有一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了,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校旁听”。
在张中行的北大时代,沙滩一带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开放空间。众多求知若渴的北大“边缘人”在红楼的“宽容”下,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学术理想。他们和张中行等北大“槛内人”一同构建了三十年代沙滩的文化生态。
这也是张中行所真心欣赏的一种宽容的“北大”氛围。他说,在这些“边缘人”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其实,中国现代史上还有很多赫赫有名者都曾在沙滩一带活动过,如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柔石、曹靖华等。
当然,还应加上一个文学虚拟人物———“林道静”。在杨沫创作的小说《青春之歌》中,有过这样的对话,“小俞的脸白了,她以为道静又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故。‘没有什么。’晓燕冷淡地说,‘她在北大旁听呢。’”(青春之歌-第二部三十七章)
林道静这段情节,自然是根源于作者杨沫亲身的生活体验。当张中行在沙滩这个地方遭遇到杨沫,他的一生注定要烙上一道极深的印痕。
-沙滩银闸胡同,是负载张中行和杨沫爱恨恩怨的地方。作为青年时代的初恋情人,张中行和杨沫只在沙滩共同生活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可这五年中的恩怨是非,却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人不断追寻真相的“历史公案”。
如果张中行没有在晚年完成数百万言的学术和散文创作,大多数国人将会遗忘掉他的名字,而只牢牢记住《青春之歌》中杨沫塑造的那个消极形象———“余永泽”。作为青年时代的初恋情人,张中行和杨沫只在沙滩共同生活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可这五年中的恩怨是非,却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人不断追寻真相的“历史公案”。
张中行关于这段往事的简短追忆中,对于沙滩生活的这段时光仅寥寥数语。“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在外面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
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流年碎影———婚事》)张中行笔下的这些儿女情事,平常无奇,使人无法参透其中埋藏着什么解不开的恩怨。
我似乎还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燕园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一起在校园围墙外租住着小平房。自己生火、取暖、做饭,也甜蜜,也争执,也怄气……
于是,在早春的一个午后,我又回到了沙滩。想紧贴着这片我曾经熟悉的土地感悟出一些东西。从喧闹的五四大街我拐进了一条叫“银闸”的曲折胡同,这里老式寂静的院落、悠闲的人物,似乎让岁月也无端慢下了脚步。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银闸人物》一文中,曾介绍,“银闸是北京临近紫禁城东北角的一条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悉的‘沙滩’……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内路南的一个小院落里。
……我住在西屋,大概有两年吧,柴米油盐,喜怒恩怨,大部分化为云烟……”也就是在这篇文字中,我们隐约窥到了一个“妻”的形象。
文章大略是说邻里人物有一些稀见的言行,小夫妻回斗室内描摹回味,窃窃私笑,别有情趣。梳理张中行个人的婚姻经历,我们不难判断,三十年代初他笔下称之为“妻”的这位女性正是杨沫。他们栖身的小院落正是当时银闸胡同里的“大丰公寓”,如今这里钉着门牌“银闸胡同26号”,早已变成了寻常百姓家。
张中行说,他有时也常会步行从这些故地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东晋桓温所吟诵的这句话,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称引以感伤生命的迅速消逝,同时也包含着浓浓的怀旧情绪。在《流年碎影———婚事》一文中,张中行明确表示自己这种感慨,是有怀念杨沫的成分在其中的,“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有的,这就好。”
读着以上这些文字,我感受到这个有些忧郁气质的写作者,已经不是名满天下的散文大家张中行,更不是负心薄情的“余永泽”,他只是一个和我一样普通的男人。在世事中沉浮起落的同时,他不时会想起以往岁月中的某些人物和某些角落。何况,这里有他年少时代的初恋,尽管短暂但却有着刻骨的印象。
初恋的经历对于杨沫来说也是刻骨的。这段失败的婚姻,促使她诀别了沙滩和以往的生活轨迹,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而张中行此后也暂别了沙滩,揣着一张北大的毕业证,去往天津、保定和北京城里的各个角落,谋求一份可以“利生”的职业,实践着一个普通小民的“顺生”之道。
十几年里,他做过夜校、中学、大学及家庭教师,甚至还给寺院和尚们上过课,编过刊物、报纸,也做过图书馆职员……当然,在此期间他一直延续在沙滩红楼陶冶出来的旨趣,沿着老北大赋予的“怀疑和追根问底”的学术精神,执着地探究、思考人生哲学命题。
此时,离开沙滩的杨沫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熔炉里,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她一直在积累人生阅历和磨砺文字,酝酿着自己的传世之作。
-今天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是张中行母校老北大的二院旧址。在这里,他像品味苦茶一样思考和践行着“顺生论”。
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重新进城后的杨沫正在集中精力创作《青春之歌》。而此时,张中行的人生轨迹却又转回了沙滩。解放后,他被分配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在这里供职了大半生。这个专以中小学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为主业的文化单位,后来长期驻留在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
很巧,这里正是张中行那已经西迁燕园的母校———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的旧址。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次迁转不同以往,“已经不再是飘流,而是有回家之感。何以言之?是因为这新迁之地乃母校的一部分”。他还记得自己当年揣着师范文凭前来北大报考登记,就在这院子中的一个角落里。正所谓机缘前定,青年张中行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要和这个地方如此难舍难弃。
从1955年到60年代末,张中行一直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默默在缘分的轨迹中耕耘自己内心的那片“沙滩”。他凭着过硬的学术素养,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工作职责。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承揽了不少编撰语法书稿的活儿,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些“外快”来维持家中老小的生计。
他自己对此是有颇多感慨,“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辛酸……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确,“为了活”,这其实就是张中行晚年大作《顺生论》的核心命题。
“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以后不断的“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革”……在多次疾风暴雨的运动中,命运多舛的张中行在沙滩这个地方隐忍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这段情缘短暂却刻骨,一个叫“余永泽”的虚拟人物从此与张中行的生命轨迹若即若离、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另一种形象的“张中行”却在沙滩之外的广阔天地间被迅速张扬和传播着。尽管在张中行后来众多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提及“余永泽”给他的生活带来过什么直接影响,但这似乎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试想,张中行所到之处,不时有人指点耳语,“瞧,《青春之歌》的余永泽来了。”当事人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多年以后,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从自己的角度想象着“成名”后张中行的生活状态:
“随着《青春之歌》(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老鬼《母亲杨沫》)
显然,老鬼认为母亲杨沫所塑造的“余永泽”的形象,一定给张中行一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分析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这一切,“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当张中行自己回顾建国后度过的几十年时,还是更愿意将自身的处境起伏归结于社会的大环境,而非什么个人际遇。直到晚年,他谈到沙滩后街这个曾是母校旧址,又是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院落,依然充满着温暖。“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超过四十年。
心情呢,主流是有回家之感,是安慰,是感谢,难道就没有不如意的吗?当然有,因为整风,大跃进时挨饿,大革命中清扫厕所、请罪等,都是在这里过的。但我有个严格分内外的理论,是那无理无礼的荒唐事是外来的,或说由上边压下来的,并非这旧二院的土生土长。”
-在这里,他用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厚积而薄发奠定了他一代散文大家的地位。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这老北大“旧二院”因为要扩展容量,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拆建改造。年过七旬的张中行随重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一次踏上沙滩的土地。“万没想到,十年之后,旧府旧院大变之后,我又走入此门,过眼看字、手拿笔的生活”。
就在这块自己历练过青春和理想、爱恨与情仇、荒诞和理性的沙滩故地,张中行开始了自己晚年的生命总爆发。尽管还作为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在坚持工作,但这时候已经不需要“为稻粱谋”而过分辛劳,更重要的是“文网渐疏”,老先生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张中行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老旋风”。其大量作品笔调清新、文风冲淡,叙人记事娓娓从容。其行文中饱含厚沉深邃的国学修养和哲理思考,让消沉或是暗淡了多年的旧学传统为之一振。毕竟在沉痛的文化劫难之后,我们的社会还有这样纯正的传统学者在活跃,是件值得欣喜的事。
当商品大潮逐渐迷失人们的精神取向时,还有这样一个耄耋老人,牵出一脉清风,让我们在世纪末“够着了”章太炎、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些五四人物,旧京故事。
真正成名后的中行老人还是恬淡地做自己的“柴门布衣”。闲暇时,他也会去沙滩红楼、银闸胡同之类的故地转转,抚摩一回旧时槐树,发出些“人何以堪”的感伤。蜗居于旧二院的某间老屋,他也会沉吟,这可曾是母校的教室啊,“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追昔,恰好半个世纪”,住在这间屋里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而以为故人来的迷惘。
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是的,故人已经驾鹤西归,人世间的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我站在已经不再有张中行的沙滩,心里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