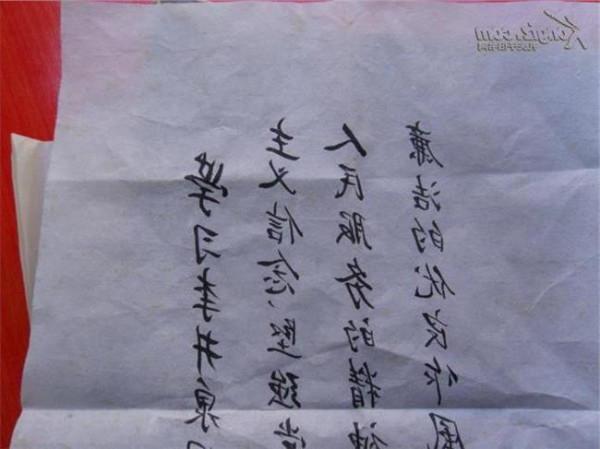李黎蔡湘妹 李黎小妹饮酒图(附漫画)
现在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孔罗荪了,那一年我37岁,站在67岁的孔罗荪面前,满心恭敬。那是1979年秋天,中国作家协会从被“砸烂”的废墟里重新搭建起来,孔罗荪从上海调到北京,参与中国作协的恢复事宜。他后来成为重新出版的《文艺报》双主编之一(另一主编是冯牧),还经常出面主持也是刚恢复的“外事活动”。
孔罗荪是上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写作的左翼作家,打我第一次到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十来年里,他总是笑眯眯的,私下里我不免揣度他是否夜里睡觉也仍然笑眯眯,又乱想到在历次劫波里,他是否也正是靠那雷打不动的微笑去坚守去盼望去争取去穿越的?
1978年,胡耀邦等从党内自上而下地使劲,跟群众中自下而上的努力汇合到一起,使得那段岁月几乎月月有新事,日日有进步,到那年年底,就量变而质变,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我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之一。
从1978年我就参与了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后最早的一些“外事活动”。1979年那天又参加一个人数颇多的见面活动,是孔罗荪出面主持。从境外来的是位美籍华人作家,她是从台湾到美国去定居的。1978年她的夫君采访过我,并将访谈录在一家香港杂志上刊登出来。
那时候积极主动打开门窗跟境外文化界进行交流的不止中国作协一个渠道,有的渠道存在得更早而且态度更加从容,比如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他就牵头接待了若干港台及从欧美来的人士,孔罗荪那天主持接待的那位女士,正是范用特邀到三联书店作过公开演讲的。
虽说我那时已经多次参加涉外活动见过若干境外来客,但都是在指定的场所有领导主持,那天活动刚散,我走到孔罗荪面前,却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申请:“她想单独到我家做客,我也想请她去。您说可以吗?”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孔罗荪笑眯眯地说:“可以呀!”后来,那到我家去的客人跟我说:“我也没有想到,我提出来想去你家拜访,孔罗荪笑眯眯地说:只要刘心武欢迎,没问题呀!”
那客人就是李黎。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在家里接待的无陪同的境外来客。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这有甚稀奇?但是,那一年,离因“里通外国”而被治罪的若干案例还不到三年。李黎来自美国,又有台湾背景,退回三年,我是无论如何不敢接待她的,遑论把她一个人请到自己家里私叙。
我带李黎乘公共汽车去我家。那时我家住在劲松。1979年劲松只盖好了一区、二区,马路南面的三区、四区还在建设中,我们下了公共汽车,必须穿越工地,一路坑坑洼洼,有时我得牵着她的手,帮她跨越坑槽,不免道歉,她却说:“很好。毕竟是在建设啊!”
我家住在五楼,无电梯,李黎活泼地跟我登到五楼。进了我家,介绍给我妻晓歌。那时候,常有人会在乍见到境外来客时或大惊小怪、热情过度,或惶惑拘谨、沟通失畅,晓歌则对李黎亲切自然、和善融通。李黎问能不能在我们屋里各处参观一下,我就带她在那个小小的单元里转了一下,她觉得单元虽小,但如麻雀五脏俱全,又猜出端赖晓歌的布置,简洁而有雅气。晓歌制出了糖渍红果,用小玻璃盅端出请李黎品尝,多年过去,李黎说还记得那美味。
后来李黎又去了新疆,再到劲松,携来一把维族短刀赠我。那时我在恢复出刊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等待决定》,属于主题先行之作,写一位科研人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公派出国有人阻挠,单位领导开会研究,会议室灯火通明,人们在等待最后决定。
我跟李黎说读了她的新作《大风吹》,技巧圆熟,主题在明确与不明确之间,耐人寻味,对比起来自己很惭愧。李黎却说:“你那小说不可妄自菲薄。我读了心中自有一种沉重。”当时她没细说,后来知道,她亲生父母兄姊一直生活在上海,因为有她以及她养父母等海外关系,特别是还牵扯到海峡两岸的问题,“等待决定”确实一度是生活中不可躲避的煎熬。
1987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李黎邀我去她在圣迭戈的家里做客。她带我参观了著名建筑家路易斯·康设计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那是一次何谓现代建筑艺术的启蒙。那个由若干斜置的四层楼房构成的建筑群的中庭,完全由水泥砌成,排斥任何花草树木及盆栽雕塑点缀,只在中轴设一浅槽,营造出一派静寂与安谧。
但是,随着日光的变化,建筑群尽头的树丛与海平面却仿佛翻动的书页,令置身在中庭的人心潮随之波动。李黎又带我去那里最大的一个MALL(购物中心),不是为了购物,而是见识“不同时间在同一空间里的并置”,也即“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范。
1998年我和晓歌联袂访美,那时因为李黎夫君薛人望已被斯坦福大学礼聘去担任正教授,他们迁到斯坦福校区居住,我们就下榻他们家,过了一段悠然的日子。李黎开车带我们到旧金山及湾区,进入黑人教堂听新派唱诗,看民俗游行,参观不同的博物馆,到雅人家中雅集。他们邀我讲《红楼梦》,我2005年在CCTV-10《百家讲坛》讲述的那些,其实已经在旧金山湾区的派对中小试锋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