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幽暗意识 从“幽暗意识”到“政治儒学”
从“幽暗意识”到“政治儒学” ——张灏与蒋庆政治哲学思想评析 张灏先生是海外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他在台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I. Schwartz)的学生。
他曾在1980年代初提出“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低调民主”与“高调民主”等一系列思想概念,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新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蒋庆先生则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后在2001年于贵阳龙场创建阳明精舍,坚持“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立场,邃成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以“政治儒学”独鸣于学界,甚至被当代学者秋风(姚中秋)先生在其微博上列为他心目中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继康有为、孙中山、张君劢、牟宗三之后的五大思想家之一。
张灏的“幽暗意识”和蒋庆的“政治儒学”本无关联,而我之所以将这两个术语相提并论,乃是由于它们恰好代表了当今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思潮。
“幽暗意识”本就是张灏依据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生发出的概念,而“政治儒学”则是秉承着儒家文化本位的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特别注意,此论当与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区分开来。
当然,国内知识界对当前改革道路的“主义”之争远不只有这两种,根据许纪霖先生的总结,现主流上可以粗略地化约为五种: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如今,世界经历了苏东剧变,中国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原教旨的共产主义信仰基本已成明日黄花,于是这就为当前学术思想界的激烈争论预留出较大空间。
尤其是当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时,当下社会公平、造假欺诈、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愈发严重,公民道德失范,伦理底线下滑接近崩溃之势,这都不能不令人开始重新反省、问责时代的病症,重建社会共同体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心。
一.“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 在张灏看來,“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
” 张灏自述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在哈佛旁听美国宗教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讲授的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受到启发,从而意识到人与神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人始终带着罪恶生存,无法变成至善至美的神。
其在基督教中就体现为原罪意识,就像奥古斯丁所说在人丧失了行善的自由意志之后,便只有作恶的本能。虽然西方近代以来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中国的法家等政治思想家也都将人假定为是只会追求自身保存、自身利益的“坏人”,但“幽暗意识”与此不同,它并没有把人性恶当成既定价值去接受,而是“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这个前提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
” 所以,仍旧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绝对不同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或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主义,因而才能在英美自由主义路向上产生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等制度设计,也许这种政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所能证明的最为合理的一种。
针对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的乐观进步精神,“幽暗意识”对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做出了深刻的检讨并抱以警惕心理,我想把这种观点放在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中都不会是什么“文化霸权”,因为毕竟制度可以不断地变更,但人性则是永恒不变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存在普世价值的原因。
当然,“幽暗意识”不仅指向人性中“恶”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极权恐怖体制下,还指向来自制度自身的邪恶。比如汉娜•阿伦特在上世纪曾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军官所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比如顺从和不负责任),而不是残暴冷酷的魔头,但就是当这样“平庸的恶”在德意志民族中普遍渗透之后,德国和世界也就因此陷入了巨大的灾难。
所以,“幽暗意识”不仅要求我们反省自己,同时每个公民还都要防止被卷入幽暗制度的漩涡,不自觉地沦为国家机器作恶的工具。 反观中国传统思想中,虽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幽暗意识”,但传统的“士”阶层却始终传承着一种“忧患意识”。
余英时先生曾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证明了中国儒家传统始终致力于在政治上把“天下无道”改为“天下有道”。从孔子、孟子再到朱子,他们的学说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充满抗议和批判精神,希望以此浇灭身处时代中的“幽暗”,恢复到上古三代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不过,在传统的与二十世纪的中国,这种伟大的精神,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政治制度的配合与主流思潮的支持,成为发展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建设的动力。
因此,它无法在实际层面于建立公平、公正、有生机的政治与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正面作用。” 林毓生先生近些年对中国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进行了集中反思,他认为阻碍传统知识分子思考“家天下”制度的替代品的思想限制在于“内向超越”、宇宙运会观与历史循环论。
两千年来,中国传统儒臣始终相信通过个体的修养功夫可以到达“至善”的道德境界,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统治者同样如此。
对古代儒臣来说,成为“帝师”几乎就是他们终生所要追求的最高名誉和荣耀,因为他们确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君主变为“尧舜”。 由此可见,从西方“幽暗意识”与东方“忧患意识”发展而出的政治理念当然会完全不同,“民主宪政是从客观制度着眼,对权力加以防范,而儒家的抗议精神则是着眼于主观德性的培养以期待一个理想的人格主政,由内在的德性对权力加以净化。
” “幽暗意识”认为人性中的黑暗是无法从根本上清除的,无论何时都要对其加以严防,特别是当一个人成为统治者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之时,就像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所提醒我们的那样: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二.“政治儒学”与“法道互补”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所谓“国学热”再度升温,继海外新儒家“本内圣心性之学开新外王”的努力失败以后,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大陆新儒家”先后登台亮相。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一种儒学传统,从而区别于以宋明心性之学为代表的生命儒学。
他针对当代海内外诸多学人对儒家传统的批评,反驳甘阳和林毓生只知“生命儒学”而不知“政治儒学”,余英时只知“政治化的儒学”而不知“政治儒学”,主张完全抛弃西方那一套自由平等的启蒙话语,重新返回所谓《春秋公羊传》里秘传的“政治儒学”中去,继续从先贤留下的只言片语中绎读微言大义,从而自立于西方现代民主政体之外,实行与中华文明相适应的“王道政治”。
其所谓的“王道政治”就是“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强调统治者应该尊中华文化的代表孔子为王,以六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以道德教化取代“依法治国”,建设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
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蒋庆更是始终坚持传统儒家价值体系。
例如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在美国芝加哥通过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蒋庆指责其仍是一种错误的“西方中心论”产物。他在《政治儒学》一书中为儒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辩护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
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
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
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我认为蒋庆恰恰就在这里犯了错误。
因为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中西之争的实质就是古今之争,古典宗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际关系是否平等,以及是否还能沿用道德伦理去规范民众顺服于这种不平等。所以,即使蒋庆关于儒家价值特殊性的论述全部正确,他依然无法证明当今中国需要的是“王道政治”而非“民主宪政”,除非他否认我们已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这个事实。
梁漱溟先生早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尊卑是个名份,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
” 显然,这就一语道破了传统中央集权帝国统治社会的秘密所在。至于梁先生本人在30年代转向构建具有本土色彩的民粹主义并根据中国文化伦理特质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在我看来则是为儒家道德乌托邦的社会改造提供了现实悲剧的注脚。
此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运用社会学方法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准确地命名为“差序格局”, 即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这样就造成了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 于是,在中国社会里便只能发育出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而不是西方群己权界分明的个人主义。 相近地,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在其长文《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中从“儒表”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时将其命名为“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
那么,如果说在“儒表”“性善论”基础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主要依靠伦理道德的“长老统治”能够维持宅心仁厚、民风淳朴的话,那么“长老”(或蒋庆理想国的“王道”)还想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君临天下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国产电影《被告山杠爷》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更何况,若从“法里”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从来是“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语),政治现实是在法家“性恶论”基础上依靠“法、术、势”维护绝对君权的“内圣外霸”,而不是儒者理想中的“内圣外王”。
总而要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社会中,儒、法两家对立的紧张关系,迫使大部分精英选择“难得糊涂”作为处世之道,再加上道家的犬儒哲学为思想纽带,于是这样一种“儒表法里”、“法道互补”的文明形态便可流衍千年。
换句话说,儒家那种从血缘宗法、伦理尊卑出发而构建的理想政治形态在现实“法家”的政治手腕下只能沦为一种“乌托邦主义”。
三.“荆轲刺孔”与“荆轲颂秦” 秦晖先生论学一向风趣诙谐,曾自撰《世说新语补》三则,其中一则名为《荆轲刺孔》,内容如下: 荆轲欲刺秦王,至秦庭,见龙威凛凛,不敢近前。踌躇有倾,于阶下一展所赍孔丘像,持匕扑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为之,悲剧精神兮万古传。
”有报于秦王曰:此刺孔之歌也,与陛下焚坑之志同,于王事有益焉。王颔之。俄而轲歌愈奋。王不怿,怪其聒噪太甚,以棒击其顶,逐之出。
轲狼狈回驿,郁郁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阳者至,责其激进太过:孔子伟人,岂可刺之哉?轲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义,与舞阳闭门读经,整理国故去矣。如是经年,星移斗转。忽一日启牖,闻市人哗然传曰:祖龙驾崩于沙丘矣。
近二十年来重新兴起的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依照秦晖故事中的隐喻,实际不过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荆轲刺孔”变为了“舞阳读经”,仍然没有摆脱“文化决定论的贫困”,因为“文化”作为一套“无制度意义的(或者说可与多种制度相容的)纯粹审美符号”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制度”却有优劣,“优劣的标准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不能分优劣的是文化,而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人无我有’的符号(或符号的‘能指’)。
‘能指’不能决定‘所指’,因此‘文化’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为中国之祸者,并非人无我有,实乃人我皆有,而人已弃之我尚未弃之物;而中国所需者,也不是什么别人古已有之的‘文化基因’,而是人我皆无而人已先我而争得的人类现代文明”。
由此,让我们按照秦晖的思路,从符号学的角度回到本文开头的“幽暗意识”。那么,张灏所提出的“幽暗意识”其实就是文明符号中的“所指”——人性中那种野蛮的力量,这种阴暗暴力的倾向是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的,不分时代,不分民族,你我皆有。
而相对于这种“所指”,东西方各个民族按“任意性”原则便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能指”,譬如西方基督教的“原罪”、东方思想的“忧患意识”等等,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你有我无,你无我有,没有什么学理上的原因可讲。
经过上述分析后,我们是否还会和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一样认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追求就是西方现代社会启蒙的产物,并且只能在欧洲和美国实现,中国不应亦步亦趋跟随之,而应该回归儒教传统开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政体呢? 实际上,我认为“政治儒学”最大的理论缺陷就在于它所提倡的“王道政治”仍然是重复着儒家二千年来从未在现实法家专制统治中践行过的上古理想,其乌托邦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才会在中国历史上被“法道互补”的实质架空。
如同许纪霖先生在解读曾国藩时所言:“儒家的政治学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那种以‘义’为唯一诉求的王道哲学所体现的只是信念伦理,而缺乏实际政治操作所必不可少的责任伦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仅提供了一种高高上悬的、道德化的政治哲学,而可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学(包括制度设置、法律规范、权力的操作技术等)却是由法家、兵家和道家提供的。
” 虽然蒋庆在《政治儒学》中也谈到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政治家所应具有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并用不小的篇幅反驳林毓生的观点,论证了“政治儒学”中亦有责任伦理资源,但也仅仅是作为资源而已,并没有在现实中形成制度安排,这和学者秋风近来极力从儒家历史中找出宪政资源同样如出一辙。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政治儒学”,相反,在中国转型的非常时期,蒋庆先生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亦多可贵,况且儒学仅就某种价值追求而言,我丝毫不会否定它们的崇高和完美。
正如西哲列奥•施特劳斯学派一样,他们虽然反对西方现代启蒙精神,企图返回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然正当,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在现实制度上给出任何有效的安排和设计,只是在道德价值的形而上阈限内倒转思想史的轨迹,看似破除执迷,十分高明,实则旧瓶新酒,无关痛痒。
西方启蒙运动后的现代性浪潮纵然有它自身的弊端痼疾,例如我们可以在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梦》中看到直观的形象展示,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我们要退回古典世界,况且那些问题究竟是因为现代性本身还是因为现代性不彻底造成的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从历史现实中看,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能够有效限制人性本源和制度的“幽暗”,它的确是比过去“进步”并值得人类整体去追求,同时它并不是什么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从普遍人性和宇宙中的原始野蛮力量出发建立的普世价值。
在我看来,当下有些学者与其在古今之争中执着于古典价值,还不如承认、发觉中国传统社会中可以与现代社会对接的合理内核,比如秦汉后政治上大体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科举制、谏言制等等,而不是将二者绝对对立。
对于“新儒家”而言,不管是海外还是大陆方面,都要做到“西儒会通”,纠正五四运动以来将儒学与西学对立乃至非要整个你死我活的局面,其实原本它们并无那样巨大的分歧,只要稍加调和就可为我所用。
而且,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一味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总会给人以“荆轲颂秦”的误解,尽管我也相信他们并无此意,但不可否认其从客观上确实会起到替强权辩护并阻碍改革的作用。
因为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人类思想行为的动机与结果往往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吊诡,比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们非但没有回到原初基督教的纯洁高尚,反而无意中加速了资本主义世俗化社会的来临。
此亦当为所有抱持着政治实践理想的学者深思。 作为一种容易为国人接受的本土资源,儒家要发挥其对于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三层价值:符号价值、功能价值以及可能的超越价值, 把儒学现代转型的重点放在伦理而非政治上,只有这样,儒学才能作为一种古典文明价值更好地融入现代化多元并存的基本理念中去,超越自身的“理想/现实”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而另外一边,谙熟西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也不能只凭现有知识结构去衡量国学精神,盲目将儒家视为中国历史上“绝对君权”的帮凶、“民主宪政”的敌人,要始终带着温情与敬意对待传统,避免陷入那种“先入为主”的鞭挞讨伐,谨防重蹈卢梭式全能理性的悲剧。 2011.8 (注释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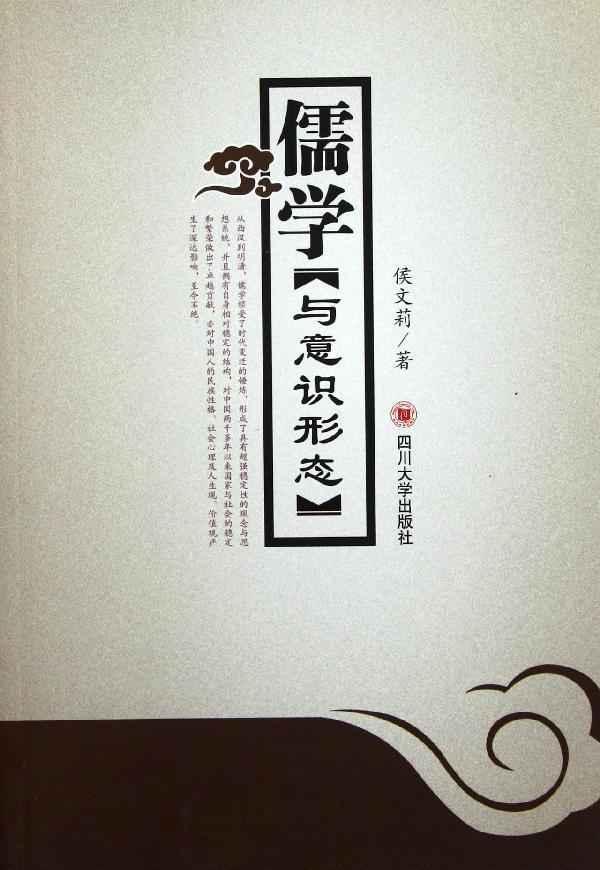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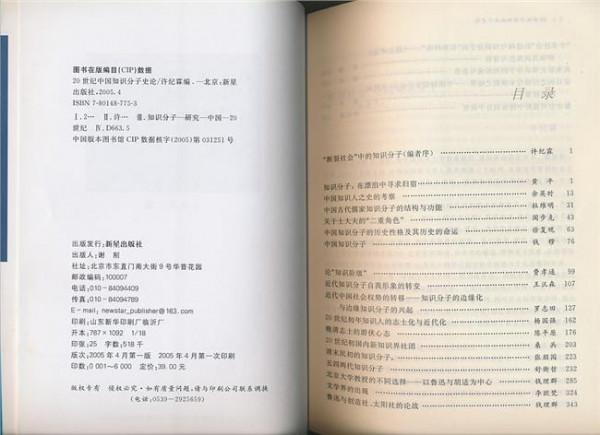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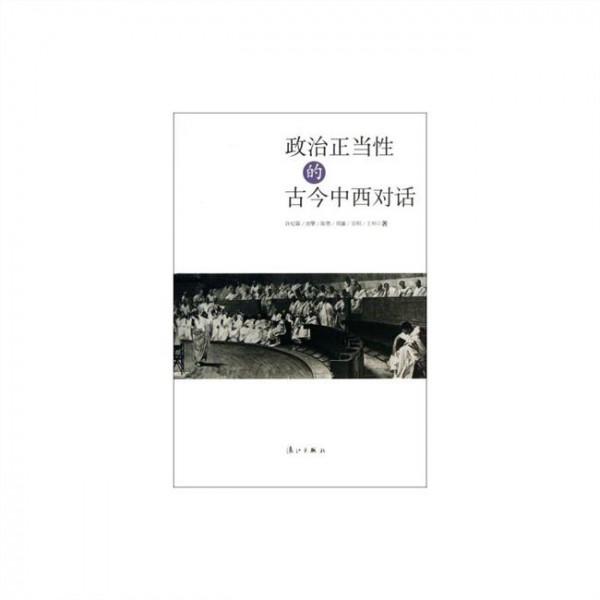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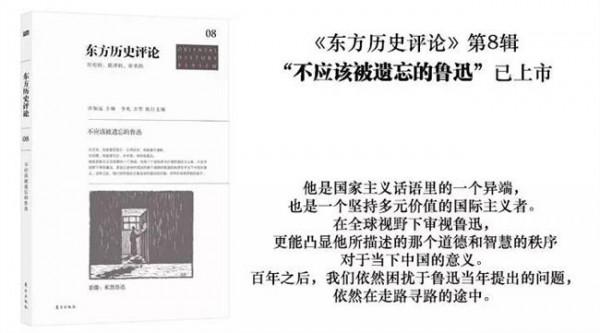


![>许纪霖反毛 [讲坛]精英等于贵族? 许纪霖:反思中西方大学教育](https://pic.bilezu.com/upload/0/f9/0f981c99e378d5a456dbcc465fadd5e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