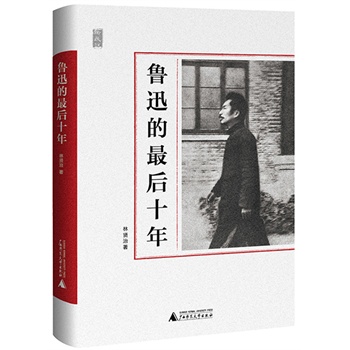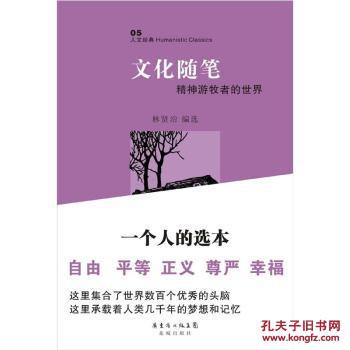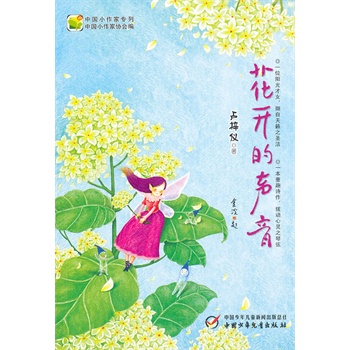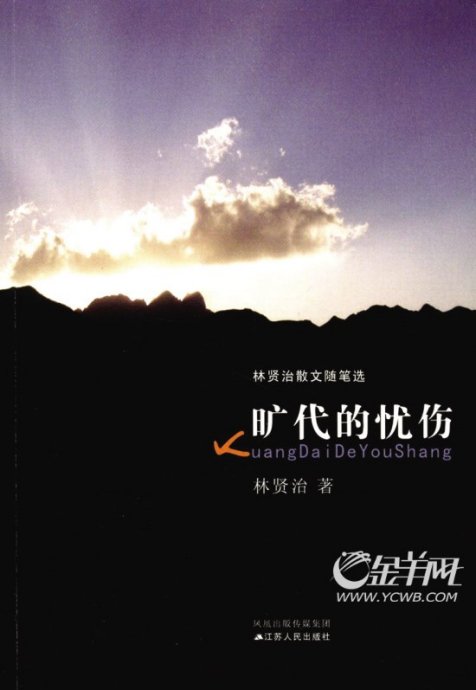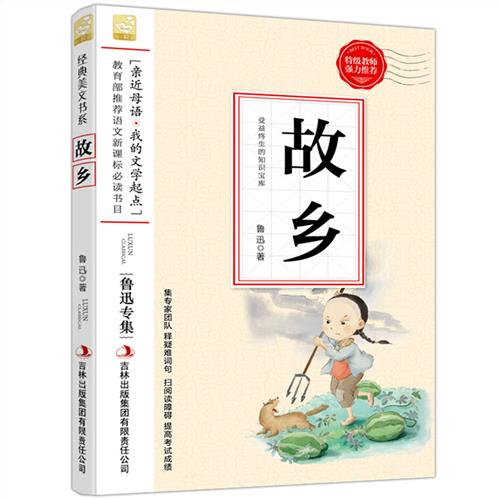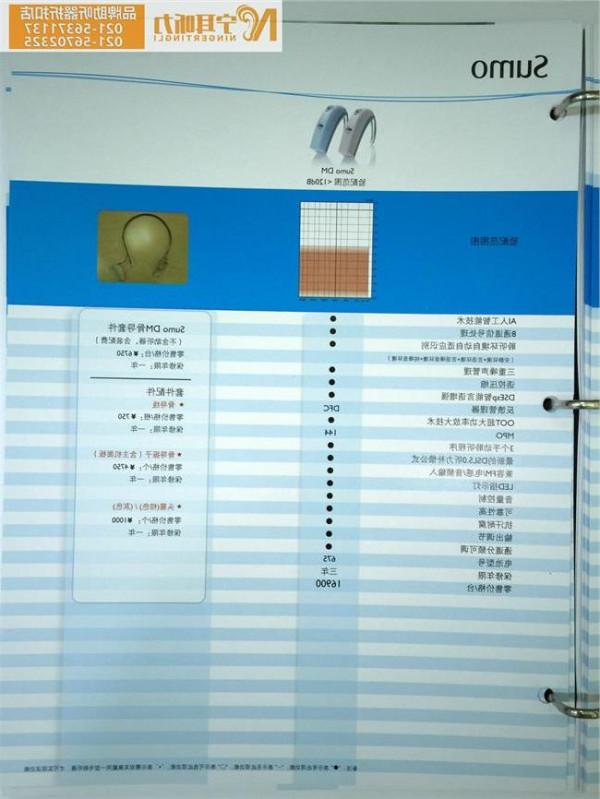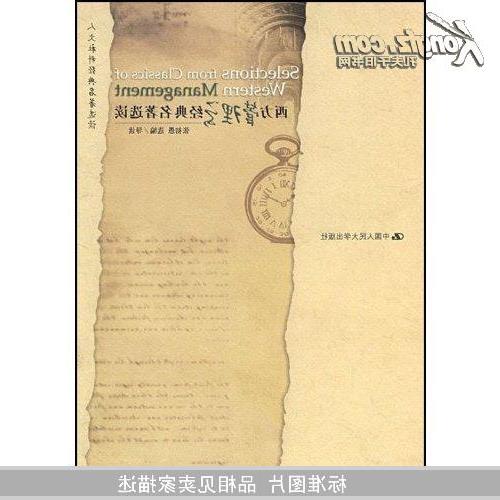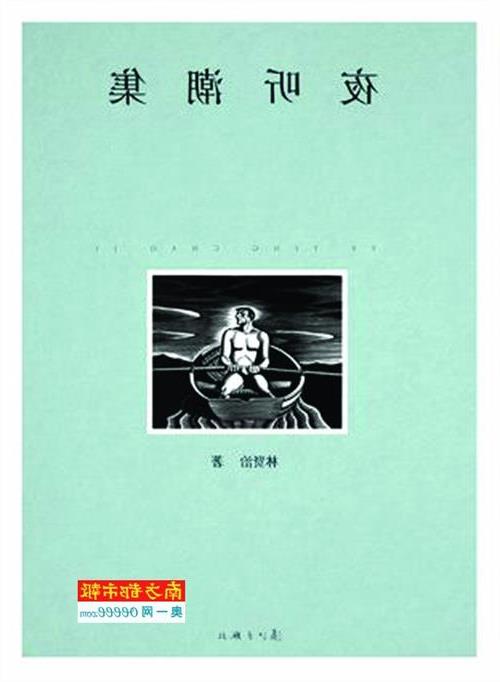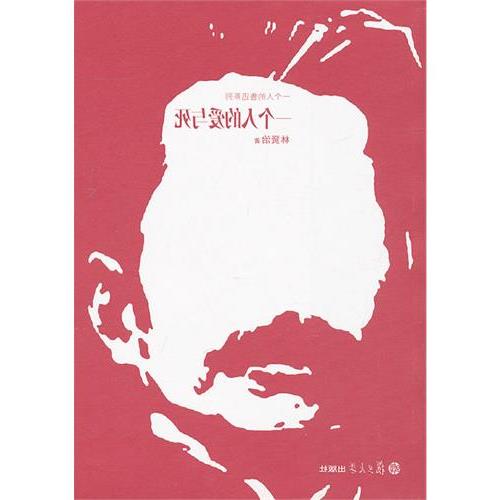旷代的忧伤林贤治 林贤治《旷代的忧伤》连载:向晚的玫瑰云
罗莎•卢森堡(Rosa Luxcmburg,187l-1919),国际共运史上著名女革命家和理论家。波兰人,后流亡瑞士,迁居柏林并取得德国国籍,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多次被捕。一战爆发后,先后组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被捕牺牲。著有《资本积累论》、《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论俄国革命》等。
高中时代的罗莎•卢森堡。
向晚的玫瑰云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
自从有了酋长及各式权威的时候起,人类便在另一种意义上被创造了出来,并根据一个被确定的目标不断地加以改造。结果,离自然人愈来愈远。所谓自然人,那是人类的童年,单纯,幼稚,却保持了生物学意义的自由,最起码的自由。
中世纪把对自由的剥夺制度化了。你以为巴别塔真的建造不了吗?一个信仰,一个意志,一个中心,众声嘈杂最后演绎为一种话语,这样的社会秩序不是巴别塔是什么呢?历史教科书肯定夸大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功绩,他们虽然给神学以沉重的打击,把社会从迷妄中拖曳出来,却并没有解除对个体的精神禁锢。
显然,巴别塔比巴士底狱更难摧毁。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性解放的洪流刚刚涌动起来,到了启蒙时代,便为理性的闸门所节制,个人的本能、欲望、各种活跃的情绪,只好在漩涡中悄然沉没。
进一步,退两步。从整体主义回到整体主义。那时,几乎只有卢梭一人向自然人的方向逃跑。即便是这样一个反思--不同于笛卡儿式的思--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他的背后仍然夹着一条理性主义的小尾巴。
及至20世纪,政党迅速成熟,意识形态急遽膨胀,无论是物质的人或是精神的人,都被高度组织化了。组织是不容玷污的,清洗异类当然要比宗教裁判所更具规模,也更为严厉。谁不知道古拉格和奥斯维辛呢?
这时,人意想成为自己已经变得不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一致把服从他者当作共同恪守的准则。譬如公民,你看众多雷同的面目,就知道那是一群复制品,模子就是法律;工人是操纵机器的机器,农民是驱赶牲灵的牲灵;政治家和革命家,其实也都是为权力原则所支配的人物。
自古而今,角色定位大抵是由权力者和知识者进行的。知识者也是立法者。他们最喜欢标榜"价值中立",实际上同权力者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总之,人被不同的角色分解了。表面上看来,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实是根据角色所规定的范围行动,甚至将奴性内化为本能,行动着仅在于适合相应角色的定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