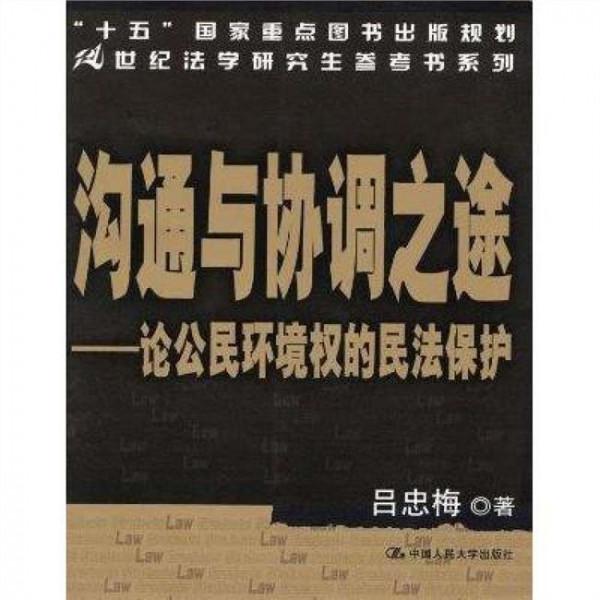吕忠梅环境法 第424期“民商法前沿论坛”——吕忠梅:环境侵权的环境法解读
《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学者们都认为应该将环境侵权写进去,但是,对于环境侵权的内涵,各位学者的认识却大相径庭。我们来看4位学者在不同的《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中对环境侵权的界定:
第一,王利明教授将“环境污染侵权”界定为:因从事生产、生活等活动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破坏生态和资源,直接或间接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这里包括转基因农产品污染、水污染环境责任等12个方面,是一个非常完整、系统的定义,远远超过环境污染的范围。
第二,梁慧星教授认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排污者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徐国栋教授认为环境责任既包括破坏环境要素的责任,也包括直接或间接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责任;并应规定由国家承担最终责任。
第四,杨立新教授认为环境侵权行为的内容仅涉及“环境污染致人损害”。
4个专家建议稿主要分歧有:一是概念不同,分别采用环境污染侵权、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环境责任、环境侵权;二是定位不同,有定位为特殊侵权行为,还有准侵权行为、无过错侵权行为;三是内容不同,包括对环境的损害、致人损害、破坏环境要素、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他人损害等等。可见,几位民法学者在立法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一致。
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第8章,环境污染责任
第65条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66条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67条 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第68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显然,《侵权责任法》只规定了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生态破坏污染,是否属于环境侵权?或者说,环境污染责任之外是否还应该有生态破坏责任?如果有,环境侵权的内涵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说核心的问题是环境侵权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民法学者可以认为环境污染侵权就是环境侵权,但从环境法角度看,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环境侵权不能也不该等于环境污染侵权。
因此,要厘清环境侵权的内涵,就需要跳出民法。以环境法的视角,《侵权责任法》吸收了环境法的部分研究成果,将环境污染责任写入,已经非常不易。但要把生态破坏责任完全纳入《侵权责任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生态破坏的特性与规制方式与民法价值观、调整方式都格格不入。我今天试图给大家说明民法与环境法对环境侵权的不同理解。
在环境法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有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两类,这一区分对于认识环境侵权具有重大意义。环境污染是在环境中排放了过量的物质或能量,导致环境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性质发生变化。生态破坏是过量的摄取物质或能量,导致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丧失或者减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行为多样性不同。环境污染始终能找到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排放行为,是对环境的“二次利用”,形式相对单一,目的明确。但生态破坏找不到有规律的具体行为,甚至是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比如“蝴蝶效应”,是对环境的“一次利用”,行为方式多样,目的各异。
我在法院工作时,遇到一起4千多户梨农诉市交通委等七被告的案件:高速公路行道树上作为梨锈病病菌的越冬宿主,春天暖和后梨锈病病菌大量繁殖,高速公路附近五公里范围内的梨花感染梨锈病,大量减产,导致梨农损失。这个案件中,高速公路建设者按照国家公路建设规范种植行道树,种树行为本身也不会引发梨锈病,那么,梨农应该起诉谁?找不到对应的具体侵权行为,但会出现生态破坏的后果,这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一个明显区别。
这个案件在审委会讨论时,有意见称,本案梨锈病的病菌寄生在桧柏上,还会有棉铃虫寄生在柳树上,稻飞虱寄生在杨树上,今后为了保护环境是否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这还是保护环境吗?
第二,损害后果的表现形态不同。污染物质最终会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人体,造成健康损害,能够找到相对确定的受害人,因此,可以通过污染物迁移转化路径确定损害后果。但生态破坏则不同,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生态破坏,这可以看做是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
二是生态破坏行为也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生态破坏的后果是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具体的受害人,比如刚才讲的梨农案中,梨农遭受了实际的损失;有的时候生态损害可能只针对环境,不涉及具体的个人。
或者说对环境的损害最终会影响到人类,但现在找不到具体的受害人。比如树砍光了,生物多样性消失,不会对现存的人产生即时后果或影响。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存活需要几万种生物支撑,生物多样性消失意味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消失,即人类的灭亡。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导致人类消亡,今天还不能清楚的确定。
第三,损害后果的预测性不同。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产生的结果不可预测,这与人的认知局限直接相关,始终存在使用既有技术产生未知风险的问题,如DDT的发明,曾因为极大的提高了粮食产量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几十年后却发现,DDT是具有极大生物毒性的危险化学物,具有强致癌性,其生物毒性半衰期长达50年,人体脂肪内蓄积的DDT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还可以通过母亲的乳汁危害孩子。
生态系统具有循环规律,大多数生态破坏的后果可预测,可以采取一些针对性预防措施。
相较民事侵权概念,环境侵权具有溢出性,具体表现为:首先,环境侵权不是单一侵权行为引起的单一后果。其次,环境侵权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价值取向不能为民事侵权概念完全囊括。最后,二者根本差异在于价值取向不同,民事侵权概念保护静止的个人的利益,而环境侵权概念保护作为公共利益的整体的环境利益。
比较民法与环境法,从外部视角观察民事侵权和环境侵权的差异,可以看出环境侵权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这在民事侵权中是不存在的。具体体现为:
第一,原因行为及损害形式。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客体是静止的、可区分的,是对人身或者财产的侵害;而环境法客体是动态的、不可区分的。例如大气、江河中的水,都难以归属于个人,大气可以扩散,水会流走,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非民法上的“物”。
环境法的原因行为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其产生损害后果过程中,还有自然因素的作用。比如甲将污染物排放至某河流,污水流到下游乙的养殖水体,甲乙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财产或合同关系,是因为河流的自然流动性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法律关系。
甲的排污行为,有可能直接导致鱼的死亡,也可能是甲排放的某种污染物与河水中其他物质产生了化学反应而导致鱼的死亡。这是环境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最大不同,我把它称之为环境法律关系的间接性。这种间接性表现在侵权上,就是环境侵权的行为主体之间、原因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都有自然因素的介入,不是直接的、确定的联系。
第二,损害后果。民法上损害后果有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都是对“人”的损害,责任也由个人承担。环境法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损害后果,可能只损害了环境而没有损害人,也可能既损害了环境也损害了人。
并且,环境法上的“人”,不是具体的、确定的个人,而是广义的“人”甚至是“人类”,例如长江污染导致许多后果,会对整个流域中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既包括现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也包括未来可能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
第三,因果关系。相较民事侵权,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范围远远超出了主体之间的行为。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环境与污染物可以共同构成对“人”损害的原因,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因果时滞等情形大量存在。在确定环境污染因果关系时,以“污染者负担”、“污染者注意”为基础,初步形成以推定为主、降低受害人证明难度为辅的基本方法。
在生态破坏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长距离、多物种、广效应影响,不能推定与对“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也不能直接套用“污染者注意”理念,受害者的注意义务更高,所需要的知识也更高,使得证明方式、证明标准成为难题。
第四,救济主体。民法上受害人及其受害后的状态是明确具体的。但环境侵权经常呈现不确定性。例如某工厂事故性排放污染物,在受污染的特定区域、特定时段内,有人患病,有人没有得病;患病者难以排除生活习惯、遗传等原因,是否确定为污染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判断或者环境保护理念。
尽管如此,环境污染因为有受害人,还可以通过立法技术将受害人确定为救济主体;而在生态破坏中,如果只有对“环境”损害而没有具体的受害人,救济主体根本无法确定。
由此可见,民法对生态破坏的损害进行救济面临更多难题:生态破坏的“损害”内涵不同于民事侵权的“损害”。民事立法以“人”尤其是“个人”为中心展开,但生态破坏往往没有对“人”尤其是“个人”的损害,不存在民法上的侵害后果,追究责任很困难。
有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包括了生态破坏,我对此无法理解。如果说将生态破坏作为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还可以算作一条理由,但是将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的生态破坏作为环境污染责任,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对“环境”的损害能否完全纳入民事救济的范畴?如果可以,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将对“环境”的损害与对“人”的损害一并纳入还是分别纳入?不存在对“人”的损害,只有对“环境”的损害时,《侵权责任法》如何适用?如果不能,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的损害如何获得救济?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大家可能有疑问,我为什么认为可以将环境污染纳入民事侵权,而生态破坏不可以?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符合民法特殊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首先,环境污染与对“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关系直接清楚;其次,可以直接确定污染造成的对“人”的损害,不需要先确定是否对“环境”造成了损害;最后,可以将对“人”的损害限定在对财产、人身、精神“直接损害”的范围之内。
结合内外部视角,我的结论是,民事责任理论下环境侵权立法不会也不能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其调整范围,从立法法律的稳定与保守特性而言,抛弃生态破坏行为是必然选择。事实上,在我目前的阅读范围内,也没有发现在侵权法中规定生态破坏的立法例,各国均仅将环境污染行为作为特殊侵权纳入。
如果我们因为“环境问题=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则认为“环境侵权=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于立法和理论研究也是有害的思维方式。
因为要提出环境侵权的新概念太困难,我做不到,所以试图用解释的方法去进行说明。为了将环境侵权与民事侵权加以区分,类比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环境侵权的遗传与变异》——民事侵权是母体,环境侵权由母体遗传和变异而来。
遗传是指环境侵权继承了民事侵权基因——四大构成要件,体现了二者的形式差异。变异包括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是指相较于民事侵权,环境侵权原因行为多种、损害利益多元、因果关系范复杂、可归责性减弱,体现了二者的实质差异。
遗传与变异是如何完成的?首先是基因突变,在民法中规定环境侵权,作为民事侵权的一种特殊形态,并没有脱离民事侵权的本性。然后是基因重组,在民事侵权中整合环境法的基因片段,形成新的可遗传“物种”:一是,因为生态环境具有对个人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功能,因此环境侵害的主体应由个体的“人”变为个体的“人”加人类意义上的“人”;二是环境侵害责任救济的利益,涉及到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双重保护,因此要由私人权益变为私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一并保护;三是环境侵害造成的损害后果,既包括对人的损害也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四是救济的方式,必须由私益诉讼变为私益诉讼加公益诉讼。
基因重组形成的新“物种”,我称之为环境侵害。之所以不用“环境侵权”,是为了避免与民事侵权混淆如果依然从侵权的构成要件看,我们会发现,环境侵害与民事侵权之间出现了“此人非比人”、“此权非彼权”、“此害非彼害”、“此责非彼责”的巨大变化。
环境侵害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环境侵害是对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侵害;第二,环境侵害是对环境资源多元价值的侵害;第三,环境侵害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是风险社会的必要代价。从发生学意义看,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副产物,其产生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从价值判断角度讲,一些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正价值”,是风险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价值否定”或者“可谴责性”特征,许多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也不具备主观恶性,。所以我希望能够用“侵害”来表达这样一种客观状态,而不用“侵权”这样具有明显主观判断的表达。
如果环境侵害能够成为上位概念,环境侵害责任体系的构建则需由民法与环境法共同作为。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各种环境污染防治法,都对侵权做了原则性规定。同时,民法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也对环境侵权做了规定。为了构建完善的环境侵害制度,民法和环境法之间要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调,通过专门环境立法强化以公权限制私权,同时,也要通过将公法义务纳入私权,实现民法的绿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