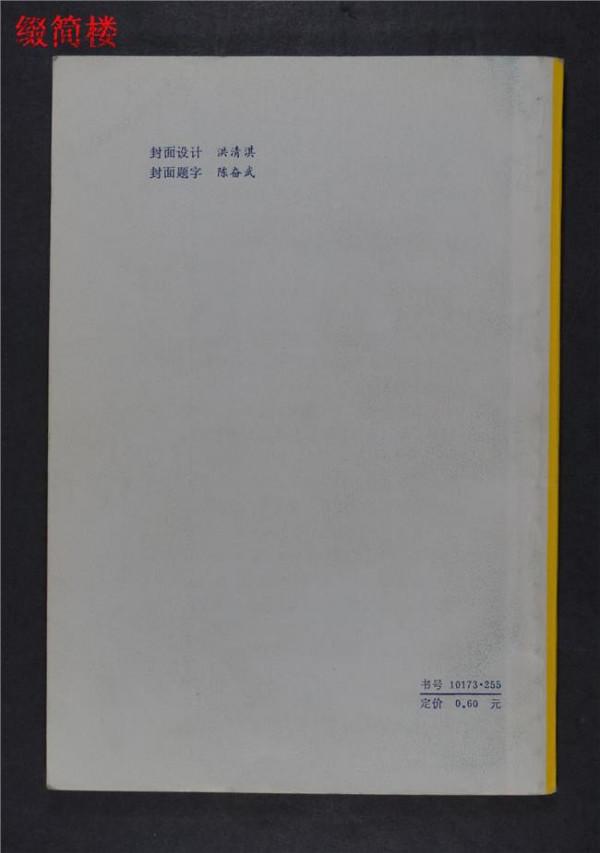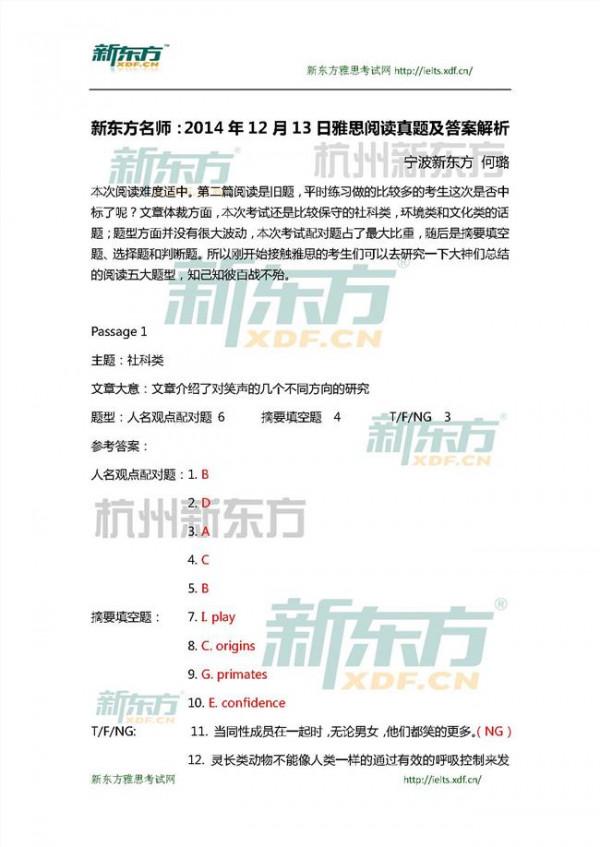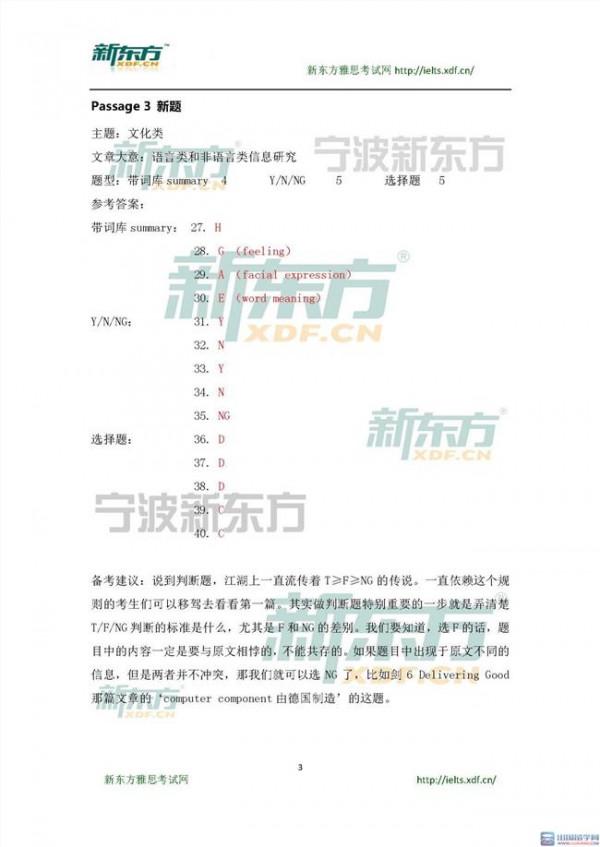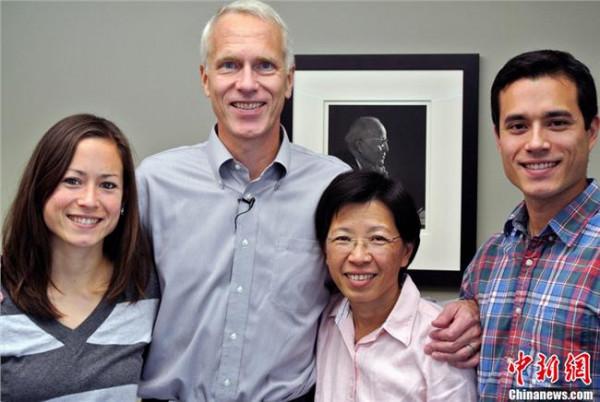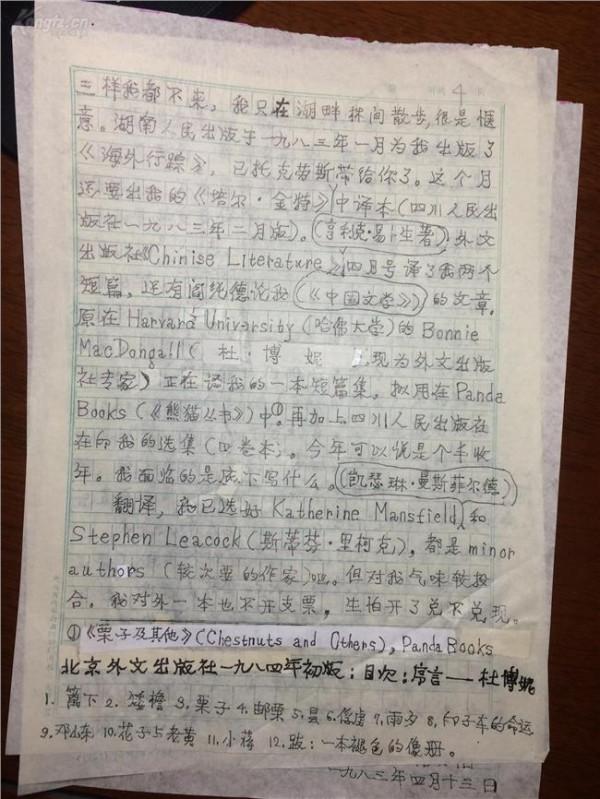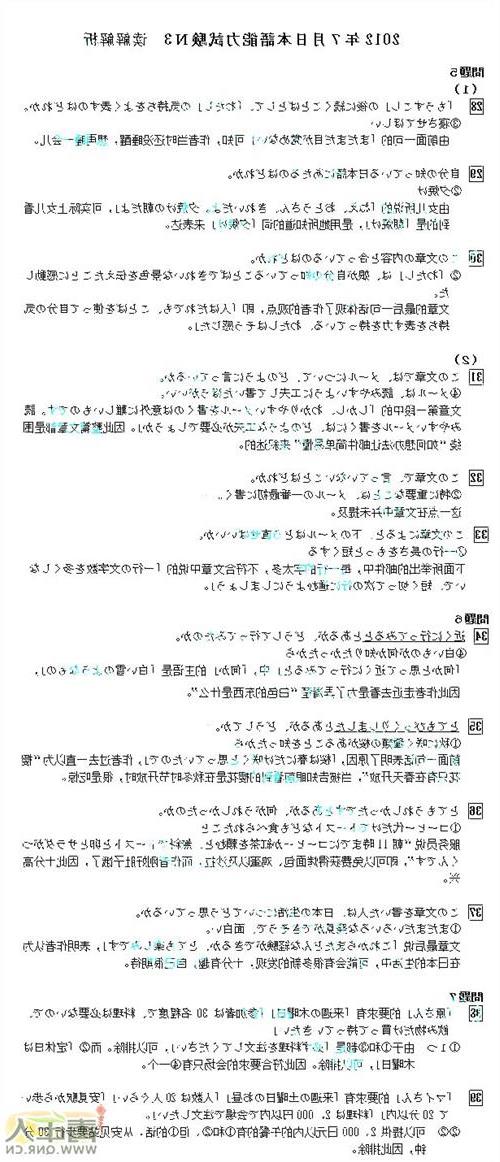(聂华苓作品)珊珊 你在哪里
“喂,喂,等一等!”李鑫跳上车,一把抓住车门后的铜柱,将车票递给车掌,喘咻咻地问道:“这是十二路车吗?” 车掌绷着她那被职业硬化了的脸,“嗯”了一声,一面将票根递给他。刚从花莲来台北的李鑫不大习惯这种冷漠的表情,瞅了她一眼,就在右边靠车头的位子上坐下来,从裤袋里掏出手帕试去额头的汗,然后又由上衣口袋中掏出袖珍记事本,翻了好几页,才找到珊珊的地址,他又默念了一遍:“吉林路九十七巷六号。
” “小姐!”他转向了车掌。
车掌的脸柔和了一些,望着他。 “到了吉林路那一站,请你告诉我一下!” 不知是因为那一声小姐,还是李鑫那一副热切的傻样儿,她点头时竟牵动嘴角笑了一下,然后转过头去看街,街上正有一个穿着花裙的女孩走过。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不是上下班时刻,车上的乘客连李鑫一起才只有四个人。“这倒象是一辆专车送我去看珊珊的。”他一面想,一面将记事本放回袋内。“十五年了,她该还认得我吧!”多少年来,每当他想到珊珊的时候,他的情绪早已没有一丝儿波动了。
但此刻,他的心开始有点儿激动起来,不觉将手中的票根搓成了一团。 珊珊是他生命中第一个女孩,一直供奉在他心坛上最隐秘、最神圣的一角。但真正说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他们甚至于没有谈过多少话。
他对她的感情是那么飘忽;他对她的记忆几乎是空无所有,但多少年来,他却常常会想起她。她象征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一个飘渺而又美丽的梦。他不是作家,也不是艺术家,但他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好幻想,好新奇。
他早听说珊珊也在台湾,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直到这一次因公由花莲出差到台北,他才有机会去看他。 车子快到第二站,车掌在喉咙管里哼了一声:“有人下车吗?”没人理会,她吹了一声哨子,车子直驶了过去。
李鑫向车上的人扫了一眼:他正对面坐着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和一个中年男人,对面靠车尾坐着一个中年妇人。那老头儿方头大耳,端端正正的五官,穿着一身黄卡叽中山装,李鑫觉得他不是挺有气魄的样子,心想:“这老头儿年轻时必是老太太们相女婿的好对象。
”那中年男人想必是近一两年来才发了福,西装已经胀得扣不上了,但他看上去并不结实,软稀稀的,象是一皮囊的面糊,这是李鑫看他第一眼的印象。至于那个中年妇人,李鑫只看到了她那个红头儿酒糟鼻子。
正当李鑫如此打量那几个人的时候,车子已到了北门站,上来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打着一条红艳艳的麻质领带。“这个人就象是木匠手里的木头人,斧子太利,一溜手把两边的脸庞削得太多了!
”李鑫望着他那尖削的脸似笑非笑地这样想。 “请你先买票!”车掌拦住那上车的人说道。 “我下一站补票!” “不行,你先买票!” “我就是不,看你把我怎么样!”那人双手在胸前一叉,硬着脖子。
车掌仍用手拦住车门,脸象刚浆过的粗布,硬板板的。 “你到底让不让我上来?你神气什么?那上车的人用一只手指着车掌的鼻尖喝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可不是骗你这一张票的人!”他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好啦,好啦,我这里有票!”那老头儿撕了一张票递给了车掌。 “谢谢,老先生,”那新上车的人在老先生与那位发福的先生之间坐下了。 “等一下我下车买了票还你!”他一面说,一面用眼睛狠狠地瞪了车掌一眼。
她正在用手绢拭眼泪。 “用不着了!听你口音,好象贵处是江西?” “不错,你老先生也是江西?” 老头儿微笑着点了点头:“请问贵姓?” 那人连忙在衣袋内掏出皮夹,抽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了老头儿。 “啊,作家,是的,作家,是的,是的!
”老头儿余音犹缭绕不绝。 另外那个人伸长了脖子看老头儿手中的名片,嚅动着嘴唇念道:“作家齐志飞。”然后眼珠子一上一下地想了一会,忽然叫了起来:“啊,齐志飞,我拜读过你的小说,什么——‘樱花再开的时候’,是吧?” 齐志飞脸上的怒气全消了,堆着一脸的笑,忙将右手伸了过去:“是的,请指教, 请问你老兄——” 那人一面握住了齐志飞的手,一面用左手在自己上衣口袋内,也抽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齐志飞。
“啊,吴大有。你老兄可真了不起,一张名片前后全印满了头衔!这总共有二十好几个吧!”齐志飞仍握着对方的手不放。 “不敢当,都是空头衔,没有实权的。”吴大有这才将手抽了回去。 这时,齐志飞才想起了他的老乡,转过身来。
“请问老先生贵姓?” “敝姓秦。” “秦老先生在什么地方得意?” “我现在是三军总司令,在家管鸡子、鸭子、狗,呵呵,我们现在没有用了!” “哪里,老前辈,老前辈。”齐志飞欠了欠身子。
“你以前在大陆——” “我以前干过几任县长,在四川干过行政专员,来台湾以后我就赋闲了。唉,这一说都说十几年以前的事罗!” 四川,十几年以前,这些极普通的字眼,在今天的李鑫心中都有了特殊的意义。
他可不就是十几年以前在四川第一次看到珊珊?她是妹妹的初中同学,那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子,说正读高中。有一天傍晚,他站在门前,远远地,看见大路上有个小女孩背着落日走来,穿着一件柔蓝的衣服,身后是一片耀眼的金辉,仿佛她就是由那天国的光辉中走出来的。
她和妹妹在一起,他走过去和她搭讪,她除了点头摇头之外,就是用手绢捂着嘴笑。 他听见了她的南京腔,和她开玩笑,喊她南京大萝卜,她啐了他一口:“呸!
我叫赖玉珊,她们都喊我珊珊!”说完又连忙用手绢后着嘴笑。妹妹暗地告诉他,珊珊摔跤摔缺了一小块门牙,不愿让人看见她的缺牙齿。他笑着逗妹妹:“没关系,她反正比你漂亮,她有个小酒涡!” 小女孩们在一块儿总是唧唧哝哝的,他一走过去,她们就住了嘴;他一走开,她们就大笑。
后来妹妹才告诉他:“珊珊喊你瘦猴儿!”“小鬼!”他笑着骂了一句,但他心里确实恨自己太瘦。 “哈,妙论!” 李鑫一抬头,那个捂着嘴笑的小女孩不见了,原来是眼面前的秦老先生大叫了一声。
只听见吴大有一本正经地说道:“……我的女朋友可以分三类:一类是父母有地位,小姐自己没有学问;一类是小姐自己有学问,父母没有地位;一类是父母没有地位,小姐自己也没有学问。
所以——这事很伤脑筋。”吴大有连连摇头。 “你自己结婚与别人父母有什么关系?”齐志飞笑着问道。 “呵,关系可很大,”吴大有双眉紧锁,“有了父母,第一,下女走了,我们可以有地方吃饭;第二,我们吵直起架来,可以有人从中调解;第三,孩子生多了,可以有人照顾; 第四——” 没等他说下去,齐志飞和秦老先生就哄然大笑了起来;车尾那位酒糟鼻子太太望着他们瘪了一下嘴;李鑫也抿着嘴想笑。
只有吴大有一个人可没有笑意,他好象想起了什么更重要的事,对齐志飞说道:“齐先生,你写小说是怎么个写法?我要向你请教。
我这一辈子, 嗨,”他摇了摇头,“罗罗嗦嗦的事可也不少!可以写好几部爱情小说。” “写小说可也不那么容易,”齐志飞扬了扬眉尖,“你首先要把你的全部感情放进去,你必须和你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叹气……” “唉!
”吴大有真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想起了他那悲哀的浪漫史,还是因为有感于创作的艰难。 “写小说的手法也多得很,一言难尽。
”齐志飞沉吟了一下,“至于我自己,我是什么手法都用: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他还翻着白眼在想。 “啊,这么多主义!”吴大有一下子愣住了。 “这年头,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把人都搅昏了。
我们以前就很少听说什么主义,一样吃饭过日子。”秦老先生摇头叹气。 李鑫在对面好象坐包厢看戏一样,不觉暗自好笑。他不想再听下去。转过身去看街。 车子正好经过一个小果摊,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李鑫一眼就看见了那黄澄澄的橘子。
怎么回事?今天的一事一物都与珊珊发生了关联?来台湾十几年,哪一年不看见橘子!唯独这一次,他就想起了当年和珊珊、妹妹一道去橘林偷橘子的情景。
初冬的太阳照着广漠的田野。田野尽头是一片橘林,好象一道金边,镶在蓝天绿野之间。珊珊、阳光、田野、橘林。这一切都使人兴奋得心跳。李鑫提议去橘林偷橘子,两个 小女孩拍手叫好。四川的橘子很便宜,他们不是买不起。
但那不是寻常的偷窃,没有偷窃者的辛酸,有的只是新鲜的刺激,只是青春的焕发。少年时代的一切罪过都含有美丽的诗。他还记得,那天珊珊穿着一件黑丝绒短外衣,配着一条石榴红的羊毛围巾,她的脸也象个小太阳一样,照得人的眼发亮,照得人的心暖暖的。
她和妹妹沿途扯野草编小花篮,一面唱着歌; 他诌些笑话逗她们笑,珊珊笑得好开心,竟忘了用手绢捂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笑话可真肤浅,但那时候确实使两个小女孩快活得象两只小鹿一样,在金色的田野上跳跳蹦蹦的。
他们分配好了工作:李鑫爬树偷橘;珊珊和妹妹分站在橘林的两头放哨。他们约好了一个最顺 口的信号,假若捉“贼”的人来了,放哨的人只要高呼一声“喂——”他们就逃掉。李鑫一向是文绉绉的,那一天不知是哪儿来的一股劲,真象个“瘦猴儿”一样,跳下了这一棵树, 又爬上了那一棵,树底下扔了一大堆金光闪闪的“赃物”。
有一会儿,他坐在树上,蓝色的空气中荡漾着橘子的清香,远远地看见珊珊象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东瞅一下,西瞅一下。
他不禁向她招了招手,她含笑跑来了。他由树上溜下,说道:“来,上去,不要怕,我帮你!他没想到那小女孩竟是如此灵巧,他没费多大力就帮她爬上了树。他们分坐两上枝桠上。
他只顾拣最大最熟的橘子摘给珊珊,自己也忘了吃,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与橘子,是蓝水晶的天 盖;风,象个调皮小仙人,只用它的小翅膀那么轻轻一扇,他们四周的权叶与橘子就哗哗哗地逐渐响开来。珊珊坐在树桠上,荡着两腿,一面吃,一面东张西望,嘴边的小酒涡荡呀荡的,仿佛装满了一涡橘汁似的,李鑫恨不得凑过去用舌尖轻轻舔一口。
突然,远处竹林里传来狗叫声,李鑫抬头一看,不好了,捉“贼”的来了!竹林里跑出了一条狂叫的恶狗,后面跟着一个头缠白布的高大女人,口里大声吆喝,手里的竹竿不断在地上敲打。
李鑫先跳下树,然后站在树下接珊珊下来。她慌忙一跳,正好撞在他的怀里,珊珊的脸一下象火烧似的红了。 他的脸也热辣辣的,一直热到耳根。
他顾不了那一堆辛苦“偷”的的“脏物”了,拉着珊珊就跑。正在这时,只听见远处有人直着嗓子怪叫:“喂来了,喂来了,喂来了!”那是妹妹的声音,吓得走了腔。珊珊拉着他的手跑得脸绯红,石榴红的围巾随风飘起,正好拂在他的脸上。
他们和妹妹在一座竹林后田埂上会合了,妹妹用裙子兜了一兜橘子,脸象刚出笼的馒头,直冒气。一见面,妹妹就撅着嘴说道:“珊珊,怪你,你放哨的,跑到树上吃橘子去了!”李鑫指着妹妹兜着的橘子笑道:“你呢,你还不是只顾摘橘子去了!
”珊珊对他挤挤眼儿,酒涡又荡了一下。他们讲起刚才的狼狈情景,笑成一团,珊珊差一点儿跌到水田里去了。 “哎哟,笑死人的,我笑不得了!” 李鑫吃了一惊,是谁也在笑?扭过头一看,车掌背后有两个女人在笑,其中一个正是一上车就看见了的那个酒糟鼻子,不知什么时候由对面移到这边坐位上来了。
另一个女人,大概是在他胡思乱想的当儿上来的吧,正好坐在车掌紧背后,只看得见挺在外面的一个大肚子和一双浮肿的脚。
两个女人之间有两个小孩跪在位子上看街。 “哎哟,天下有这种事?自己生孩子生不出来,骂别人,哎哟,我笑不得了!”一听就知道那是一个南方人打官腔的口音。 “你这一个多大?”酒糟鼻子的声音。
“才一岁半!” “你也真密,头一个不满一岁就又怀了!” “告诉你了,我年年大肚子,我早不想要了,就是他爸爸!” 两个女人挤在一堆叽叽咕咕了一阵子,接着又是一阵笑声。酒糟鼻子突然不笑了,叫道:“你看,那不是崔小姐!
哪,在那辆三轮车上!” “那个老处女!五十岁了!我看了她就恶心,要找男人也不趁早,到老了反而打扮得象个妖精。你看她那一副干柴象,谁要?” “你别说,她一个人,总得有点依靠,比不得在大陆。
” “谁叫她年轻的时候田里选瓜,越选越差!到老了就乱抓了。她那男人比她年轻二十岁,年轻二十岁呀!她可以做他的老娘!那个老处女,我们都叫她老处女。那男人当初追一个小姐,刚好那个小姐又喜欢他爸爸的一个同事,他有一栋房子,手里还有许多美金,他太太在大陆,又好看,又能干,他也花了一番功夫才讨到她,花了好大功夫啊!
她生肺病,别的男朋友都走了,只有他天天带一把花去,就只有他一个人天天带一把花去呀。他们家那条狼狗呀,真凶!
我去过他们家,布置得才叫漂亮!那条狗是英国种,他们没有儿子,把狗当儿子一样……” 李鑫皱了皱眉头,心里想:这真是一只语无伦次的话匣子!对面三个人本来还嗡嗡的在谈什么,现在也都没劲了。
车子象个大摇篮,一颠一晃,再加上窗口射进来的微温的阳光,秦老先生和吴大有似乎昏昏沉沉地想打盹;齐志飞衔着一根香烟,眯着眼望窗外,大概又在想他的小说吧。 车掌一声哨子,车子又到了一站,上来了一个女孩子,杏黄衬衫,白毛衣,墨绿裙子,腋下夹着一本洋装书,她空着位子不坐,偏直挺挺地站在那两个唠叨不休的女人面前。
只听见那个打官腔的女人说道:“我还显得年轻?老罗!我要不是大生小产的这么多胎,比现在还要显得年轻!
我现在都怕照镜子,他爸爸说我变得简直象只大母鸭一样了!”接着是一阵鸭叫的笑声。 那新上车的女孩,皱了一下眉心,刚好跪着的两个小孩子要转过身坐下来,有一个孩子又踹了那女孩一脚,裙子上沾一块灰印子,她用手掸了掸,转身悻悻地走到车头来,扶着司机背后的铜柱了站着。
李鑫看了看身旁的空位子,挪动了一下身子,又望了望那女孩。 但她却是个石雕木刻的人,昂着头,尖着鼻子,眼睛盯着前方。 “女孩儿家差不多都是这么怪里怪气的,就象一世界的人都在她脚底下!
”李鑫心里这样想,眼睛仍盯在那女孩的脸上。乍一看,她长得太单薄,尖下巴,细眼睛,但她那修长的个头,那松散的长发,以及那眉梢眼角所流露的孤芳自常的神情,使人有一股清逸之感。
“这女孩大概二十左右吧!”李鑫如此打量她。但紧接着,他的思想又飘回珊珊身上去了。“胜 利那年在重庆碰到珊珊的时候,她不就是这样的年龄吗?”恍惚之中,他又看见了她远远走来那风韵嫣然的样儿。
那一年夏天,他大学刚毕业,买好了回家的船票,在上清寺那条路上闲荡。迎面走来一个女孩,穿着一件银灰撒花府绸旗袍,戴着一副墨镜,打着一把浅紫小阳伞。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瞪在那女孩身上,心想:“好一个匀称的身段!
”却不防那女孩走近身来,取下墨镜一笑:“你不认得我了?”他再一看,原来就是珊珊!自从他离家到重庆升学以后,他们有四年没见过面。他第一眼就发觉她的缺牙齿已经没有了。她已经由一个娇憨的小女孩子长成一个娉娉婷婷的少女了!
不知为什么,那一次见面使他很尴尬,他结结巴巴地什么也说不出来,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之后,就向她要了她寄住人家的地址。她是暑期到重庆考大学的。当天晚上,他在她门外徘徊了好久才有勇气去敲门,但开门的女佣人告诉他珊珊不在家,刚刚和同学上街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上了船。复员以后,听说珊珊结婚了。“假若那一晚见到了她,她是否——” 这时,只听见他面前“呼”地一下,他眨了一下眼,原来是车上那个女孩的大裙子在他面前掠过去了。
她被他瞪得恼了火,撅着嘴移到对面车尾空位子前站着,谁也别想再看她。李鑫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转过脸去看窗外。车子正好走过堤上,远处耸立着火葬场的黑色烟囱。堤上有一长串人正呜哩哇啦地在送殡。
李鑫回头一看,秦老先生和吴大有不再打瞌睡了,坐直了身子看窗外,齐志飞转身用胳臂碰了一下他身旁的吴大有:“喂,你看了这送殡的,有何感想?”他嘴角吊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象这样死法也可说是备极哀荣了!
”吴大有回答道。 秦老先生转身背着窗外,皱着眉头,看样子,他既不愿看送殡,也不愿听人谈到死这个问题。 “你猜我想的是什么?”齐志飞嘴角吊着的那个微笑这一下可笑开了,用手整了一下他的红领带,掸了掸身上的灰,对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得意地瞥了一下。
“我们写小说的人就是要会利用生活。别人看上去没有一点意义的事,在我们眼里就有了意义。你懂吗? 譬如看见了这些送殡的,我一下子就有了个灵感!
” “啊!”吴大有脖子一伸。 秦老先生也好奇地转向齐志飞,张着嘴听他讲。 “我突然想到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男的死了,他在生时一表不凡,风流倜傥——” “就和你老兄一样!”吴大有打断了他的话。 齐志飞笑了一下,急忙又拾起了自己的话。
“有两个女的同时爱他,一个象月亮,温柔美丽;一个象太阳,热得象一团火——” “那真艳福不浅!”吴大有又忍不住插了一句。 “呵呵!”秦先生的兴致更大了。 “你听我讲,”齐志飞又用胳臂碰了一下吴大有,“这两个女的都爱他。
好,那个男的死了,两个女人都来送殡,这一下了可碰上了!”齐志飞还用两个食指头尖互点了一下。 “嘿!那她们还不打起架来?”吴大有一脸严肃的神色。 “呵呵,有意思,有意思!
”秦老先生连连点头。 “哪里还打得起架来!”齐志飞不屑地望了吴大有一眼,“她们碰上了之后——”他用手摸了一下他那油光水滑的烦恼丝,“嗯——,这以后我还要想一想,还要好好地想一想。” 齐志飞歉然一笑之后,便不作声了。
李鑫正高兴可以安静一会儿了,车掌背后那两个女人的声音又象夏天的绿头苍蝇一样,嗡到这边来了,挥不掉,打不开。 “……我这个儿子呀!”是那南腔北调的声音,“他爸爸象命根一样。
你看,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他和其他几个小鬼是不同,我打针催生把他催下来的呀,就是要他刚好在腊月初六那一天生,命才好!果然他就不同,会看人脸色,花样又多,从不吃亏,说话跟大人一样,有板有眼,刁得很!……” “你们平时作何消遣?”酒糟鼻子显然对别人儿子不感兴趣,转换了一个话题。
“打打小牌!嗨,前天我和了一副巧牌!” “怎么样的一副牌?”酒糟鼻子的兴趣来了,声音也宏亮了一些。 “条子清一色,一条龙,还有一般高!
” 真叫绝!以后你们三缺一的时候,我来凑一脚!” “你只管来,我们那里有三个脚,你来了总凑得起来。我打牌呀,可是要看人来,牌品不好的不来;一个小钱一个小钱零掏的不来,我——” “我也一样,我们的性情倒是很合得来!
” 他们俩人越谈越亲热,最后酒糟鼻子竟把别人命根子儿子抱在怀里,说要认他做干儿子。车子正经过翻修的马路,碰着了一个大坑,猛然颠动了一下。“哎哟!”那女人一双手捧着大肚子叫了一声,“他老是不要我出来,我在家闷不住,就带两个孩子出来逛逛街。
” “你们先生真好,疼你得很!” “哪个先生不疼太太!”那南腔北调的声音更扬高了,“我打牌,他就乖乖地守在旁边,乖乖地。我打一夜,他就坐一夜,你叫他去睡,他都不睡。
有一次,别人都看不过去了,劝我不要打了,说他第二天要上班。我说:“不行!我这一百三十六张可比他亲爱得多!” 两个女人又咯咯笑了一阵。 李鑫厌烦得恨不得用手捂住耳朵。他看了看表,车子已走了二十五分钟了。
他转过头去问车掌:“怎么还没有到?” “修路嘛,车子要绕路走。快了!”这一次,车掌可多说了两句话。 快了!他快要看到分别十五年的珊珊了!不由得又掏出那个袖珍记事本,将珊珊地址念了一遍:“吉林路九十七巷六号。
”他的心开始噗噗地跳了起来。他看到她时称呼什么呢? 还喊她珊珊吗?对一个做了几个孩子的母亲仍叫小名,似乎总不太合适;喊她邱太太吗?也别扭。这样一称呼,就像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儿关系似的,他不甘心!
他决定什么也不称呼,他只要用眼睛那么深深地望她一眼,再低声问她一句:“还记得我吗?”她也许起先会怔怔地望 着他,然后淡淡地一笑,点一下头。于是,她的酒涡又轻轻一荡,缺牙齿又露出来了。
啊, 不,那是她小时候的样儿,她在重庆时就没有缺牙齿了。他极力要幼想出珊珊此时的神态,但那捂着嘴笑的娇憨神情,在树上荡着两条小腿吃橘子的贪婪样儿,总是来打扰他的幼想。 她现在也许松松地挽了一个髻,用一根柔蓝的缎带绾在脑后,就和他第一次看到她时那衣服的颜色一样,那种柔和的颜色只有配在她身上才调和。
她不象小时候那么爱笑了,静静地抱着孩子坐在角落里,眼睛里有一种少女时代所没有的东西,迷迷蒙蒙的,看起来叫人有点儿 愁。
她一定会叫她的孩子们来挨着他。他会特别喜欢她的女儿,因为她更象她妈妈小时候的样儿。他要把她女儿抱在身上,问她认不认得他。她当然认得他的,因为妈妈常常向孩子们 讲到他,用一种低沉的、柔美的声调讲到他。
“先生,先生,吉林路到啦!先生!” 李鑫惊得一抖,转过头去,已经有人下车了。 “我喊了你好多遍啦,吉林路到啦!”车掌说道。 李鑫忙站起身来,但手上的票根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弯着身子,在位子上下四周一 一看过,都没有。
“快点啦!只等你一个人!”车掌已将哨子放在嘴里。 他直起身子,那酒糟鼻子正对着窗外高声叫道:“邱太太,我哪天来陪你打小牌。 你多少巷?我又忘了!” “吉林路九十七巷,六号!
”那南腔北调的声音在窗外回应。 李鑫一下子怔住了! “慢点!小毛头,你想死呀!”那一声“小毛头”却是纯粹的南京腔,由车外无情地 钻进李鑫耳中。 一辆大卡车从公共汽车旁擦了过去。 李鑫想扭头去看窗外,但他扭不过去,扶着那冷冰冰的铜柱子,无力地倒在车凳上。
“你到底下不下车呀!”车掌发火了。 “我——我不下车了!”李鑫吃力地说出了这句话,眼睛愣愣的。 车掌不耐烦地吹了一声哨子,咔哒一下将车门关上了,咕噜了一句:“莫名其妙!
” 车上的人都觉得李鑫的神色不对。秦老先生摇摇头:“唉,这年头,古怪事越来越多!”酒糟鼻子弯着身子,伸长了脖子来看李鑫;吴大有转动着他空洞的眼珠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反应;齐志飞若有所思地望着李鑫,然后掏出了记事本,在上面沙沙地写着,说不定李鑫这一下子就荣任了他那篇送殡小说的主角。
连那个高踞在世人之上的女孩竟也扭过头来瞅了李鑫一眼。 (选自《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