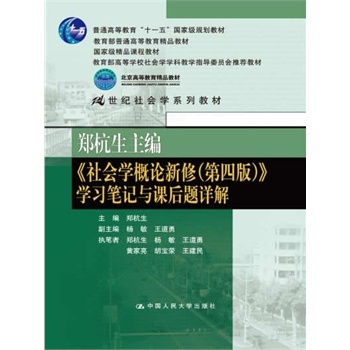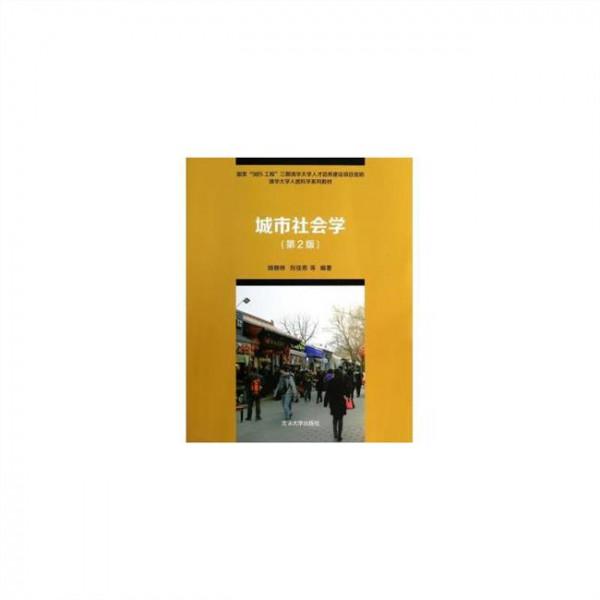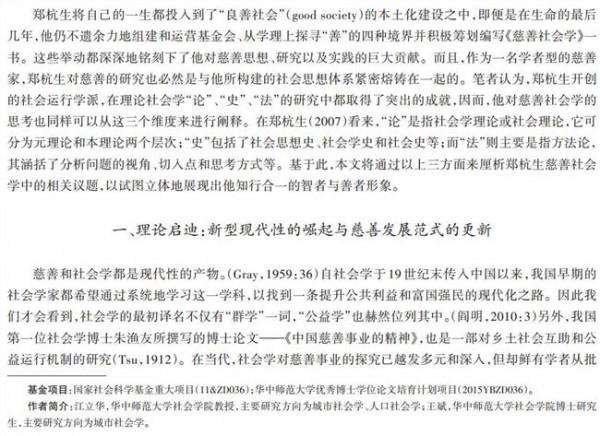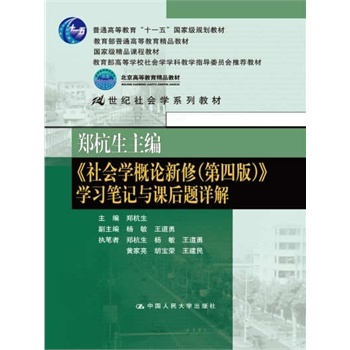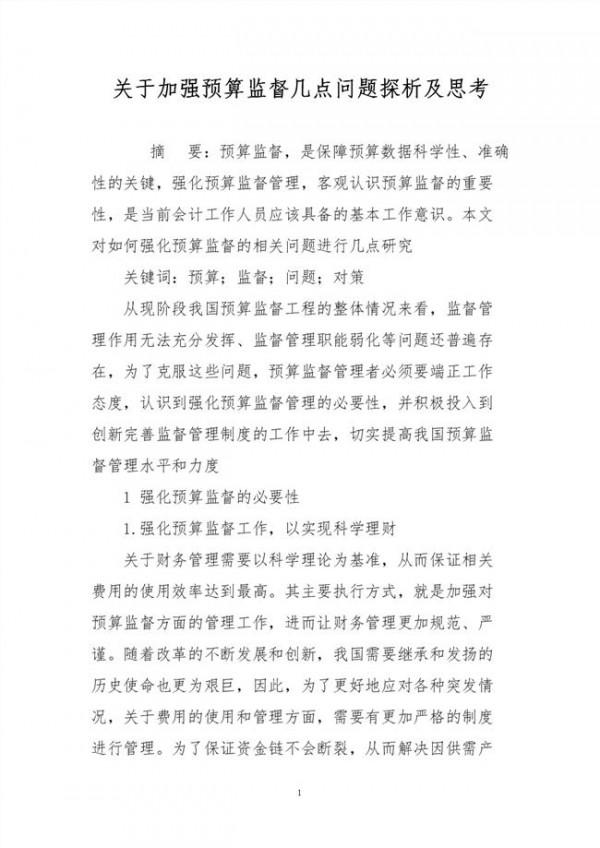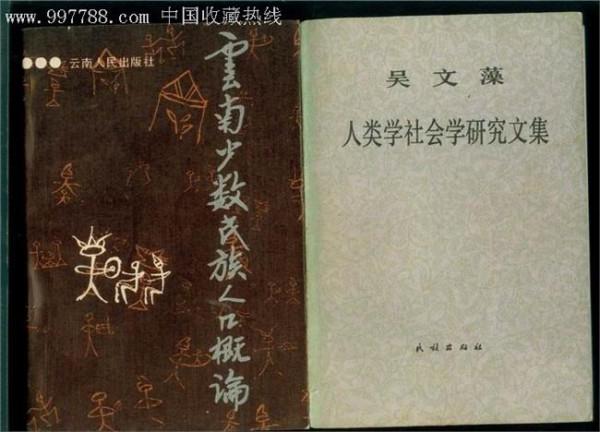消费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视角
夏建中(1952—),男,江苏省镇江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欧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和社区。
【内容提要】消费社会学研究近年来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薄弱。就消费社会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来看,该分支社会学在研究理论方面的主要视角有玛丽·道格拉斯的消费的文化意义、鲍德里亚的物品消费的制度与符号、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布丢的区隔与文化资本等。文章认为,现代社会的大众消费包含的社会意义,即形成“我们”的共同生活方式,从而维持与整合群体特征和认同感,以及展现某种“标志”和培养阶层归属意识的功能,应当成为消费社会学关注的重点。
【关 键 词】消费/消费文化/消费社会学
由于消费社会的迅猛发展,消费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不仅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表现形式,以致影响或反映出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不少学者认为,自19世纪以来长期统治社会学的诸如强调生产作为社会秩序和社会冲突以及社会意义的那些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至少,与消费有关的休闲、时尚、旅游、体育以及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所以,自19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消费社会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虽然消费社会学的研究是近晚发展起来的,但对于消费这种重要的人类活动很早就有人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可能最早存在于各种宗教教义和各种文化的早期文本中,世界上所有大的宗教都对诸如贪婪、奢侈、自私、嫉妒和欲望等有基本的道德判断,民族志的文本中也充满了各种力图教育人们抑制欲望、控制嫉妒的说教。以这些道德遗产为基础,关于消费的现代学术话语大多有一个基本的潜台词,即欲望对于社会是有害的,真正的需要必须与虚假的奢侈区别开,那些不受约束的现代物质主义,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对社会是有破坏性的。
关于消费的道德话语是对现代性、技术进步和货币经济进行批判的主要话题之一,如卢梭认为,人类本性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并且很容易得到满足;而现代人内心充满过多的欲望。新的发明逐渐“失去了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得到快乐,而是慢慢退化为发明本身变成真正的需要,直到对发明的欲望变成为一种乖戾,而不是对发明的占有成为一种快事。人类对于发明的失去感到痛苦,虽然对发明的占有并没有使他们快乐”[1]。
19世纪的经典社会学家普遍认为消费是理所当然的,但通常也是持抨击态度的。在最低程度上满足人们对食物、衣服和居住方面的需要以外,消费的欲求被马克思看做是资本主义诱惑导致的社会需要,是一种“商品拜物教”。虽然他承认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穿得更漂亮、吃得更好,但是他仍然认为这些行为是“动物的功能”。马克斯·韦伯认为,消费是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身具有意义的社会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消费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韦伯看来,在任何社会,对于物品消费的占有和掌控能力都是标志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社会,具有同样市场地位的人有着相同的购买商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实用主义地被置于对基督教救世的宗教信仰的境地,成为将消费等同于享乐主义的一个重要术语。齐默曼将空虚的现代生活与传统的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前者“自私自利”,是“一种及时行乐”、“直接的感官体验”和自私的“享乐性的愉悦”;后者是“使社会稳固、持久地得到满足,是利他主义的和对社区承担义务的”。[2] 齐美尔是第一个既讨论支持大众消费的时髦、新异所具有的吸引力和人们沉湎于声色口腹之乐,又指出消费者明显的不相干行为如关注时尚和购物,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生活中普遍现象的社会学家。不过,杜尔克姆则进一步发展了对消费的批判,认为,如果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经济放纵消费者无休止的欲求,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就会被摧毁。
所有这些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没有关于消费思想的经验研究,他们依赖的是通则化的、人类学的观察来支持他们的宏大历史观念。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更不重视消费,生产在他们那个时代更为重要。形成对照的是凡勃伦,他根据在美国的特殊社会实践,第一个对消费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过,他关于“有闲阶级”的著作也不是系统的经验研究。但是,凡勃伦的著作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学家较少研究消费的两个令人关注之点:对于“地位消费”道德方面的反对;女性在消费活动中扮演的卓越角色。由此可见,消费从一开始就被看做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和性别化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契约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支持者们力图将消费作为对现代性成功的最关键的度量指标。如果人们占有或消费了比他们的渴望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比那些生活在贫困和希望之中的人们要幸福。人类能够被收入的增长、财产的丰富或者其他客观的生活标准所测度的理论,是可以与道德主义的理论分庭抗礼的,虽然它的假设和结论受到反现代性理论的攻击。
总的来讲,全部关于消费的理论主要可分为三种,即心理的、文化的和社会的。
第一,心理学的视角。这种理论探索的是人格形成过程中或者早期家庭交往以及个人成长中的欲求和需要。消费是客体化和人格化的一种必经过程。这方面的典型研究是斯阵梯弥哈和罗兹堡-海顿在《东西的意义:家庭象征与自我》一书中的研究,他们赋予了中产阶级消费者一系列的功能,包括自我表达、创建个人历史、提供安全。消费反映了在寻求个人差异性的个体需要与寻求社会共同性和团体成员资格的群体需要之间的矛盾和平衡。其他学者也使用相同的理论,区别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提出在不同的背景中消费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目的。这种研究结合了近年来后现代与消费的反射性理论,关注的是主体性、经验、自我实现,以及消费文化中的创造性和嬉戏性的潜能。一句话,它主要关注个人。
第二,文化的视角。文化理论家们将消费看做是建立和表达主体间意义和身份识别的一种象征行为形式。某些文化学者强调消费的嬉戏、对抗和反抗的方面;而另一些学者对消费在文化中的作用持批判态度,强调消费文化取代了文化整合的传统形式,导致了消费者进入到无尽无休的自我陶醉的挥霍的循环中;更广阔的比较文化的研究者们则认为,任何社会中人们消费的原因是它建立了文化秩序、表达了观念或者赋予了新的环境以意义,使那些经验上模糊不清的东西得到了条理化和范畴化。
第三,社会的视角。心理学视角是在绝大部分属于内在的个人的人格、动机、欲求的维度上寻求消费的关键因素。与之相对,社会学的视角主要关注于群体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的视角发现了在社会互动中、特别是在竞争和群体关系中消费的一个基本动因。许多社会理论都可以回溯到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他提出了消费是受社会竞争和攀比刺激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用物品来显示自己,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被出身、阶级和社会等级所严格彰显。在传统社会,人们知道他们的地位,社会关系流行的是权利、责任和义务,而不是物质财富。物品是稳定的社会地位的符号,而不是地位竞争的工具。由于先赋地位的消逝,人们消费是为了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取地位,通过与那些更富、更有权利的人竞争和攀比,力图不断地获得地位。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社会区隔或群体中社会团结的需要是通过消费的展现而得到满足的,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需要也发生变化。布丢对消费的社会理论做出了极大贡献,他认为消费反映了品味和嗜好的基本结构,而这些品味和嗜好将不同的阶层聚集在一起,就如同它们将不同的阶层区分开一样。逻辑上讲,在任何有社会分层的社会,消费在维护和挑战社会等级与地位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社会理论的另一个分支强调的是,消费在家庭和亲属群体的整合中的作用。社会学消费理论更多关注于政治、市场制度、权利利益、价格和政策。
社会视角主要指的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在该传统内,主要的学者和研究视角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四种。
1. 玛丽·道格拉斯:物品消费的文化意义
在《商品世界:消费人类学导论》一书中,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对消费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是物品的用处?她们提出了两个功能。第一,物品是“用作使文化的范畴可被看见和稳定所必需的”[3](P59)。这种看法与经济理论中一般采用的消费理论模式相对立。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消费是个人的行为,是个人在满足自己需要方面独立自主的选择。经济学的模式固守在个人的层次上。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突破了这个界限,进入了更广泛的文化层面。这样,物品就不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范畴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而且以十分具体的方式固化了这些范畴。如同她们指出的,“标准的民族志研究认为,所有的物质拥有都携带着社会意义,都关注于将其文化分析的主要方面置于其(作为媒介的)用处的基础上”[3](P59)。
第二,物品“制造和维持社会关系”[3](P60)。这同样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视野,进入到亲属和人际交往的整个关系网络中。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举了伊文斯-普理查德研究的努尔人的例子,“婚姻联盟因牛的支付而产生,这个仪式中的每一阶段都是由传递和屠宰牛而加以标记的。伙伴的合法地位也是由对牛的权利和责任而界定的……Kraal人中牛的移动遵循的是谱系表中的路线……努尔人根据牛来定义所有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他们的社会习惯用语就是牛的习惯用语”[3](P60)。
对于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来讲,消费的根本功能不是以某种庸俗的使用方式来满足需求,如吃东西,而是其制造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食物不一定适合于吃,而是适合于思考。确实,也许我们会说,任何食物都能够满足我们的生物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一些人从来不吃猪肉,还有一些人从来不吃袋鼠肉,并不是它们不能满足我们的生物需要,而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所以,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指出:“如果没有选择和固定一致认可的意义的约定方式,社会最低公认的基础就会丧失。对于部落社会、同样也包括我们来讲,仪式服务于对某些意义的漂移的包容……按照这种观点,物品是仪式的附件,消费是仪式的过程,其主要功能是使事物早期未定型的状态具有意义……消费者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其选择的物品建构可以理解的世界。”[3](P65)当然,不同的阶级用不同的物品来制造他们自己关于世界的意义。
2. 让·鲍德里亚:物品消费的制度与符号
鲍德里亚对物品的制度很感兴趣,但他并没有对消费实践做较多的经验性研究。他的主要观点是:从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来解释需要,不能够恰当地理解当代的消费,需要应当联系物品的制度——对于特定具体的物品和特定的个人对特定物品的欲求,我们都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研究。
那么,需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多半认为,人的经济性赋予人以需要,并指引他们去取得能够满足他们的物品。对于这一观点,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曾给予猛烈的抨击,认为这种理论将需要局限在个人身上,因而不能抓住消费的社会层面。鲍德里亚认为,没有可靠的方式可以确定需要,需要看起来是以一种魔术般的方式出现,如果需要是天生的,那么它的扩大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讲,应当清楚的是,我们今天思考的需要要比几个世纪以前的需要复杂得多。所以,需要必须放在某个地方,而不是个人的身上。从市场和广告的实践来看,市场对于消费者表达出来的需要做出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能更值得关注的是厂家精心策划的通过广告来塑造消费者行为的努力。
对此,鲍德里亚指出,“至少从趋势上讲,这完全是生产一方的专政”,它“破坏了古典理论的基本神话,这种理论认为,正是个人在经济制度中实践着自己的权利”。[4](P38,P42)鲍德里亚坚持,我们不应当将需要简单地理解为由厂家制造的对某一特定商品的需要——如电视制造商也许希望促进消费者对一种新电视的需要。鲍德里亚认为,这不是关键,“真理不在于‘需要是生产之子’,而是,需求制度是生产制度的产物,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这里需求制度的意思指的是,需要不是在某时生产出来的与特定的物体相联系的东西。需要是作为消费的力量、是作为在更大的生产压力的框架内普遍的潜在预备被生产出来的”。[4](P47)
换言之,生产出来的并不是对某一具体物品的需要,而是为需要而需要、为欲望而欲望,是一种对任何物品的普遍需要。我们成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消费者,不是对于特定物品需要的消费者。根据鲍德里亚的看法,需要与愉悦和满足没有多大关系,消费看起来是加固了资本主义。
一般来讲,由于某种物品具有某种自己特有的性质,我们购买或者不购买,都要考虑其基本功能。比如,我们通常不会为了烹饪鱼而去购买洗衣机。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可能为了购买某种舒适或声望而去购买洗衣机或者微波炉。从这方面讲,洗衣机和微波炉是等价的。这样,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在物品的领域内,而是在象征的领域内;所以,消费者并不是为了具体的目的过多地消费具体的物品,也许更普遍的是为了大致的社会目的而消费符号。社会的差异变成了某种牌子的名称,在这里,恐怕没有什么理性-功利主义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需求。对于鲍德里亚来讲,商品的目的是传递,“商品和物品,如同词语和历史某一阶段的妇女一样,是建构一种全球性的、任意的和一致的符号系统,一种用需要和愉悦的不确定世界或自然和生物的秩序取代社会价值和分类秩序的文化系统”[4](P50)。
鲍德里亚将消费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逻辑结果。消费深化了劳工的被剥夺:在生存状态内,人们不会被空前增长的消费主义需求所玩弄,也不会被作为消费力被剥削。但是,越出生存,如果他们希望能够作为一种恰当的消费者生活,消费就迫使他们成为经济化的和受控制的劳动力。这样,剥削和控制就不仅仅发生在生产领域内,同时也发生在消费领域内。鲍德里亚并不认为消费是消费者欲望的自由实现,而是认为消费是被制度控制的另外一种生活,一句话,消费不是自由王国,而是强化依赖性的场所。他进一步指出,消费是19世纪发展的逻辑必然,“19世纪在生产领域发生了生产力的理性化过程,20世纪在消费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通过将大众社会化为劳动力,产业制度必然进一步满足自己,即将大众社会化为消费的力量”,“生产和消费是生产力及其控制力扩大再生产的同一个逻辑过程”。[4](P50)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不仅仅让劳动大众从生产上服务于这种制度,而且也从消费上服务于它。
所有的消费都是象征及符号消费的一部分。消费就是文化符号的消费或者是符号之间的关系。为了成为消费的目标,就必须成为符号。正是符号之间的关系使得差异得以建立或形成。这些符号或象征不表达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阶级)早已存在的那些意义,意义通常在引起消费者注意的符号和象征系统中产生,消费是既包括集体认同也包括个体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
对于鲍德里亚来讲,我们变成为我们购买的商品把我们塑造的那种东西,象征领域已经居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首位,“形象”比物质需要的满足更重要。换句话说,“我购物所以我存在”。
3. 凡勃伦:炫耀性休闲与炫耀性消费
事实上,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是第一部研究消费的著作。在此书中,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在他看来,答案十分简单,就是财富。换句话讲,财富的拥有可以给人们带来比金钱更重要的某种社会资产。一些人或许会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表面化或愤世嫉俗,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有不少道德方面的传说,讲述的似乎是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东西。但凡勃伦认为,这些传说不过是为了让穷人自我感觉良好些而已。
如果某个人拥有财富并且渴望社会地位,那么这个人必定要炫耀其有钱。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人如何炫耀自己的财富,从而使所有人能够看到并尊敬他呢?凡勃伦区分了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是炫耀性休闲;第二种是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休闲不能混同于强迫性休闲。凡勃伦认为,在工业化统治几乎所有人的生活之前,“有闲生活是金钱实力、因此也就是优势地位最简捷、最确凿的证明,它能够让有闲人士生活在从容和舒适之中”[5](P32)。所以,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炫耀性休闲是显示财富和要求社会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当财富显示已经成为基本的社会现象时,显示的形式会随着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凡勃伦指出,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5](P32),而不能不参加劳动自然是其反面。他接着指出:“摒绝劳动不仅仅是受到尊敬的、值得称赞的行为,而且成为保持身份庄重的必需。”[6](P41)劳动是不受尊敬的,标志着卑贱的社会地位。受尊敬的职业包括“政务、战事、体育竞赛和宗教类崇奉活动”[6](P40)。这些活动要付出很大努力,但都是休闲性活动。我们可以从体育活动中看出区别来,在网球和板球运动中已经逐步发展出球员与绅士的区别,这种区别已经将这个领域分为业余爱好者因而也是值得尊敬的绅士和专业人士因而也是不怎么受尊敬的球员两种人。对于前者来讲,运动是一种闲暇消遣,而对于后者来讲,运动则是赚钱谋生的一种手段。从社会意义上讲,参加同样的运动,比如同样的比赛和同样的球队,会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同样,参加其他的运动也是如此。
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避免参加任何生产性的劳动,所从事的活动本质上都不产生任何实际用处。他们不需要劳动,而且他们要尽量显示出自己不需要劳动的优越条件。在这里,良好的举止和礼节知识非常重要,对礼节的违反会被看成卑劣之人,明显地不是那种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消磨时间的人。如果你花时间去学习一种濒临灭亡的语言或者着迷于某种超自然的学问,那么就很好地显示出你的闲暇状态。从社会荣誉的角度看,学习死的语言比活的语言更有价值;从经济上讲,学习现代语言或许会显露出一种职业的因而也是声名不佳的倾向。
炫耀性休闲是一种对时间的消费,因此,如同对时间的非生产性消费是一种光荣的事情一样,对于物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也同样受到尊敬。凡勃伦认为,底层阶级对于物品的消费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再生产,只有上层阶级的消费才超越了生存,炫耀性消费的目的是显示自己的生活质量。某些类型的活动、饮食、服饰都是上层阶级所特有的,“关于饮食方面的礼仪上的差别,在酒和麻醉品的使用上最为显著。如果这类消费品代价高昂,其间就含有了高贵和光荣的成分……因此,由于刺激品享用过度而陷入沉醉或其他病态,反而带上了光荣的色彩,因此再进一步,它就成为那些有能力支付这种放纵的人的优势地位的标志,一些民族还把那种因放纵过度而造成的病态,看做是男子汉的特有属性”[5](P54-56)。
就像炫耀性消费能够通过向其他人的扩散来用于获得更多的声望一样,妻子和仆人也能够作为代理人,为了主人的荣誉以非生产性的方式消费时间,同样,还可能将主人消费的物品扩散到其他人那里。宴会和舞会可以很清楚地显示个人有能力支付那些寻求声望的竞争者的花费,所以人们很容易看到,诸如宴会和舞会这些场合,常常被用来作为对付那些炫耀自己以获取更多荣誉的对头的武器。当然,这些场合一般还具有其他的社会功能,如团结、娱乐等。
在凡勃伦时代,中产阶级也雇不起仆人。在这种情况下,“代理性的休闲和消费的职责就被转移到妻子身上”,凡勃伦称这种现象是“古怪的倒置”:“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中产阶级的主妇,为了家庭和户主的荣誉,仍然要代理休闲的业务。……人们发现男人竭尽全力地辛勤工作,为了其妻子可以以适当的方式为他执行当时一般要求的那种程度的代理性休闲”。[5](P62)面子和荣誉就是以这种方式维持的。那些骄傲地宣称“我的妻子不需要工作”的人的言外之意,就是她通过代表其丈夫消费时间和物品来炫耀他的财富。
当具有严格的阶级差别的封建社会让位于流动性更强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上层阶级可以被看成是社会所有阶级尊奉的社会标准的制定者。随着代代相传,普遍的消费模式就是对上层阶级生活方式模仿的结果。物品的消费成为人们显示自己财富和荣誉的主要方式,如同凡勃伦指出的:“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甚至极度贫困的也不例外——对惯常的消费会完全断念;除非处在直接需要的压迫之下,否则对于消费的这一范畴的最后一点一滴是不会放弃的。”[5](P64)但是,在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的主角是中产阶级。这是与封建社会不同的地方。作为社会存在,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看起来都继承了某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习惯:所有的社会都会为人们获得社会荣誉而提供严格的道德主义者认为的浪费标准,包括浪费时间或者浪费物品。
进入复杂的工业社会以后,比起为了显示金钱多少的休闲来讲,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任何人知道任何人的小型社会中,休闲活动是获得荣誉的主要手段;但在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就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所以,通常可以发现城市的消费比农村要具有更多的炫耀性质。根据凡勃伦的看法,炫耀性休闲与炫耀性消费的区别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