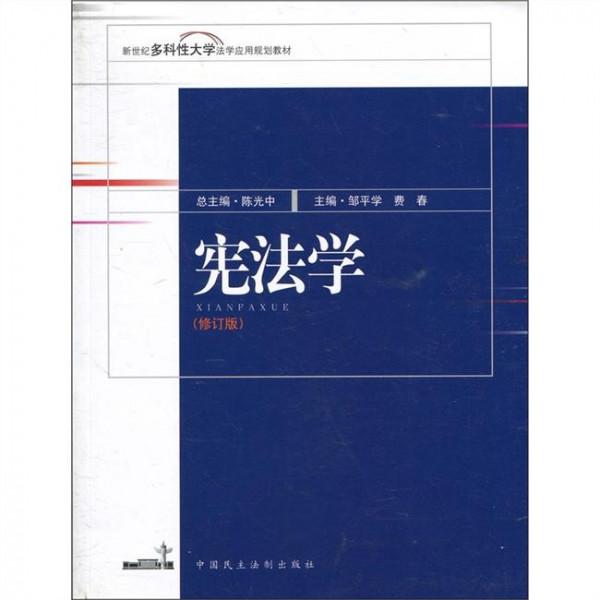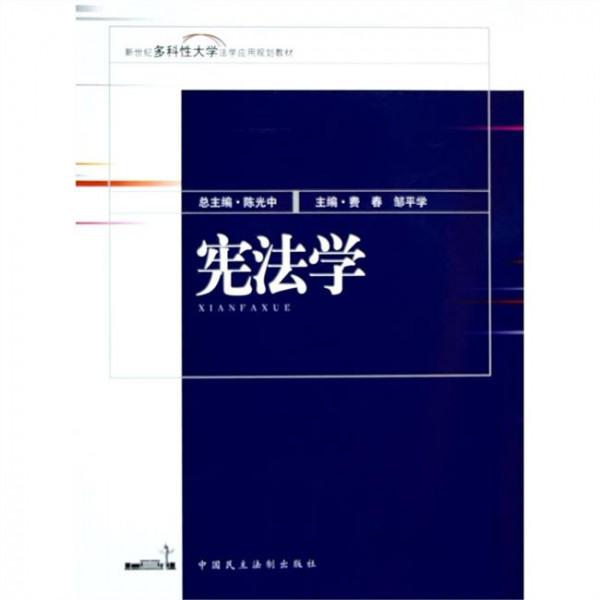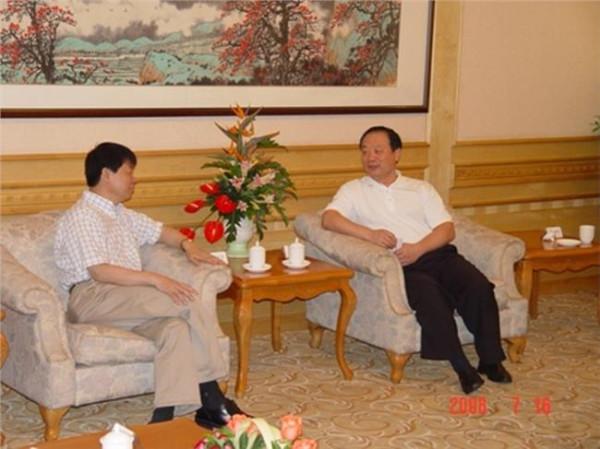宋海春宪法学 宪法学30年流变:从民主法制到依宪执政
编者按 10月25日至26日,宪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在成都召开。今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会学者对三十年来宪法学研究的梳理与总结,为我们理解我国宪法发展与执政党治国方式的选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的演变》
1949年,权利是后天获得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政权,也即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而这个进行国家统治的权力在革命胜利的初始状态下被认为就是权利。这种权利不是旧政府赋予的或同意的,而是人民经过艰苦斗争争取到的。因而权利的后天获得毋庸置疑。虽然,我们现在基本认同“权利天赋观”,不认同人的权利是其他人赋予的,但在新中国成立时,权利是后天获得的这一观念具有绝对统治地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甘超英撰文总结了学术界对建国初期的“权利”的看法,首先是它的后天性;其次是权利的阶段性和斗争性;三是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性;四是集体权利观,个人权利很少被提及。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开放,人们的权利观也发生了改变。
甘超英认为,我们的宪法权利的发展和权利保护的进步,均产生于对过时权利观的批判和反思过程中,在中国社会条件于三十年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是人权和宪法权利的研究,还是宪法权利的保护,都会迎来春天。
1982年,走向“法制”
1982年,中共中央作出修改1978年宪法的决定。
当时,北京地区的所有宪法学者差不多都参加了这项活动。草案拟定后,由《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供全国人民共同讨论。公众参与的热情之高、人数之众前所未有。有的报刊还出现过有关分析西方两院制和东欧国家践行的宪法(法律)委员会之类的文章。作为当年的草案起草参与者,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云生始终认为,1982年,那场关于宪法草案的全民大讨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立宪史上的辉煌。
“八二宪法”文本首次使用“法制”一词,并多次直接使用“依法”或“依照法律”,但是,“八二宪法在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与国家的根本任务时,其过多地考虑了权威与秩序的确立问题,忽视了立宪本来的目的在于权力限制。”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指出。
除此之外,立法技术问题也为宪法的实施设置了障碍。“八二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按理,应当存在着一个比较完整的“基本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莫纪宏发现,实际上,目前的“基本法律”制度作为法律形式不具有形式的完整性。
“基本法律”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是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式的法律地位在对外效力上有一定程度的清晰性,但当二者分别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关系时,就很难加以判断了。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关系,前者由全国人大制定,是基本法律;后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是“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现在律师法实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的法律位阶问题。
截至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现行宪法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共38件,在230件法律总数中占16.52%。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过的达16件,占“基本法律”总数38件的42.1%。而“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内部效力关系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关系比较模糊,按法律位阶解释的可能性,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基本法律的内容在法律效力上只相当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莫纪宏主张,要改变目前这种不理想的状态,必然要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前提,在制度上实现“基本效力”与宪法效力的同一性,并在法律形式上将“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完全分离开来,使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结构、功能和机制完全统一起来,以此为基础,才能推动宪法的有效实施。
不管是理念问题还是技术问题,宪法文本、宪法实施与宪法价值之间的鸿沟被有些学者归结为宪法的中国化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宪政建设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宪法体现的民族性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既包括宪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良性遗产体现得不够,也包括宪法联系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够。
宪法固然有其世界性的“通律”,若不和本国的传统文化、实际联系在一起,仅靠“舶来”一些基本语词,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的。
1999年,依法治国(依宪执政)
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我国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正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载入宪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叶中认为,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实质。因为从一国法律体系的效力位阶而言,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效力最强,是所有法律的立法依据和基础,因而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从宪法蕴含的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而言,民主是执政的基础,人权是执政的目的,法治是执政的保障,因而依法执政必须是依宪执政。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基础和核心。
至少,在宪法学界,“依宪执政”这一提法没有受到质疑。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邹平学进一步强调,依宪执政是制度、行为、文化的结合,它不仅是文本、制度意义上的,也是理念、文化上的。依宪执政意味着执政党的执政权力既来自于宪法的授权,得到宪法的保障,又受到宪法的制约,必须接受宪法的监督。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宋海春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他说宪法制定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通过立法建议的形式,把党的意志主张提交人民讨论,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制定为国家的宪法。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宪法理念对我国宪法的性质和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强调理念的更新,不仅是宪法实施的内在使命,经济基础的要求也不容忽视。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制定的,其遵循的理念也必然带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倾向,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国家化和对人性与公共权利本质的不合实际假设基础上的宪法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宪政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执政党的理念更新,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宪法发展以及法治建设进程。
毫无疑问,社会管理体制以及深层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是未来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趋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茂林提出,相应地,中国宪法的未来发展也将表现为对这一发展趋势的回应和指引。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应当也可以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
社会建设在遵循宪法指引的同时,也对宪法和传统宪法理论提出新的诉求。面对这些诉求,现行宪法需要完善,传统宪法理论需要更新。
关注和回应这些诉求是中国宪法及其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宪法学需要在社会变革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和理论的现实适应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建立更加紧密的、有效的良性互动关系。
2008年,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
在2008年宪法学研究会年会的闭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历数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十大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体系不完善;宪政理念还不够成熟;研究者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没有形成合力;从宪法角度和法律角度研究问题的界限不够清晰;宪法学者对违宪审查的推进比较消极;从宪法角度研究立法和司法改革的积极性不够;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的研究不足;对国家和公民基本关系的研究不够;缺少从宪法角度对司法改革的研究;对国家权力及其运行研究不够。
三十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宪法学者对宪法学研究缺陷的强调恰恰体现出这一学术共同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的参与热情。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把宪法学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方面的能力强化作为宪法学成熟的标志。
他重申,30年来,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法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的增长,相应地,事件的最终解决又会或多或少地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
目前,我国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开始呈现出一种互动局面,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林燕)
【相关稿件】
我国30年来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