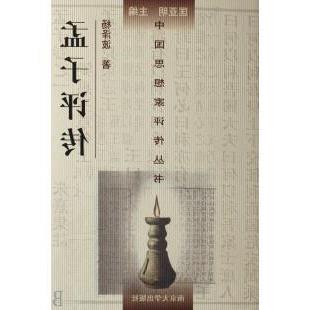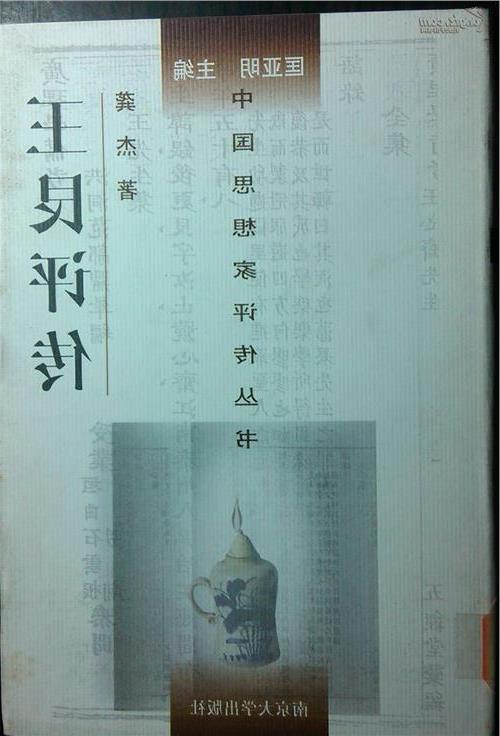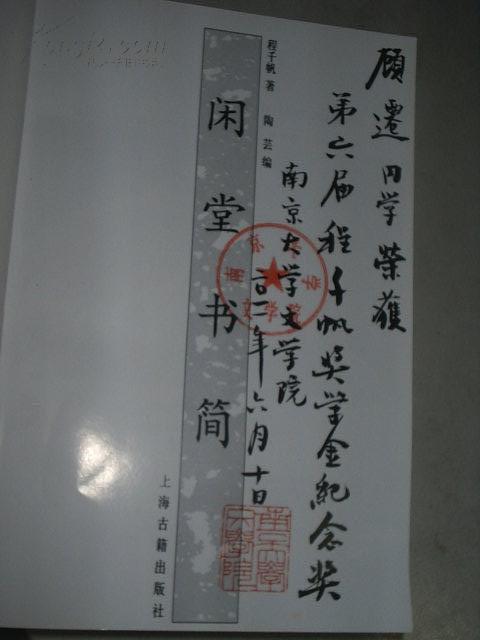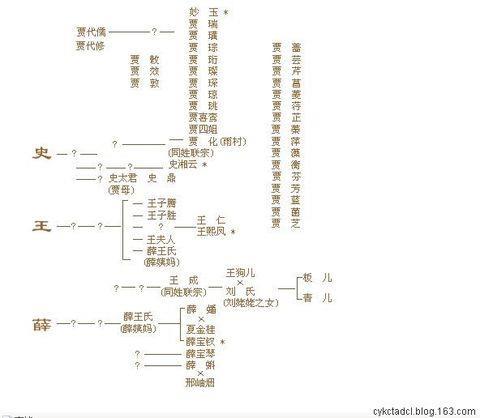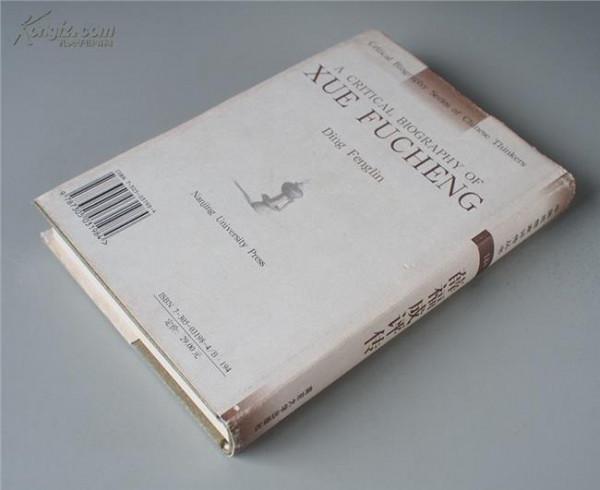匡亚明与程千帆 匡亚明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二三事
【周末报报道】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对“历史学”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依照这一观点,匡亚明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围绕《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做的一切,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人是什么”。
“没有困难,还有什么意思”
1982年,匡亚明主动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职务,任南大名誉校长。这一年,他已76岁。可这位老人心中藏着一个宏大的愿望——组织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若论编纂《丛书》的缘起,是当年在延安毛泽东与匡亚明的谈话。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潘群教授说,这件事最后能做成,也是经过一波三折的。
匡亚明退居二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胡耀邦打了书面报告,要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夙愿。胡耀邦批转胡乔木:请乔木同志协助匡老完成当年中央的决定。
接到信后,胡乔木在北京召集了专题会议,拟将《丛书》出版交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测算了一下成本,每部需要1万元。当时《丛书》计划不是出200部,而是2000部。2000万元的经费一时无着落,出版任务转交齐鲁书社。齐鲁书社的经费压力也很大。这样,报告转到教育部。教育部长蒋南翔批示,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匡亚明同志亲自领导。
成立中心的最直接任务,就是编纂《丛书》。
中心成立之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经费缺乏。后来,《丛书》由南大出版社陆续出版,江苏省新闻出版局陆续特批了几个畅销书书号给南大出版社,营利贴补《丛书》的出版。
匡亚明曾亲自筹措经费,潘群、卢央(中心党支部原书记,《葛洪评传》、《京房评传》的作者)二位也都有过“化缘”经历。
澳门基金会全职委员吴志良是南大历史系茅家琦教授的博士研究生。1994年,吴志良邀请潘群和周群(现为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去澳门讲学。中心经费紧张,当时他们的家庭经济也不那么宽裕,二人买了两张硬座车票,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珠海,在一家破旧的小旅馆的阳台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换一身干净衣服进入澳门。
一日,新华社澳门分社一位领导请客。潘群道谢。领导说别谢他,因为旁边一位先生给他们埋了单,他是一位慈善家。潘群再次致谢,出门,“坐在吴志良的车子里,我的心里开始‘打算盘’”。周群也悄悄碰碰潘群,潘群会意,但总不好意思提。这当儿,吴志良说:“潘老师你们也是,我让你们坐飞机过来,你们还是坐了火车!”潘群顺势开口:“不瞒你说,中心经费紧张,你能不能请那位慈善家给我们捐点钱?”潘群问过办公室,中心一年的办公费大约需要5万元,预计搞10年,要50万。吴志良听了,说:“50万太少了,我不好去跟他讲。这样吧,我们基金会给50万。”
在潘群的印象中,当年中心用公款请客只有一次,就是吴志良来南京。“匡老说请客请客,我说用公款了,匡老笑笑,人家给了50万,我们还不请客!”
“匡老对人厚,对己严。”潘群透露,匡亚明在德国访问,途中内急,他想反正快到宾馆了,就不找公共厕所了,免得付费。没想到好一会儿才到,“急死了!”匡亚明后来在一次闲聊中,不经意提起此事。但是,他回国的时候,自费给中心每个工作人员都带了一件小礼物。
2006年9月2日,在《丛书》整体出版座谈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了一句:匡老当年做这件事是遇到很大困难的。“这句话别人听了也就听了,我当时坐在下面,是深有感触的。”潘群说。
卢央介绍:“匡老是老革命,从不怕苦。他说:没有困难,还有什么意思!”
“匡老是个浪漫主义者”
组织《丛书》的撰写,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问题。
卢央笑称“匡老是个浪漫主义者”:“匡老要求高,要把全国一流的学者都拢过来,请他们认真地写。他跑到上海,跑到北京,跑了好多地方,一位位去拜访。”
匡亚明网罗人才的胸襟与胆识是有口皆碑的。在吉林大学时,他曾经三顾茅庐,礼请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出山任教,许下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非同小可的条件——不参加一切党内政治学习。在南京大学,他顶住政治风浪,力聘陈白尘、程千帆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
匡亚明要网罗一流的学者来写《丛书》,倒不是不要年轻人,他要的是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卢央当时50多岁,跟老先生比,算是“年轻人”了,但匡亚明交给他两项写作任务——《葛洪评传》、《京房评传》。
历来对京房作系统研究的很少,当代更是乏人。“但是匡老坚持要写,而且要层层剥笋,深入研究。我是在跟古书讨论,跟京房讨论,跟古学者讨论。”卢央苦笑,当时到网上搜索,几乎一条信息也搜不到。泡在图书馆里,有时一天一个头绪都没有,憋在那里,几天跳不出来。换一个思路,弄通一个问题,“高兴得不得了”。但弄出一个问题,又会牵出一串问题……
“一点一点写出来,花了好大的力气,自己蛮高兴的,现在我好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了,但是当时一点不好玩!”卢央说。
“你见过谁两个肩膀上各放一根扁担的吗?”
到潘群家采访,我一进门,他就指指墙上一个相框:“喏,匡老。”然后便说,“我在中心10年,10年时间,没做自己的学问。”他本是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曾和他的老师黄云眉一道主编国家重点图书《郑和下西洋》。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匡亚明把潘群从山东大学调来任副主任,主持中心日常工作。他跟潘群说:“把你调来,就是为《丛书》做服务工作的。你不要想自己的学问怎么样,不要想‘双肩挑’——你见过谁两个肩膀上各放一根扁担的吗?所以,你要全心全意为《丛书》服务!”
后来匡亚明物色了几个副主编,让潘群代表他一一把他的聘书送上门,并且一定要当面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
一天早晨,7:50,匡亚明把电话打到潘群家:“怎么搞的,中心没一个人接电话,连你都没上班?”潘群解释:“匡老,你打给我电话是8:00缺10分,那么你打到中心的时候应该在7:45的样子,上班时间是8:00啊!”不行,匡亚明说,万一有作者有事来电话呢?
从那以后,中心的同志轮流提前10分钟上班。
“我们那时候,不仅仅8小时在工作,匡老有什么事,随时会打电话给你。”潘群说。
“我们恨啊——匡老一个电话,我们骑个自行车到处跑!”卢央笑着说,“我们当时也50多岁了,骑车也不那么利索了。”
据说当年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职工到吉林大学教务处办事,教务处没人,匡亚明见了,对这位同志说,很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你先回去,明天我找人去你那里办这件事。回到办公室以后,匡亚明马上把门卫叫来,说你去把教务处的牌子摘下来,门卫只好照办。教务长回来后,看到牌子没有了,四处找,门卫告诉他,你去匡校长那里找吧。教务长低着头去见匡校长,被匡校长狠骂了一顿,说你这块牌子是吉林大学一张脸,你今天就是丢了吉林大学的脸。
匡亚明就是这样,对身边的人“凶”,对“外面的人”好。
匡亚明每年都要派人到各地去访问作者,问问进展情况,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听说谁有困难,匡老总是很急,想办法帮助;有人生病,他恨不得带人去看病。”卢央感叹,“匡老就是这种精神!”
“其如‘为人师表’何”
和潘群约好9月7日上午9:00见。9:00整,我刚到他家楼下,一位老先生走下楼梯,问:“你是周末报的记者吧?”他怕我找不到,特地下楼来接我。
中午12:00,采访结束,我在潘群家门口和他握别,请他留步。潘群执意把我送下楼。他说:“这也是跟匡老学的——不管什么样的客人,匡老都要把他送到大门口。”
吉林大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次,两个学生在校园散步,看到匡亚明,出于敬畏,想绕着他悄悄走开,却被匡亚明叫住。匡老告诉他们,见到老师要行礼。他让那两个学生重新从他面前走一遍。许多同学远远地围观,取笑,那两个学生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才好。于是,匡亚明向他们认真地示范了一遍,他们这才胆怯地从匡亚明面前重新走了一遍。听说,从那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吉大的学生见了老师都行礼。
《丛书》开山之作《孔子评传》的作者匡亚明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非常注意尊师重教。
另一方面,他同样非常重视“为人师表”。潘群参评教授职称时,匡亚明亲笔写的满满两页推荐意见中,只有四个字打了着重号,那就是“为人师表”。他在列举了潘群的一些优秀品德后,写道:“如其不然,其如‘为人师表’何!”
在吉林大学时,匡亚明经常去各教学楼转,看哪个教室的玻璃碎了,哪个教室的黑板坏了,他就用本子记下,等到月末的时候,他就再去看。如果那块玻璃还没有换,那后勤负责人肯定是要挨一顿骂的。“文革”时匡亚明被押回吉大受批判,在解放大路游行,路过理化楼时,匡亚明抬起头,问旁边押着他的学生:“同学,理化楼一楼大厅那块屏风修好了吗?”当时这个学生就哭了。他后来说,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没想到在那种情况下,匡校长还记挂着学校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无论是尊师重教,无论是为人师表,都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吧?
“伯乐千古”
刚开始,匡亚明坚持《丛书》要请一流的学者撰写,后来,他提出一个更具发展意义的思想:《丛书》要出书,还要出人,就是通过《丛书》,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匡亚明送过很多东西给潘群,潘群没有回赠过,“他会骂的”。匡亚明逝世的时候,潘群说:“这次我一定要送!”他送了挽幛,写了“伯乐千古”四个字。旁边的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潘群告诉大家,匡亚明生前跟自己说过一段往事,让潘群等他不在世后再说。
江泽民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来南大视察,接见匡亚明的时候,迎面伸手一指,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伯乐!”匡亚明一愣,江泽民看出他的不解,说:“你忘啦,在吉林的时候……”原来匡亚明任吉林大学(当时称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时候,一次副校长生病,匡亚明去医院探望。副校长跟匡亚明介绍,隔壁有位年轻人,很有才华,很有抱负。他说的就是留苏归来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江泽民。爱才如命的匡亚明主动到江泽民的病房慰问。德高望重的匡亚明的一番话,一直记在江泽民的心里。
“匡老总是鼓励人成才。我女婿在公安系统工作,匡老到我家来,见到我女婿,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成为大侦探!我儿子喜欢篆刻,匡老和他夫人就请我儿子给他们刻章。这对年轻人,是一种怎样的鼓励啊!”潘群至今说起来还很感慨。
拖板车的大学问家
那几年,匡亚明逢人必谈《评传》,在病榻上亦然。每次住院,潘群都要去陪他。有一次,他午睡醒来,潘群说:“匡老,我们约法三章,今天不谈工作,只谈轶事。”匡亚明笑着答应了。
潘群说:“匡老,我只在‘文革’中被关了45天,已经感觉到很受罪。你是老革命、老首长,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四次,受尽酷刑,‘文革’中间也一直受迫害。你觉得在监狱里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匡亚明说,最不自由的是“文革”中被关,动都不能动。“是啊是啊,最难受的就是坐着不能动!”潘群说,“但是后来看管我的人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自由活动一会儿了!”他告诉匡亚明,他当时和一个小偷关在一起,看守不在的时候,小偷从耳朵里掏出一个小铁钩,轻轻一拨,就把自己的手铐打开了,看守来了,他再把自己铐起来。处得熟了,潘群给小偷一支烟,小偷就帮他打开手铐,再给他一支烟,他再帮潘群铐起来。匡亚明听了很惊奇,他坐过那么多的牢,没碰到这样的“高手”。他说他坐过那么多的监狱,数“文革”中最不自由,如果当时遇到这样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倒是值得回忆的。
潘群讲得高兴了,说:“我被关了45天后,每天拖板车,从挹江门拖到石门坎,拖了3年。”
他问匡亚明:“匡老你拖过板车吗?”
匡亚明点头。他“考”匡亚明:“拖板车有什么诀窍?”
匡亚明微笑:“东西要摆好,不要前沉,不要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