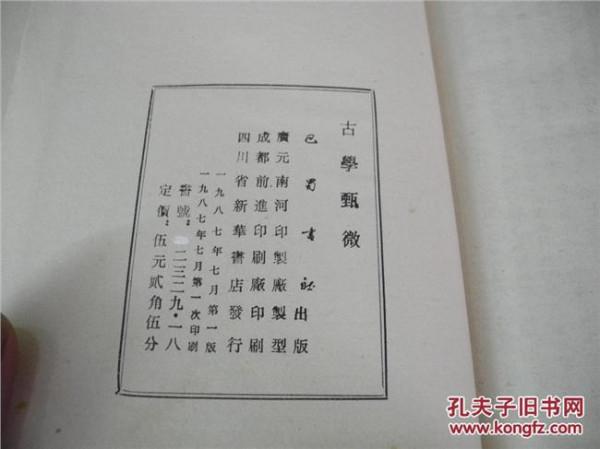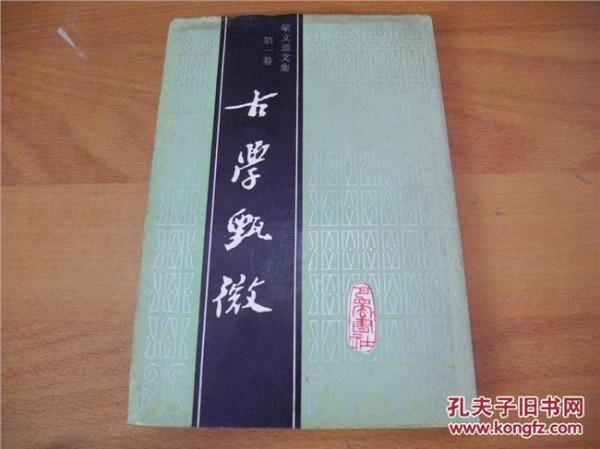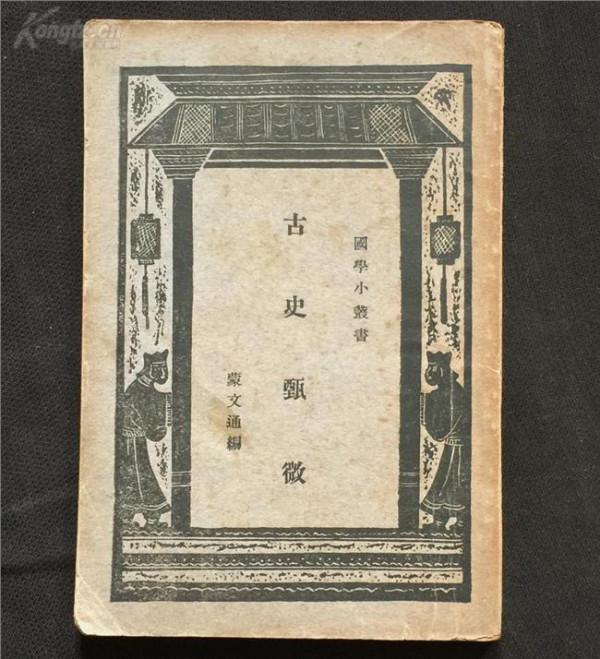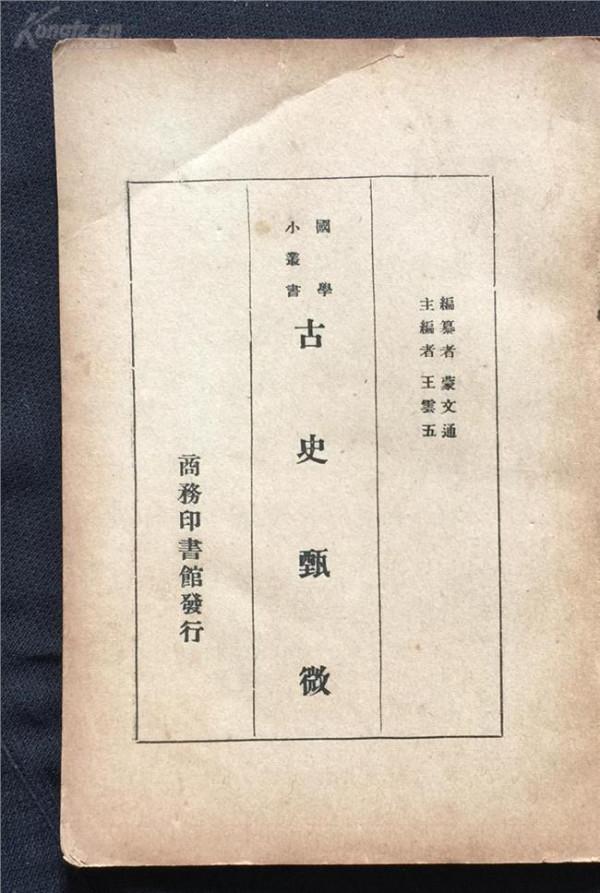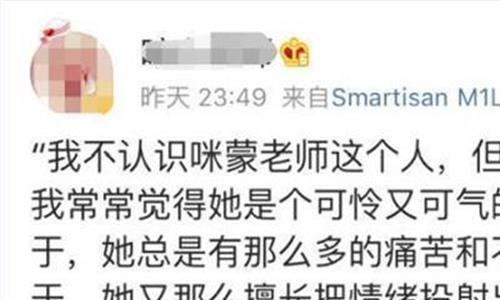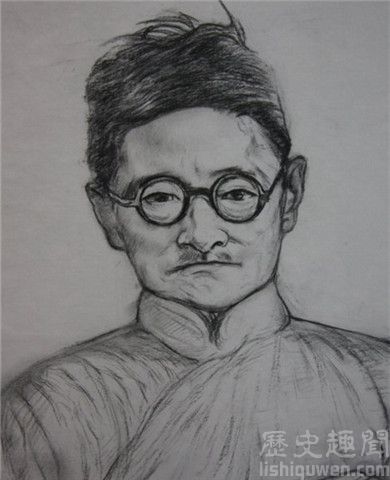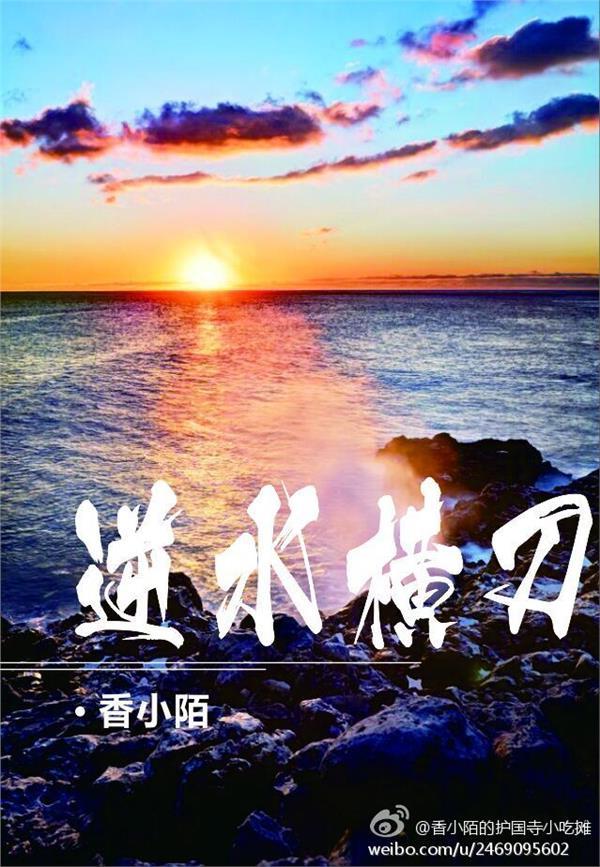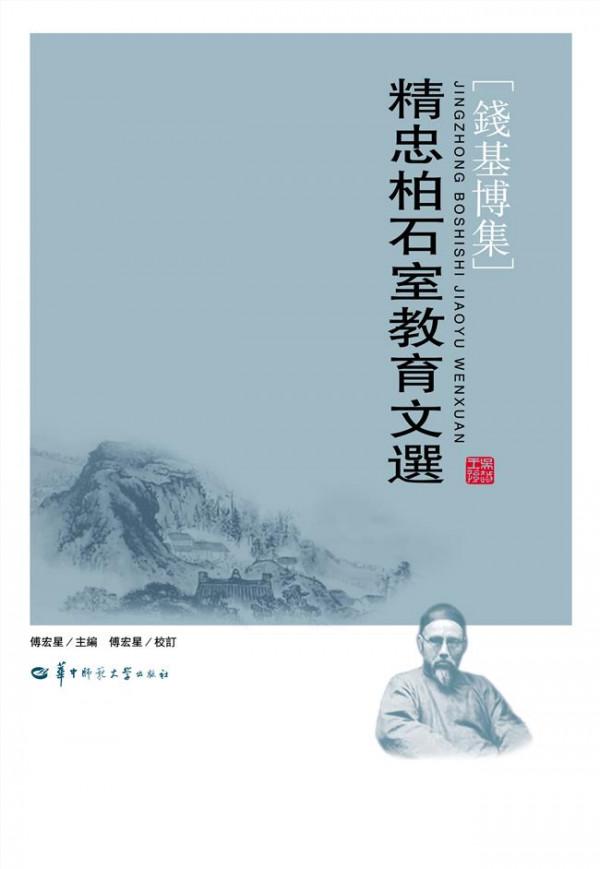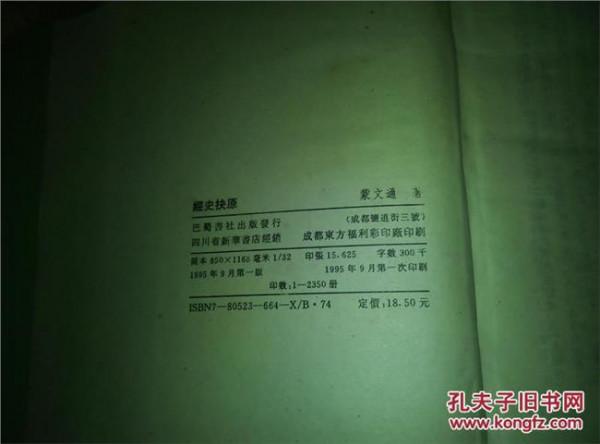蒙文通微盘 蒙文通与《古史甄微》
《古史甄微》的写作,乃缘起于作者本师廖平先生于1915年提出的一道命题。廖氏的命题只有百余字,而指示旧时所称的上古“五帝”皆以祖孙关系相传承的“一元论”观念靠不住,以为若“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蒙先生浸寻于师说十余年,采获既久,遂于1927年发愤撰集为《古史甄微》六万言。
《古史甄微》的最大特点,是由学术文化入手考察中国上古民族(部族)及其文化,引入了区系文化的类型学原理。第一,作者不同意清季经学上仍然主张“六经皆史”与“托古改制”的两派对于古史的衡断,认为二者皆“未可以上穷古史之变”,因而推论传说的“古学”有齐鲁、三晋、荆楚三方的分别。
第二,由三方学术之不同而逆推上古,自然得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结论。这既是《古史甄微》全部论证的主题,也是蒙先生发明古史的核心观点。
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
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古代黄河在今河北境内的下游流域)”,而“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实为汉族之故居。
第三,三族在上古时代更互为王,亦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作者指出,“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君长)”;“及其后世,炎族起于西南,黄族起于西北,而风姓之国,夷灭殆尽”。
炎族文化较朴陋,而其建国又早于黄族。“五帝”各传数十世,或数百千年,至夏代始归于和睦。第四,作者又说,上古“中国之中心,前后有三,以次自东北而西南”:始在鲁、卫故地(今鲁西南至豫东北地区),后移于三河(伊、洛、黄河交汇地区),再后乃移于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
以“五岳”言之,古人最早以泰山为天下之中者,即是都鲁、卫之事;后以嵩山为天下之中者,则为都河、洛之事;再后以华山为天下之中者,乃为周人都丰、镐之事。
此即“我华族自东而西”,亦即“汉族自东而西之迹”。第五,作者强调,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营耕牧渔猎,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黄族为游牧民族,故“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长于立法度、制器用”,凡实用器物皆自黄帝始创,“颇似罗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组织”,然“皆率神农之教”,又“崇幽灵、信鬼神”,“长于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旷浪漫”,“颇似印度”。
中国文化即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故谓“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早期开化的大体过程是“起于渤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
蒙先生划分中国上古民族为三系的创说,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其一,他力主中国上古文化的发展大势是自东而西,明显是对晚清以来曾经甚嚣尘上的中国早期文明由外域输入并自西而东传播的“西来说”(蒙先生称之为“中国民族西元论”)的强力反拨,并完全摒弃了此说背后所隐藏的外域文化中心论和中国古文化后进论的观念。
其二,彻底解散传说的“三皇五帝”皆以祖孙亲统一系相传的古史架构,对以往过分强调华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的传统观点也提出了挑战。其三,首次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对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创始之功。
当《古史甄微》最初发表时,古史辨学者曾以其对旧史体系的破除而颇引为同道。然蒙先生对传说史料的甄别,又与古史辨学者大相径庭。其《自序》说“百家杂说,自成统系,若或邻于事情;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又说“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翻不免于理想虚构”。
即如所举《孟子》书中的十四件古事,他也以为“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因此《古史甄微》之作,信传不信经,为文波澜时起,新解屡出,而所用史料亦纷然杂陈,甚至纬书之言亦不放过。
这与作者治古代学术史、思想史,仍以鲁学、儒学为正宗的主导理念,又当分别来看,未可混同。事实上,蒙先生对泰族文化的推崇,本意也是要证明儒家义理“实为中国文化之精华”,正为“东方之东方文化”,与法家之为北方文化、道家之为南方文化本自不同。
故其《自序》末有言:“《庄》、《老》沉疴,若在膏肓;荀、韩所陈,有同废疾;思、孟深粹,墨守无间。必读而辨之,而后知东方文化之东方文化,斯于学为最美。”《古史甄微》别有专章,各述夏、商、周三代之兴替,以见泰、炎、黄三族文化的衍传和流变,可与此旨通观,而对书中具体的结论正不必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