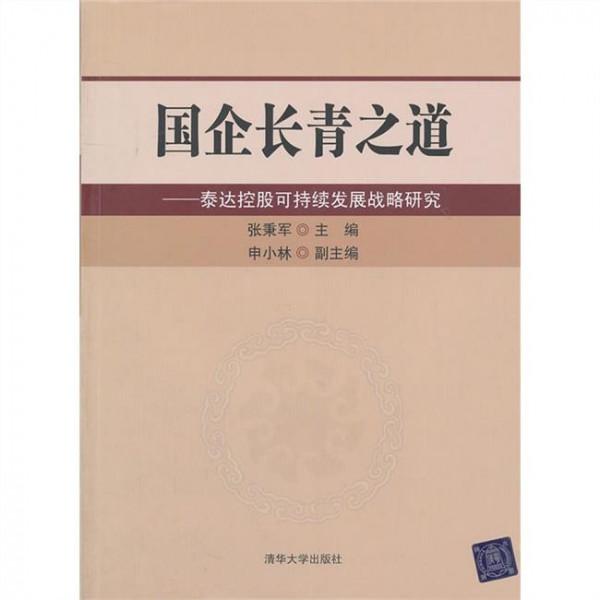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 酸甜苦辣的回味张道藩
我出生在贵州西部盘县城郊一个清寒的家庭。在前清时代地方上的人,虽然都羡慕我们那世代书香门第,却是暗中又在那里笑我们贫穷。在我年幼的时候,本族大部分的人还是聚居在北门外崇山营张家坡三大进古老的住宅里。
我们有三个大宅院因此也有三重大门。在那些大门上除了挂着六块“进士”、四块“文魁”的横匾而外,还有满清皇帝颁赐旌表节孝的“贞寿之门”、“德寿双高”等直形的匾额。第一道大龙门前面是一个大院坝,左右两边排着七八对桅竿。
那都是祖先们得过进士举人功名的标记。至于族人当年先后中文武秀才或武举人那就更多了。由家谱记载里我知道一百多年以来族中好多位祖先们曾经先后在四川、云南、浙江、湖北、江西和本省做过官。
大官只做到知州、知县。小官则州判、教谕、巡检等等都有。我的祖父是个进士,分发在四川,还没有做到官在他卅二岁时就逝世了。我的父亲成了孤儿,自幼失学,虽曾苦读,后来始终没有得到过什么功名,也没有做过清朝的什么官,但却教出了许多有成就的学生。
我既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幼时自然免不了一脑子的读书、求功名和做官的想法。到我十多岁的时候前清的科举考试废除了,各省先后兴办了新的学校(当时一般人都称之为“洋学堂”),我的思想才有一些转变。我在十四岁以前读的书就是《千字文》、《龙文鞭影》、《千家诗》、《幼学琼林》、《对子书》、《四书》、《诗经》等书。
当时的老师只教学生们读而不讲。我的悟性又差,所以读了许多书都不能完全了解,也得不到读书的乐趣。后来父亲教我读了当时编的许多新知识的书如《启蒙歌略》、《地球韵言》、《韵史》(以韵文编写中国简史)、《万国都邑歌》等等。
因为是韵文,易读、易记,也容易了解,我才对于读书感觉有兴趣。我以后许多年能够随便对人说出任何一国首都的名称,他们都很惊奇。
其实不过是我把《万国都邑歌》读得烂熟而已,并没有其它的奥妙。直到宣统元年一位私塾老师教我读了两本虚字会通法(也是当时的新学书之一)和一本短篇论说(记得是邵伯棠著的),我才渐渐的懂得什么叫做文章。同时因为对于之、乎、也、者、矣、焉、哉,以及且夫、呜乎、嗟乎,等等虚字的意义大致有了了解,回头再读过去读过的经书也就容易懂得多了。
到了宣统三年我考入了本县的高等小学,(照当时的学制高小四年毕业。等于现在高级小学二年加上初中二年。)课程中有读经讲经,才有老师给我讲解《孟子》和《诗经》。此外还有一门功课叫做《修身》。我记得我所读的修身教科书是诸暨蔡元培著的《中学修身》。
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所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从好一方面说,是给我打好了一些中国固有文化的底子。从坏的一方面说使我后来对于西洋文化很感觉不容易接受。这自然就是所谓“先入为主”的关系了。
后来因为族中有两位长辈在日本留学常常寄回《新民丛报》等刊物,读了以后增加了不少的新知识。辛亥起义各省先后光复,在国父和各革命先烈先进奋斗牺牲从事建立中华民国的一段时期间,我由报刊上读到许多有关革命的文告和通电,使我对于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满清帝制政府和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民国”有了更多的认识。我的思想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可是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后来会参加一种革命团体,成为一个革命党员。
(一)、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
民国成立以后我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其次,因为读《新民丛报》,由爱其文而敬佩其人的,是梁任公。再其次,因为与自己家乡有关的,是蔡松坡和唐继尧。稍后则对黎元洪、黄兴也很佩服。以为他们都是了不得的革命人物(可是后来黎元洪使我非常失望)。
当我知道我族中有一个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叔叔家瑞,回到本省与王文华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反对当时的贵州都督刘显世,我非常的感觉骄傲。但是使我和革命党直接发生关系的人,却是我的家骏七叔。那已是民国五年春季的事了。我民国三年在本城高等小学毕业以后,因为无力量到贵阳升学去进中学或优级师范(每年只不过需费二三十银元),只有苦闷的待家里自修。
不久以后,邻县普安所属的罐子窑地方一个姓易名晓南的绅士开办了一个私立两等小学(初级和高级小学),聘我去当教员。此地离盘县有九十华里,乘滑竿须两天方能到达。月薪是当时的现银十二元。
(当时物价一银元可买三百个鸡蛋或最好的煤炭一吨,猪肉两角钱一斤。)我在不得已而求其次心情下接受了这个职务。于民国四年二月到罐子窑去教书。那年我十八岁,那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同时也是第一次做事赚钱!
本城的人因为我能够每月赚十二块银元非常羡慕。我所教的功课是两级的算术、音乐、国画、习字、体操和初级的国文。这些功课,除了体操而外,我都还能够胜任。因为我自己在高等四年八个学期考试有七个学期考得第一,毕业考试也是第一。
那时去教小学正是现蒸热卖,当然可以应付的。我记得当时最难应付的不是所教功课,而是高级部的几个比我年纪大三五岁不等的五六个学生。有一个年龄廿四岁的学生最会捣乱,事事和我为难,倒使我提高了警觉,时时小心准备教材。
结果总算没有被他难倒。其实此人相当聪敏,可惜不知道把他的聪敏,用在用功读书上,后来终久因为几乎打死一个同学被学校开除了。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于我有很大的益处。第一使我因小心准备教课,觉得对于过去读过的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第二使我有机会学了一点与同事们相处的方法。第三使我由报刊杂志里知道更多有关革命的事情。第四使我多读了几部小说。(在高小未毕业以前先父只准我读过一部《三国演义》,在罐子窑我读了《水浒传》、《列国演义》、《红楼梦》、《花月痕》、《二度梅》、《西游记》等小说。
)因为已经会留心时事的关系,所以知道了中国二次革命的简单情况。也知道了袁世凯如何摧残当时的革命党和筹安会那一些人如何拥戴袁世凯做皇帝。
又知道袁世凯如何解散了当时国会而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我的光炜五叔是当时国会参议院的议员,国会被解散后,他应云南督军唐继尧之约赴昆明做事。由北京回籍过罐子窑住了一夜,告诉我许多有关当时政治上变化的事情。
)在民国五年的春天我的莲舫七叔要我替他保管一包秘密文件,并且告诉我不能让家族亲友知道这件事。万一泄漏出去让县长知道了,我们可能有性命的危险。我问他要我保管究竟是什么文件?他说是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志愿书和誓词。
随即打开给我看,并且说他已经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同时告诉我领导中华革命党的就是创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这个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恢复共和国体。
他的任务是要在盘县找五十到一百个人加入中华革命党,他希望我将来也参加做一个党员。我知了这件事以后非常兴奋。在我保管这些文件期间,他曾经先后找到廿多人加入中华革命党。到了阴历六月中旬,五叔由昆明有信给我,要我立即赶到昆明,随同他一道去北京读书,我才将这批文件交还了七叔。
在我离家前两日的一个深夜,七叔教我填了中华革命党的志愿书,又盖了指印,并令我在家堂祖先神主牌前面小声读了誓词,又打了指模,然后他将这两种文件收好,又告诉我说:“你从此以后已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了。
你到北京要绝对保守秘密,不能和任何人说到你加入党的事。以后怎样和党取得联络我会想法子写秘密信告诉你,或者介绍同志去找你。”可是自从此次和七叔分别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任何消息。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华革命党的党证。
(二)、由平津转往塞外就业
民国五年夏天在袁世凯洪宪皇帝死了以后,国会又恢复了。我追随着五叔婶及道同弟由昆明乘滇安铁路到海防,改乘船经过香港到了上海。五叔因为要赶在参议院复会日期前抵达北京,所以由上海乘津浦铁路火车先去北京。
我带了仆人和许多行李由上海乘船到天津转赴北京。因为替五叔送贵州土产礼物给住在天津的严范荪先生,乃得拜识了这位老教育家。他在前清光绪初年曾经做过贵州学台,五叔是在他任内得中举人的,所以成了他的得意门生。
严太老师见了我时非常高兴,问我到北京后是读书还是做事?我告诉他是读书。他说:“南开学校是我和几个朋友创办的,我希望你到南开来读书。你的叔叔是我的门生,希望你也是我的学生。”这是我后来进南开学校的来由。
民国六年张勋拥护满清废帝溥仪复辟重做皇帝,又把国会解散。五叔失业,对助我读书发生了困难。恰巧在暑假期间笏香五叔祖被派任归绥(即后来绥远省)、察哈尔两特别区(此两特别区当时尚未成行省)烟酒公卖总局的总办。
把我带到归化城总局去工作。因此我在南开读书中辍了。这个总局之下只有张家口和包头两个分局比较是好缺。张家口局长给了当时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某,而烟酒公卖总署署长交下来的魏毓生先生只能出长包头分局。
因为当时包头及其附近几县范围以内有大土匪陆占魁,到处抢劫杀人放火,又包头一带鼠疫盛行,所以魏先生不愿去。后来因实无其它更好位置可得,乃不能不去,但找不到助理人员,因为谁都怕被土匪抢劫杀害;更怕鼠疫传染死亡。
所以魏先生竟以“如果总办让道藩到包头去帮我的忙我就去,否则我只好打道回北京。”五叔祖不得已只好同意让我和他去。因此我到包头做过两年工作。初到半年我是个办事员月薪六十元。后来因为我工作成绩不错,改派为科员月薪一百元。
每月除了薪水之外,我还可以和分局内同事们分享向来税收机关所有的漏规规费。每月多则得五、六十元,少亦有二、三十元。有此种收入已够我自己一人的开销而有余。所以我每月的薪水除了以一小部分寄奉父母贴补家用而外,就存储起来作为再读书的用费。
(三)、响应勤工俭学决心赴法
我除办公之外不特温习旧课,同时还读函授英文和日文。我当时本有留学日本的打算。等到民国八年秋天回到北京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进行之际,许多留日学生因为痛恨日本侵略中国,都返回祖国了。
因此我也打消了留学日本的原意,再回南开学校读书。在返校之后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看到我两年前的同班同学们都升班了,我的自卑感使我不能安心,也不甘心再读下去;每天花很多的功夫和同学们作反日讲演宣传或参加其它爱国活动。时间一久,自己觉得终日这样做不能好好读书,不是根本爱国之道。
正在我傍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吴稚晖先生到南开作讲演,鼓吹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颇为所动,居然大胆的到吴先生所住的旅馆去拜访他。承他亲切的接见,诚恳的指示,并且介绍我给南开第二宿舍舍监姜更生先生;请他指导我如何进行赴法勤工俭学。
当时的姜先生也和吴稚晖一样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我当时对于无政府主义并不甚了解,可是我对吴、姜两先生都很尊敬。在和姜先生两次亲切晤谈之后,我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十月下旬我向学校请了两星期的假,到上海去办护照和洽购船票。一切应办的事完毕以后,我到杭州去省视五叔祖父母。
五叔祖头一天领我乘船游览西湖名胜地。我谈到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他开始并不赞成,后来因为我坚决表示非去不可,他也就不再反对。不料我第二天去向他们辞行的时候,五叔祖忽然坚决的反对我到法国去。
我仍然坚持原意。五叔祖见我意志非常坚定,教我必须先发电请求我的父母同意之后方可前去。我告诉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去电表示,我的父母是不会允许我到外国去读书的,因为他们正来信要我回到家乡去结婚。
”五叔祖母对我说:“你这孩子真淘气,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独生子,你不告知父母就到外国去,你的父母对你这种不孝的行为不但不高兴,而且还会误会我们为什么不阻止你。”我笑笑回答:“我希望我父母能够宽恕我这一次的不孝,我到了法国之后会详禀父母,说明你两位老人家都曾经阻止过我的。
”他们两位老人也只好叹气。最后五叔祖说:“你一定要去,将来如果需要我帮助你的时候,只要我力量所及,我会帮助你的。”我表示了感谢之后,乘当天下午的火车到上海,住了一夜,就乘津浦铁路火车回到天津。
我到学校要求晋见校长张伯苓先生,将我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告诉他,满以为会得到他的赞许,那晓得他竟大不以为然。他问我:“你学过法国语文吗?”我答:“没有!”他说:“你这孩子真胡闹!
法国话都不会说几句,你到了法国怎么能做工?又怎么能俭学?”我说:“那些华工到法国以前不是也不懂法国话吗?”他说:“他们是去做简单的苦工,只要身体强壮吃苦就成。你是想去勤工俭学,你必须能够得到酬劳比较多的工作,才能达到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的目的。
你如果只想去做一名工人,那又何必到外国去?在中国做工不是也一样吗?看你身体这样瘦弱,恐怕想做一个单纯的工人还不够格呢?”我说:“校长,我的护照船票弄好了,无论如何我愿意去试一试!
”他见我意志极其坚定,点了点头说:“试一试!这句话说得好。你既一定非去不可,那就去试一试吧。天下许多事只要有决心去试,总会有成就的。我希望你将来会成功。”接着我获得了张校长的允许离开了南开。于十一月中旬就到上海去准备行装,候船起程去法国。
(四)、起程前晋谒国父求教
在候船期间,我们认识不久将要同船出国的十二个青年共同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当时正在上海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说明我们转赴法国勤工俭学,请求赐一机会让我们晋谒求教。我们当时不过想试试看,原不敢想国父会约见我们的。
那知道两天之后得到回信指定日期时间教我们到他莫利哀路的公馆见面。我们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到了要去晋谒的时候,临时又有六个同船的青年朋友一定要跟我们去见国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胡胡涂涂的带了他们一同去。
到了孙公馆才向孙先生的秘书说明白临时又加了六个人,幸而没有遭拒绝。我们先被引导进入一个大客厅,在一个长方形的大餐桌似的桌子周围坐下。不一会儿国父微笑着走入客厅。我们大家起立鞠躬致敬。
国父点头回礼,以右手示意说:“请坐,请坐!”我们大家遵命坐下。国父按着我们呈上的名单,一一叫我们的姓名。他称我们为“某君某某”,我们一一应名起立。他看了看,点了一下头,起立者再行坐下。国父又分别问我们某人到某国去学什么?我们十八个人当中,除了五个答说是要留学英国而外,其余都说是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
至于去学什么?我记得除了三位说到英国学工科,两位说学法政,和要去法国的有两个说打算学法律、哲学等而外,多数都只说等到了法国先学法国语文,到能听讲的时候再看情形决定。
我们事前商量好了由一位比较年龄大的黄某代表我们陈述求见的意思。他的话大意如下:“孙先生,您是领导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建中华民国的伟大政治家,承您今天允许我们晋谒求教,我们非常感谢,也认为是莫大的荣幸。你对于欧洲各国的文明、政治、学术都有深切的了解,我们恳求多多给我们指示,使我们知道怎样的好好求学,将来能够对国家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
国父微笑着对我们说:“不管你们到那一国去留学,也不论你们将来学什么,只要你们能够刻苦用功切切实实的去学,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满清专制政体,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可是我们的立国的基础还没有巩固,许多官僚、政客、武人,对于共和政体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才有袁世凯推翻共和政体要做洪宪专制皇帝的可笑事件发生。
袁世凯现在虽然已经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
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你们也要知道中国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事事都受世界列强的干涉和压迫。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知识份子,必须要大家齐心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
我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应该都是最优秀最革命的知识份子。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许多留学好的,只知道读死书求知识;其次的只学了一些外国学术的皮毛;再次的只学得些外国人的生活享受和恶习。最奇怪的是大多数都不知道过问政治。
比较起来还是留日留法的学生好一点。比如过去留法学生在巴黎和平会议(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时的表现和最近留日学生为了爱国运动,宁可牺牲学业,离开日本,回国参加反日工作。最不行的是留英学生,他们多半误解,以为英国人民不管政治。
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在留学期间或者回国以后,也就以为参预政治是不必要的。因为英国人民平时只靠他们的政党替他们过问政治,而很少直接参与。但是他们留英期间如果遇着英国一次大选,他们得到机会仔细观察就知道英国人是怎样疯狂参加政治活动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到外国去不要以能读死书求得一点知识为满足。你们应该除了专门科目而外,随时随地留心考察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这些活的知识于你们学成归国之后,对于国家社会当有很大的贡献。(国父当时的训示,我原有日记,可惜已于对日抗战时失于南京,故现在只能记其大意。)
国父训示完毕看看自己的手表,我们知道这是暗示我们接见时间已完,我们就起立告辞。大家对这次能够会见国父,又得到宝贵的指示,都非常的兴奋。我自己更是永远不能忘记。我记得当时国父稍带广东口音的国语,我几乎一句一字都听得懂。
国父那种安详尊严,而又平易近人的诚恳态度,使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晋见国父。因为到我民国十五年六月归国,国父已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直到十八年国父灵柩奉安南京时,方得瞻仰国父的遗容。可是国父当年接见我时,他那里会知道我后来竟成了他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呢?
(五)、改入伦敦大学习美术
我和四十几个赴英、法留学的青年(当时同船的人,现在在台湾的有台大教授盛成和立法委员苏汝全和我三人),于十一月下旬某日,乘一艘名瑞秀士,载重七千多吨临时改装可载数十个乘客的英国小货船离开了上海。
据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朱少屏(好像是这一姓名)告诉我们,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以后载留学生出国的第二艘轮船。我们临时在船上组织了一个同舟共济会,每星期有一次讲演,又有一次同乐的聚会。
我还记得一位在广东传教廿多年的英国牧师,用极纯熟的广东话给我们作了一次传教性的讲演。当他讲演时发现我们听众没有注意听,有的交头接耳小声说话,有的皱眉头,有的看着他微笑,他颇有误会大家不原听他传教式的讲演。
事后他问我究竟是什么原故。我告诉他说:“你的广东话虽然说得很好,但是听众之中除少数五六位两广的同学而外,都不能听懂广东话,你算是白费气力了!”他才恍然大悟叹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广东话在中国是通行的呢!
以后我要能来中国,一定要努力学北京官话了。”另有一次是盛成先生对我们讲宗教哲学。他准备一大张纸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里面又有几道渐渐小到中心的圆圈。我只记得他指着为我们讲有关佛教的某种问题。
听众的秩序也不好,居然有人睡着了。其实并不是他讲不好,实在是在座的对于宗教哲学而无研究,不感觉兴趣。再有一次是留了小八字胡很像日本人的唐应铿先生,用他带广东口音的官话给我们讲他所知道的英法各国的风俗习惯和礼节。这次的讲演很成功。因为他所讲的正是大家要知道而且不久就会有用的。
我们所乘的船原来是要在法国马赛靠岸的,所以有那样多的留法学生订乘这艘船。开船前两天忽然通知乘客赶快办到英国的过境签证,因为船公司有某种原因该船可能不在马赛靠岸而直开伦敦。
因为那时由上海赴法国的船很少,购票也不容易,所以留法的人们还是决心不改乘其它的船。幸而得到环球中国学生会、上海交涉署和轮船公司的帮助,我们很快的都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签证,如期成行。因为轮船太小,船过中国海、印度洋,和绕过直布罗陀海峡经大西洋到伦敦的几段时间,轮船颠摆得非常厉害。
许多乘客不只是呕吐,简直像害了重病一样,卧床呻吟,既不能也不敢进食。由上海到伦敦船行了四十多天,一九二O年一月九日到达伦敦。
船到提尔布勒码头出乎我们意外的有石瑛、吴筱朋、黄国梁、任凯南等四位留英的老同学来接我们。领带我们乘火车抵达伦敦市中心区,把我们带到一家中国楼的饭馆。一面吃饭,一面谈话。他们把许多应该注意事项告诉我们。甚至于吃西餐时如何用刀叉,吃汤嚼东西不能有声音等,都当场表演教给我们。
最后告诉我们自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军队中原来是工人的都复员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因此要找工作非常困难。提醒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要作郑重的考虑。
因为自己既没钱,单欲勤工已不容易,又何能以工作所得来实行俭学呢。结果有七八个人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而留在英国,我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得世交曲荔斋老伯和五叔祖的帮助就留在英国四年八个月之久。
先到满秋斯特一个私立中学读了半年。又转到伦敦在天主教办的克乃芬姆学院读了一年,才考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Fine Art Depatrment of University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
)。我是入该学院第一个中国学生,三年以后我也是第一个得到该学院美术部毕业文凭的中国学生。当时傅斯年先生就在大学院的文学院读哲学。陈通伯先生已经大学毕业,下一年就回国了。而已留英十四年的广东人潘济时先生还不想回国。
(六)、最后终于同意参加国民党
我在伦敦时期除读书外,和一些同学联络一些知识较高的伦敦华侨组织了一个工商学共进会,除了联络情感之外,最大的目的是要无形中帮助他们革除聚赌、械斗等恶习,鼓励他们改进他们的生活、灌输他们更多的爱国观念。
当时最热心会务的有潘济时、裘祝三、陈剑修、莫耀(当地华侨)、龚某和我等人。在三年期间我们几乎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的时间都在为此工作。三年以后居然有些成绩,我们都非常高兴。慢慢的我们将此会的工作,移转到新到伦敦的同学和更多的侨领手里。
大概民国十一年我和刘纪文先生在伦敦认识了。他看我带到伦敦的一本《孙文学说》,又仔细看了我读此书的笔记,知道我很服膺国父孙先生的主张。就对我说:“你这样崇拜孙先生,你应请加入他所领导的革命党。
”我说:“我是学美术学文学的。加入革命党不会有什么贡献。”他又说:“革命党里无论什么人都有用,尤其是真心诚意赞成孙先生革命主张的人。”我说:“我本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世家,从小自然免不了有读书求官做的想法。
可是当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听说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那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人还免不了受武人官僚政客的气。所以我到英国以后不但是不学准备做官的学科,连哲学、教育等科都不愿学,就是怕卷入政治圈里去,受那些官僚政客和武人的气,因而选学了与人无争的美术和文学。
我如果加入革命党,将来一定会卷入政治漩涡,免不了受那些混蛋家伙的气。这是和我志愿相违背的,所以我不愿入党。”纪文又说:“你这种逃避现实的想法是不应该有的。
你既知道那些官僚、武人、政客的混蛋,正应该加入革命党,大家共同努力把他们打倒,来改造中国。”我听了他的话,虽也认为有道理,但是仍然没有入党的决心。以后我和纪文的友谊一天一天的增进,他不时总刺我一句说:“还没有决心参加革命党,打倒祸国殃民的官僚武人吗?”我总是笑笑了事。
后来邵元冲先生来到伦敦,又和纪文来谈过许多次,一定要介绍我入党。邵先生却比纪文会说得多了。一来就长篇大论说上二小时,并且他们要直接写信给国父介绍我入党。我真感觉有些烦了,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对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为他们的热忱和诚挚的友谊所感而最后同意入党了。
接着党的中央要恢复伦敦支部。经过在伦敦数十个老同志和裘祝三与我的努力,伦敦支部在十二年恢复了。那时国内已将中华革命党改为国民党。但是伦敦的同志们还没有得到新的组织规章,所以在支部恢复时纪文先生主张先照旧的规章恢复起来再说。当时支部内部组织,分为执行、评议两部。选举结果裘祝三同志当选了执行长,我自己当选了评议长。这是我参加中国国民党工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