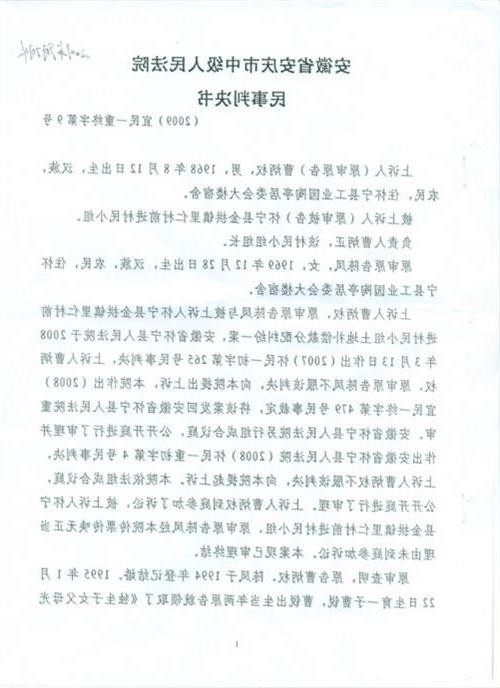安子文的子女 听凌子风、石联星的女儿讲述过去的故事
坐在已故著名导演凌子风惟一的女儿凌丽家里,墙上挂着的那幅凌老送给女儿的大写意花鸟画格外引人注目。画面上荷菊相映成趣,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和菊花不畏严寒的意境,饱含和传递着慈父对于女儿的希望。 坐在我面前的凌丽,1米80的个子,声音悦耳,这位当年北京女排的主攻手、今天的声乐教师已经56岁了,但风采依然。
凌丽的父亲凌子风1938年从南京戏剧专校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由他执导的影片《中华女儿》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捧回了第一个国际大奖。
母亲石联星1932年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都瑞金投奔了革命,解放初期由于主演了电影《赵一曼》而成为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女明星。由于出身于革命之家和红色电影之家,凌丽在长达5个小时的讲述里,充满了对父母的真情,也充满了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眷恋。
记得我上学时,学校请妈妈来给同学们作报告,整个学校都轰动了。“影片《赵一曼》的女主角、著名影星石联星要到我们中间了!”同学们兴奋得奔走相告。
当我见到妈妈时,从她的目光里,我只读出了四个字:“不许声张”。尽管整个学校都沸腾了,我却一直没有告诉同学们,石联星就是我的妈妈。爸爸教导我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我们的路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你们自己的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
”父母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这就是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父母。 这就是我热爱电影艺术而更热爱祖国的父母。 下面我讲几个父母亲的小故事。 有关父亲的故事 父亲是1938年从南京国立剧专投奔延安的。
他和我的爷爷一样,都具有极强的叛逆性格。我们家自古是满族正黄旗人,我的曾祖父还是朝廷命官,从租宅的上马石、下马石就能看出来,他当时官职不小。到了我爷爷这一辈,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满族人了,把祖籍也改成了四川合江,民族自然也改成了汉族。
父亲自小就喜欢航模,后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报了航校,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爷爷知道后关了父亲的禁闭,后来因为一件小事,父子俩吵了一架。
父亲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和东北来的穷学生张汀一起,租房子住下,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当时他正就读于北京国立艺校,生活的担子一下子压在了两个穷学生身上。出生于富裕家庭的父亲,利用课余时间蹬三轮拉客,捏了泥人到大街上卖,就这样和张汀一起艰难度日。
最后还是祖父向儿子服了软,请他回家。他为了说明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和同学借了钱,就请祖父在外面吃了顿饭。 这就是我父亲的叛逆性格。
就连从南京剧专到延安这么大的事,他也没和祖父商量。 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父亲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本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原则,创作了很多在陕甘宁、晋察冀地区屡屡受到好评的作品。
他首创了两种新的战地戏剧形式:田庄剧和幕表剧。别说今天的年轻人了,就连一般人都不知道战争年代的当年还有这两个剧种。田庄剧就是不用人工布景,用田庄里的自然景观作布景演出的戏,而幕表剧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
一般的戏剧是根据剧本演出的,而幕表剧恰恰相反,它是先有事件,演员们马上把这个事件演出来,最后再整理成剧本。经过一次次演出,一次次修改台词,一次次整理剧本,使剧本日益完善。
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三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父亲异想天开地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活报剧,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众多、气势规模最宏大的万人活戏剧了。这是由父亲直接策划和指挥的。父亲化装成聂司令员,跨上他的战马,在山野间纵横驰骋。
漫山遍野的八路军战士,高喊着“跟着聂司令员前进”的口号,挥舞着红旗前进! 除了编戏和演戏之外,父亲还担任过战地摄影记者,拍下了不少毛主席的珍贵历史照片。有一张大家比较熟悉的毛主席站在窑洞外看地图的照片,就出自于我父亲之手。
他为了拍毛主席,就住在毛主席的窑洞旁边,原来是偷拍,后来很快就和毛主席一家子混熟了。我父亲回忆说,毛主席这人特随和,对于晋察冀那边的情况毛主席问得特细,我感觉到他是通过聊天儿了解基层情况。
我拍主席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塑一尊像,因为我在北京艺专学过雕塑。结果像没塑成,倒是刻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枚毛主席像章,经陈老总父子之手,这枚像章现在仍珍藏在革命博物馆中。
有关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出生于1941年,是湖北黄梅人。1932年母亲正在读高中时,她最信赖的一位姓黄的老师被国民党杀害了,黄老师的死,让母亲决定走出书斋投奔革命。 她走出了家乡湖北黄梅,第一站到了上海,她在上海也见到了鲁迅,后来由于“红色恐怖”笼罩申城,她与先生的联系便中断了。
她带着两箱红旗,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苏维埃红色根据地瑞金。一路之上,她携带的红旗一旦被发现,她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在瑞金,她先后在高尔基学校、红军学校任教。在当老师的同时,她积极投入苏区的文艺活动。与李伯利、刘月华一起被称为红军的“三大赤色明星”。每个星期,他们都要为群众演出。当时在瑞金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都来看过他们的演出。
母亲在建国以前的革命活动,都是她的老战友、老同事告诉我们的。1934年,母亲与红军师长钟伟剑结婚。他们的婚礼,是同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妈妈同时举行的,就连他们新婚的洞房都是里外间,朱总司令和康妈妈在里间,母亲和钟伯伯在外间。
长征开始后,当时任党中央领导者之一的瞿秋白找到我的母亲,把钟伯伯留下的笔记本和一些苏区票(中央苏区流通的货币)交给了她,告诉她钟伟剑已经随大部队长征了,由于时间太紧,也来不及打招呼,只叮嘱我把这些东西转给你。
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在一次斗争中,钟伟剑牺牲了。 钟伟剑牺牲后,母亲继续在苏区开展工作。除了和同志一起进军作战,主要仍从事革命文艺活动。
她参与了八一剧社、工农剧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创作了《共产儿童团歌》等一批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作品。在一次战斗中,红军被打散了。母亲和当时任苏区艺术局局长的赵品三伯伯、韩进叔叔一起在战斗中被捕。
在狱中,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也没有撬开他们的嘴,后来他们分别逃了出来。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此周总理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写了信,信中认真负责地介绍了我母亲的一些情况,也点出了几位证明人的名字,连他自己也愿意为我母亲作证人。
他建议安子文部长认真考虑我母亲重新入党的问题,他同时也给我母亲回了信。当我母亲重新宣誓入党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内心里感激周总理对她的关怀、理解和信任。
在她病重的日子里,说话已经很困难了,面对前来看望她的晚辈,她吃力地说:“我已经很知足了,在我的档案里,有周总理为我解决的重新入党问题,写给安子文部长和我的两封信。在我的履历表上证明人那一栏里,多次出现了周恩来、康克清的名字。
我真的很知足了。” 无论是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母亲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教员、演员、导演、编创人员,还是一位待人宽厚、为人热情、乐于助人的长者和朋友。
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要拍影片《赵一曼》,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认真地说:“赵一曼这个角色就找石联星演吧!我相信她一定能演好,因为她有着和赵一曼相同的经历。
”总理的话一点也没有说错,母亲1932年从家乡到苏区投奔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整有17年的战斗经历。她不但是文化教员、演员,更是一名战士,和男同志一样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斗。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阿姨听到由我母亲饰演赵一曼时,深有感触地说:“我听说东影拍《赵一曼》,主角由石联星演,当时我们都认为就应该由她演,因为只有她经历了那个时代。
” 母亲果然不负众望,她把赵一曼这个女英雄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
在第五届国际电影节上,我母亲获得“最佳表演奖”,与此同时,由我父亲凌子风执导的影片《中华儿女》也在国际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父母双双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在我和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在言谈话语中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些事。
还是在两位老人故去后,我才知道他们这一段光辉历史的。 十年浩劫,江青一伙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把新中国剧社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很多剧社的老同志及其家属因此受到了迫害。当时的母亲尽管自己也受到冲击,但仍然联系了几个当年在剧社工作过的老同志,向有关部门和组织反映情况、写申诉材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清剧社是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组织。
中央组织部后来下发了新中国剧社平反的通知。
这件事是在母亲去世后,我在严恭伯伯悼念母亲的文章中知道的。 关于对母亲从事电影事业的评价问题,她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同事、北京人艺四大名导之一的梅阡先生,对我母亲作了这样的评价:“石大姐是影剧界的元老,革命资历最深,在影剧界里这么老资历的现在没有,石大姐是惟一。” 这就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