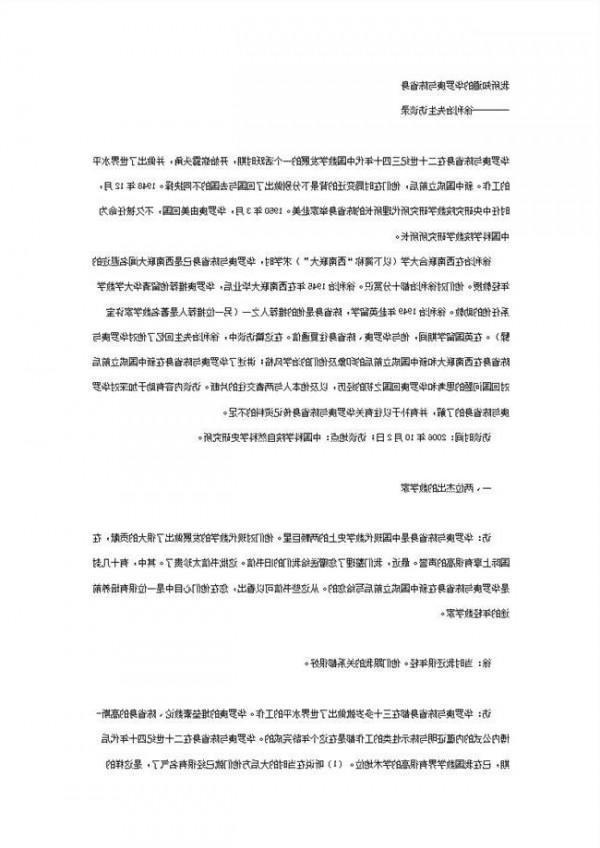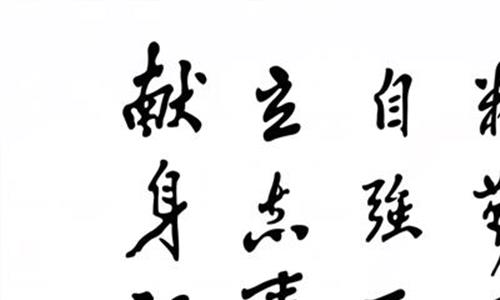陈省身与华罗庚谁厉害 18我所知道的华罗庚与陈省身
我所知道的华罗庚与陈省身--------徐利治先生访谈录 华罗庚与陈省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数学发展的一个活跃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并做出了世界水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在时局变迁的背景下分别做出了回国与去国的不同抉择。
1948年12月,时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的陈省身举家赴美。1950年3月,华罗庚由美回国,不久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徐利治在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求学时,华罗庚与陈省身已是西南联大闻名遐迩的年轻教授。
他们对徐利治都十分赏识。徐利治1945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华罗庚推荐他留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他的助教。徐利治1949年赴英留学,陈省身是他的推荐人之一(另一位推荐人是著名数学家许宝騄)。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与华罗庚、陈省身往复通信。在这篇访谈中,徐利治先生回忆了他对华罗庚与陈省身在西南联大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印象及他们的治学风格;讲述了华罗庚与陈省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回国问题的思考和华罗庚回国之初的经历,以及他本人与两者交往的片断。
访谈内容有助于加深对华罗庚与陈省身的了解,并有补于以往有关华罗庚与陈省身传记资料的不足。 访谈时间:2006年10月2日;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一、两位杰出的数学家 访:华罗庚与陈省身是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两颗巨星。他们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最近,我们整理了您赠送给我们的旧书信。
这批书信太珍贵了。其中,有十几封是华罗庚与陈省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写给您的。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您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数学家。 徐:当时我还很年轻。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
访:华罗庚与陈省身都在三十多岁就做出了世界水平的工作。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陈省身的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与陈示性类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年龄完成的。华罗庚与陈省身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已在我国数学界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1〕听说在当时的大后方他们就已经很有名气了,是这样的吗? 徐:西南联大有“数学三杰”,就是指华罗庚、陈省身和许宝騄。陈省身先生年纪最轻。华罗庚与许宝騄同年,比陈先生大一岁。他们是西南联大数学系的三位杰出人才。虽然他们当时都只有三十多岁,但都已成为名教授。 访:当时就称他们为“数学三杰”吗? 徐:是的。这三个人在西南联大数学系的确很突出。现在人们对华罗庚与陈省身两位
宣传得比较多。其实,许宝騄先生的数理统计工作也是国际一流的。他很早就得到英国统计界皮尔逊(K.Person,1857—1936)学派的称赞。 访:您在西南联大是华罗庚与陈省身的学生,还与华罗庚有过不少交往。
他们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徐: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常常乐于谈到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收获。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伏在吃饭用的桌子上做研究。那时,我是随机去的。这说明他不是在摆样子给我看。
他喜欢在饭桌上做研究,因为他的书房很小,桌子也不大。 不过,华先生讲话时经常会表露出一点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在西南联大的这种表现,得不到老先生们的好感。他当时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没有跟他来往的,所以华先生是相对孤立的。
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的时候,起初是选择苏步青担任筹备处主任。当时会议的记录现在还在。会议主要有苏步青、段学复、张宗燧、闵嗣鹤、周培源、钱伟长以及其他几位先生参加。
华罗庚因为出国等原因,参加得比较少。关肇直先生和田方增先生做记录。田先生记得最多。从记录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华先生的业务都很佩服,但对他的为人看法不一样。对于华先生是否适合担任数学所所长也是有异议的。
段学复先生也曾这样评价华罗庚先生:华先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我很佩服他的学问,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您说华先生在西南联大没有真正的朋友,印证了这一点。您能不能谈谈对陈省身先生的印象? 徐:陈先生的用功程度可能赶不上华先生,但他也很努力,有一阵因用功过度得过胃病。
他由法国回中国时带回嘉当(Elie Joseph Cartan,1869—1951)的二三十篇论文。他在西南联大苦读这些论文。
在我的印象中,陈先生做学问爱抓大问题,不主张多写文章。这点与华先生明显不同。1949年我在英国留学时,陈先生写信问我“出国后不知对于学问看法有无新观感”,他在信中还特别对我提出期望:“盼注意大问题,少涉细节,亦不必多写论文。
你作风已有此趋向,不必多言也。”他的意思就是说,华先生写文章太多,我的作风有点像华先生,不要跟华先生学。 访: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结束后,中央研究院刊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
这个资料刊载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著作目录。从目录可以看出,五位数学院士中,苏步青发表论文最多,有九十五篇;华罗庚次之,发表六十八篇;陈省身再次,发表三十八篇;许宝騄发表二十四篇;姜立夫发表一篇
。这个统计数据是截止到1947年为止的。通过比较可知,华先生写的文章确实不少,要比陈先生多三十篇。您对陈先生的建议有何感想? 徐:陈先生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论文不必做太多,因为质量还是很重要的。有些大数学家一生只写了几篇重要文章。
华先生与陈先生的价值观不完全相同。华先生觉得做得越多越好。其实,这也是有道理的。我看过很多数学家的文集。其中,十之八九都是一般性的文章,只有几篇是特别重要的。很多大数学家也不是只做重要的文章,一般性的文章也做。
他们的文章中只有若干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国外一般的数学家的文章都是很多的。他们一辈子发表两百篇、三百篇文章不算一回事。咱们国家的数学家如果一生发表两三百篇文章那就多得不得了了。
访:我们看过关于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 1789—1857)的传记。 徐:柯西的文章多得不得了。 访:柯西好像完全被数学控制了。他听到一位学者在报告中讲述的主题后,就会情不自禁地马上去做。
因为他的数学能力强,他肯定能做过对方。当时有人就评论说,柯西是不是有点在抢人家的饭碗。其实,柯西并无此意,而是他对数学已经到了非常入迷的程度了。 徐:柯西的脑子很好。
他在《法国科学院院报》发表的文章不但多得不得了,而且快得不得了。他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投给《法国科学院院报》的前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后一篇文章又去了。关于他的英文传记,讲他有快速发表的习惯。华先生虽然文章多,但还比不上柯西。
他发表文章的速度也比不上柯西。柯西发表文章的速度要比华先生快上几倍。当然,后人评价柯西时说,柯西不必写这么多。他一生发表六七百篇文章。欧拉(Léonard Euler, 1707—1783)的文章也多得很呢!
但这些大数学家的文章,几百篇中只有三五篇、六七篇传世的。 访:现在有些国外机构让科学家写自己的工作时,要求他们列出三件最满意的。 徐:但我也觉得,文章不做到一定的量,一定的程度,突然做出一个重要的来也不容易。
所以完全不讲量,只讲质,一下子突然就做一篇很重要文章也是不大可能的。 访:有人说华罗庚是少年得志。就是说,1941年数学界就他一个人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查委员会评定的首届国家学术奖励金一等奖。
徐:许宝騄先生得了二等奖,但他的工作也是一流的。华先生得一等奖的主要评审人是何鲁。何鲁是留法的,中央大学的名教授,数学界的老前辈。他在国内相当有名气。他写了很多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看来,这些书
都是比较初等的。其中,有《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等。我年轻的时候也买回两本。《虚数详论》是一本薄薄的、红布面的书。但何鲁不是研究解析数论的专家。访:那为什么请何鲁审稿呢?徐:他有名气,又是中央大学的老教授。
学界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何鲁写的评语非常好。由于他不是数论专家,他是否吃透书中的内容也很难说。不过,他的话是很起作用的。当然,华先生也发表过很多论文。他的“堆垒素数论”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工作,在国际上也有地位。
当时国内没有别人在这个方面可以比上他。 访:华罗庚得奖后,其他数学家有什么反响?徐:议论是有的。华先生得奖后,国民党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昆明的各种小报也刊登得奖的消息。陈省身先生当时说,连街上修皮鞋的人和小店铺的店员都知道华罗庚的名字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报纸把华罗庚宣传得过分。当年国民党时代,社会风气是把一点东西吹得很大。陈先生的话有些道理。许宝騄先生也讲,他对当时把数论捧得这么高不以为然。
他说,数学中重要的东西多得很,数论也不过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这可能是针对华先生的“堆垒素数论”得了一等奖说的。访: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离现在已有很长时间了。我们这些隔代的局外人,也能想象和理解底下会有种种议论。
徐:当年获得一等奖的还有冯友兰。国民党把华先生与冯先生到处宣传。而且当时不少报纸上都在神化般地宣传华先生。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只要有引起市民好奇的消息就喜欢登。访:我们看到一个材料讲,设在西南联大的新中国数学会,在1942年6月3日晚举行茶会,庆祝华罗庚与许宝騄得奖。
不知西南联大数学系对华先生得奖有没有搞庆祝活动?徐:我当时在叙永分校,还没有到昆明。我是在四川看报纸知道这个消息的。
有些人也在传华先生得奖的事。庆祝活动可能是有的。访:华先生得奖后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什么反响?徐:华先生得奖后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是很出名的。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对他很崇敬。争着选修他的课。
当时西南联大数学系的学生很少,上华先生数论课的学生就有十五六个人。这与他得奖有关系。选陈省身先生的课的学生,超不过十人,一般只有五六人。访:华罗庚与陈省身都受到过清华数学系的培养。清华的熏陶对他们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都有哪些影响?徐:清华数学系的培养对华先生后来取得重要数学成就应该很起作用。陈先生虽然在清华读研究生,但恐怕是德国、法国的教育对他更起作用。布拉施克(Wilhelm Joh
ann Eugen Blaschke, 1885—1962 )、嘉当对他的培养很关键。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刘晋年先生教过我复变函数。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是陈省身的师兄弟。他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来的。
他说,他当年出国留学的机会没有陈省身先生好。他说陈省身留学占了便宜。一个是,陈省身遇到了布拉施克。布拉施克是几何方面的权威。后来布拉施克推荐陈省身跟嘉当学习。这个机会更好。当时嘉当的那套活动标架法和外微分形式等一套方法越来越成熟。
嘉当是这两方面的创始人。陈先生到法国学完这些东西以后,回过头来一看,在国内学的射影微分几何就显得落伍了。他说苏步青先生的许多工作都是比较平凡的。他好像用了“肤浅”两个字。
访:数学在发展,评价也会变化。徐:随着数学的发展,有了新进的东西,再看过去的老东西,当然会显得简单了、平淡化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数学发展了嘛,是不是?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华先生对陈建功先生的工作也是有看法的。
当时,浙江大学的陈建功与苏步青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学生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华先生与陈省身先生都认为,陈建功先生等是在“按照归纳法搞研究”。什么叫按照归纳法做研究呢?比如搞傅立叶级数求和法,先搞C1。
C1搞完了,再搞C2。搞完了C2,再搞C3、C4,等等。按照归纳法,这样下去无穷多的文章都可以写出来。陈省身先生还说,浙江大学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好像是一架机器似的,放进去,一摇出一篇文章(加动作)。
意思是说,浙江大学出东西太快,而且都是老一套。华先生也跟我说过这个意思:浙江大学的分析,专搞傅立叶级数求和法,已经按照机械化的形式出文章了。文章出得很多,倒都能发表。只要人家没有做过的都能发表,但价值、意义是另外一回事了。
访:在西南联大数学系,除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这“数学三杰”十分突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突出的数学人才?徐:应该提到的是两位从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来的教授,一个是程毓淮,另一个是蒋硕民。
程毓淮与蒋硕民先生都是北大的教授。他们都是通过江泽涵先生请来的。蒋先生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程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十五年前回国时,我在长春还接待过他。听说,他现在也去世了。
这两个人学问很好,但不大写文章。因为他们不怎么写文章,也就没有什么名气,报纸也不会宣传。他们在哥廷根大学听过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库朗(Richard Courant,1888—1972)的课。哥廷根大学当时是世界数学的一个中心。程先生去美国后也做了一些工作,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