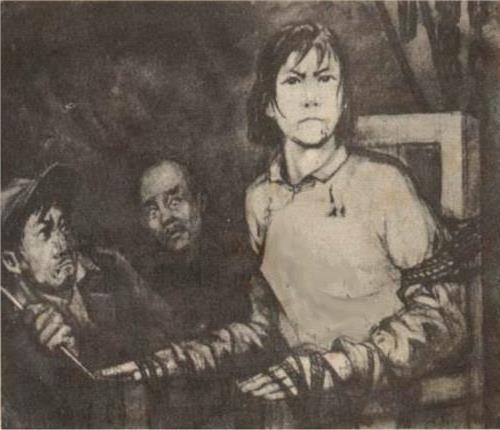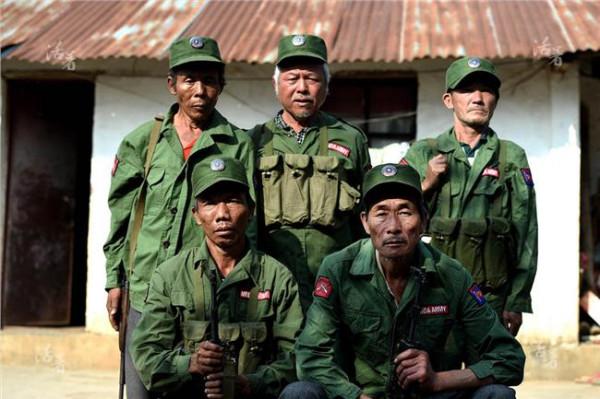江姐到底受的什么酷刑
关于江姐是否受过竹签子的酷刑的问题,我过去一直都认为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正反双方其实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江竹筠在被捕之后的确受过酷刑,而且在酷刑之下坚不吐实。这样的事实,足以证明江竹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关于江姐是否受过竹签子刑罚的问题时时被人提起,在有些人看来,否定竹签子,就是否定了江姐的坚贞不屈,就是否定了几代人心中的偶像。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既然竹签子是假的,那么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甚至连罗广斌的《狱中报告》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我现在的看法有了一些转变,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宣传英雄人物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才是尊重烈士。把烈士偶像化和神话化,跟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烈士”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意义之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文献和所谓“口述历史”。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尽信“史”也不如无史。互联网上的争论,最终往往会沦落为口水战,因为一些喜欢辩论的人,或者是把文学作品以及准文学作品当成历史材料一再地加以引用,或者是对个别亲历者的回忆或者所谓官方人士权威人士的话深信不疑,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主张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人一遇到持异见者就进行人身攻击。这就迫使我非要专门写个东西来对1950年以来关于江姐受刑问题的种种材料略加梳理剖析。我的目的不是要支持谁否定谁,而是想把目前能够找到的证据罗列出来,与对“红岩”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们进行讨论。
二、何蜀的文章
在我的印象中,专门写文章对江姐的受刑问题进行分析的是第一人是曾在《红岩春秋》做编辑工作的何蜀,他在《江姐受过的是什么酷刑》一文中对“竹签子”之说的来源进行了追溯,以下是他文中的内容: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1957年2月19日出版的《重庆团讯》当年第3期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江竹筠》(连载之一,编者按称选自即将完稿的《锢禁的世界》),其中描写江姐受刑的情况是:
‘绳子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子从她的指尖钉了进去……竹签插进指甲,手指抖动了一下……一根竹签钉进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了出来……’
“1959年1月10日出版的《红领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其中写道:
‘刽子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对江姐受刑也是这样描写的:
‘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冷水的声音。泼醒过来,就又钉……’
“以后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受的这种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样。歌剧《江姐》第六场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在下令对江姐用刑时狂叫着:‘把她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
可以说,何文已经对竹签子的起源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显然,在“红岩故事”的宣传史上,最早是没有“竹签子”之说的。“竹签子”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小说《禁锢的世界》(笔者按:长篇小说《红岩》最早取名“禁锢的世界”),也就是说,“竹签子”从一出世就带上了“文学”的胎记。如何蜀所说,“竹签子”的描写实在是太有刺激性了,因此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正是读者的反馈使得罗广斌等人在以后的宣传或者艺术创作中就一再地沿用了竹签子的说法。何蜀最终得出结论说,江竹筠所受的刑罚是夹竹筷子而不是钉竹签子。当然,何蜀也指出,夹竹筷子的事实对于江姐的英雄形象不会有所贬损,只是,历史不应虚构,无论是以什么主义的名义。
何文在互联网上发布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表示惊讶——原来先烈的受刑问题也会掺杂水分,也有读者表示质疑——何文所列举的文献还不够全面,对不能支持自己的证据采取了忽略的态度。那么,到底是哪些文献不支持何说呢?是否还有何蜀没有提到的不支持竹签子的材料存世呢?
三、不支持“竹签子”的证据
首先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一下那些不能支持“竹签子”的证据。这里的证据是指来自渣滓洞斗争亲历者或者专业研究人员的说法,不包括任何艺术作品或者非亲历者的描述。此外,“不支持”不表示“反对”。
关于江竹筠在狱中的表现,何文所列举的成书于1950年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还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文献当属罗广斌写于1949年12月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河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谈到下川东干部时说:“江竹筠杨虞裳为首的万县干部大多数是非常优秀而且有资格作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经验的。江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里提到江的受刑,未提受的是何种刑罚。
在何蜀提到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中,罗广斌等人至少有三次提到了江竹筠所受的刑罚,均未提及“钉竹签子”。例如,该书的封面说明是“江竹筠女同志坐过老虎凳,灌过水葫芦,还被吊晕过好几次,特务从没有在她口中得到过一个字……”。此处的“吊晕过好几次”与罗广斌在《报告》中所提到的“晕死三次”是否有重合,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中美合作所”内的酷刑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另外还配了许多插图表现酷刑。关于夹竹筷子的刑罚,插图的主人公是唐虚谷烈士,图片说明为“唐虚谷烈士说:‘筷子究竟是竹子做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关于这句话,熟悉长篇小说《红岩》的读者都知道,书中的女主人公江雪琴在被钉竹签子的时候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关于竹签子的刑罚,该书也配了插图,主人公是许建业烈士,说明是:“特务用竹签子钉许建业的指头时,他说:‘无论哪一样,来吧!’”
罗广斌等人稍后发表的回忆录《圣洁的血花》中未提江竹筠被钉竹签子之事,关于这一点何文已有引证,兹不赘言。
1972年,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特务罪行展览馆曾对渣滓洞和白公馆幸存难友进行过笔头调查,调查内容之一是“美蒋特务如何残酷迫害革命者?施用的酷刑有多少种?如何施刑?刑具如何制造?”江竹筠的女难友牛小吾和李玉钿对这次调查均有书面答复。牛小吾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了老虎凳和竹筷子,并且对夹竹筷子的酷刑有具体描写,说这种刑罚“看起来不怎么样,但也要伤筋骨的”。关于受刑最多的犯人,牛小吾提到的是许建业。而关于江竹筠的受刑情况,她只字未提。李玉钿的答复是,“渣滓洞内有人受过二十几种刑。如……竹筷子夹十指……”,其中未提及竹签子。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李玉钿说:“听说受刑最多的是杨虞裳,受了二十几种刑未向敌人投降。许建业受刑时用头去撞敌人的刺刀也不投降。江竹筠受过敌人的吊打和日夜不解去脚镣。”
牛小吾和李玉钿均没有提到江竹筠在狱中被钉竹签子。这次调查的时间是1972年,距离罗广斌等人第一次提出江竹筠被钉竹签子已经过去了15年,距离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发表也已经过去了13年。在这十余年的时间内,“竹签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小说《红岩》发表之后更是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但是,与江竹筠一起坐过牢的两位女士在回忆往事时却对江竹筠与竹签子的关系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曾经亲自参加刑讯江竹筠的法官张界在文革中写有若干交待,在谈到江竹筠受审情况时,他提到了夹竹筷子时江的表现,但是一直没有提到钉竹签之事。
1991年,江竹筠在渣滓洞女牢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曾紫霞(小说《红岩》孙明霞的原型人物)的遗作《战斗在女牢》公开发表。在这篇回忆中,曾紫霞特别提到了女牢难友对江竹筠受刑之后的照顾,但她跟牛小吾和李玉钿一样,都没有提到竹签子的刑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请,让我们把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来进行一番推理。
如果江竹筠真的被钉过竹签子,按照常理,曾紫霞在这篇文章中即便不对竹签子大书特书,也不应该把笔墨吝惜到只字不提的程度。当然,她也没有刻意否认竹签子之事,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有人在用盐水清洗她的伤口”。这句话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无论是竹签子还是竹筷子,都有可能留下伤口。也许有人会说,曾紫霞对竹签子之说没有否认,即是默认。我认为,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自1949年以来,官方宣传牢狱中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以所受酷刑的多寡和程度作为某种标尺的,这种思维方式早已深入到绝对大多数受众的骨髓中,作为江姐亲密战友和作为政治理论课资深教师的曾紫霞,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如果竹签子之说属实,曾紫霞是不大可能用如此寡淡的语气地一笔带过。
那么,如果江竹筠真的没有受过竹签子的刑罚,曾紫霞为什么不借写回忆录的机会对事实进行澄清呢?如上所述,在一种强势思维范式的引导下,曾紫霞若在回忆中对竹签子之事进行刻意的说明,那就无异于给烈士脸上抹黑。她不会“不懂事”到如此地步。此外,曾紫霞与红岩故事最著名的宣讲者罗广斌是私交很好的朋友,她也断断不会在朋友故去之后作惊人之语地把他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宣布为“仅仅是故事而已”。因此,她的语焉不详,其实已经是一种态度。
以上是见诸文字的渣滓洞斗争的亲历者的回忆。笔者在2006年曾经在成都牛小吾老人的家中采访过牛小吾,当问及江竹筠在狱中受刑的情况时,牛老的脸上一片茫然的神色,我们启发她说,江姐受刑之后,女牢的难友们集体照顾她,渣滓洞的难友们还组织过慰问活动,您还记得吗?牛老明确表示,她不记得江姐在渣滓洞受过刑。我们又继续问,难道连夹手指的刑罚也没有受过吗?牛老肯定地表示她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至于竹筷子夹手指,她本人因为拒绝交出关系倒是受过此种刑罚。这让我想起牛老在1972年的调查材料中曾经详细叙述过此种刑罚给犯人造成的痛苦,若非亲身经历,恐怕不会专门对此刑罚加以详述。2006年距离牛老出狱已有57年的时间,虽然牛老身体康健,精神矍铄,但记忆发生偏差也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如果把牛老1972年的回忆和2006年的回忆对照起来分析的话,恐怕就不能简单地认为牛老2006年的回忆是完全不可信的了。
关于口述历史,还有一位男牢的幸存者也曾经跟网友若水讲述过渣滓洞的生活,这就是《把牢底坐穿》的曲作者周特生先生。据周老介绍,他对江姐在渣滓洞受刑的事情有所耳闻,但没有听说过是受竹签子的刑罚。周老的话当然不能作为论证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但至少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旁证。
四、支持“竹签子”的证据
如何蜀文中所述,最早出现江姐被钉竹签子说法的历史文献是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烈火中永生》于1958年2月发表于《红旗飘飘》第6辑,1959年2月出版单行本。早于《在烈火中永生》的《禁锢的世界》节选《江竹筠》(1957年)只能算是文学作品,因此不能作为讨论竹签子问题的证据。但是,这里仍然要提及《禁锢的世界·江竹筠》,因为早在1956年罗广斌等人就开始了《禁锢的世界》的写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说竹签子之说是起源于小说还是起源于回忆录。无论如何,小说与回忆录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以及在竹签子问题上的相同处理都是不容忽视的。
1982年,《江竹筠传》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第一作者卢光特是江竹筠生前的战友,也是当时“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罪行展览馆的领导者之一。在这部传记中,作者明确指出,给江竹筠施以钉竹签子毒刑的是重庆绥靖公署二处侦讯组长陆坚如,这次施刑的地点是在渣滓洞看守所。
在写作《江竹筠传》的时候,卢光特担任展览馆副馆长,因此他应当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与烈士相关的档案材料,具体是什么材料披露过给江竹筠施刑的是陆坚如,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张界在交待材料中提到陆坚如参与过审讯江姐,但如上文所述,他未提到竹签子之事。当然,作为主审法官,张界在交待中有意隐瞒钉竹签的酷刑也不是没有可能。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事人陆坚如在1949年底被解放军抓获,1951年初被镇压,他在被关押的1年左右的时间内是否交代过关于钉竹签子的事情,今天看不到公开出版的资料。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江竹筠传》对于江姐在渣滓洞受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竹筷子的刑罚上,先后用了两个自然段展现江姐被酷刑折磨的痛苦,这些描写明显来自张界所写的交待材料。而对于被罗广斌们浓墨重彩地描写过的竹签子,《江传》只用一句“陆坚如更采用了在她手指尖上钉竹签子的毒刑”就一笔带过了。竹筷子与竹签子的轻重对比如此悬殊,而竹签子的当事人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就被镇压,这其中是否暗藏玄机,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
一个非常著名的支持竹签子的证据是沈醉所写的关于江竹筠的回忆。沈醉是老牌特务,在江竹筠被捕之时,他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与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的徐远举多有工作往来。据他自己在《敬怀江姐》一文中说,他曾经亲眼目睹徐远举在二处审讯江姐,就在这一次,他听到二处负责对犯人用刑的“社会侦察组长”与徐远举的对话,徐远举下令“用竹签刺她一下”。但是,沈又说自己并未亲眼看到用刑,因为江被送进刑讯室之后他便走了。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沈醉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竹签子刑罚的目击者,顶多是“耳闻者”。而沈醉的回忆在细节上的可信度有多大,是需要打问号的,光是他关于徐远举和周养浩之间矛盾的回忆,就足以另外写篇文章来讨论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及与史实不符的叙述了。
关于“社会侦察组长”给江竹筠钉竹签子的说法,沈醉的回忆与《江竹筠传》一致,但是,沈文发表于《江传》出版之后,因此这个一致性貌似还不足以证明二人的说法没有“传承”关系。一个可以否定沈沿用《江传》的旁证是,《江传》里提到过徐远举审讯江姐时沈醉在场。但是,沈的回忆在比较重要的环节上又与《江传》冲突,这就是,沈所说的江竹筠被钉竹签子的地点与《江传》所述不符。《江传》说是在渣滓洞,根据《江传》,沈“旁听”审江的那次,江受到的刑罚中并未提及竹签子,因此可以理解为那次受刑没有沈所说的竹签子;如果有的话,下文就不会说“陆坚如更采用了在她手指尖上钉竹签子的毒刑”,而是应该说“……又一次采用了……竹签子的毒刑”。
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迄今为止无法找到能够直接支持竹签子的证据,而竹签子的最早诞生又与文学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那些支持竹签子的旁证是否可以形成证据链呢?目前,有可能(而不是一定)能够形成链条关系的只有《江传》和沈的回忆。如前文所述,这两者只有在不存在彼此传承竹签子之说的关系的前提下,才会有证据的链条关系。尽管《敬怀江姐》的发表时间晚于《江传》,但是,《江传》中特意提到沈的在场,应该不是凭空杜撰;而如果沈之在场的确属实,那么,沈之回忆可信度就增添了几分。当然,这也依然不能与《江传》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至多只能证明沈的确目睹过审江。
可惜的是,在我所见到的文献中,也只有沈本人和《江传》声称沈目睹过这一的历史重要场景。据徐远举解放之后写的材料,他本人并未亲自审讯过江竹筠,如果他之所述属实,那么沈醉也就根本不可能在审讯江竹筠的时候在场。当然,徐远举不承认亲自审过江,也许是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见证人是亲自参与审讯江竹筠的特务张界,他在交代材料中提到过审江时在场的比较重要的人员,其中有徐远举(似乎可以证明徐声称自己未曾审江的说法不可靠,但这个证据是一个孤证)、陆坚如,但是他未提到过沈醉。现在在问题是,《江竹筠传》是根据什么材料断定沈曾经目睹过徐审江的。据沈美娟《我的父亲沈醉》称,在小说《红岩》出版之后,罗广斌和杨益言曾经到北京找沈醉了解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情况,沈醉向他们二位讲述了自己目睹徐远举审江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后来《江传》中出现的场景以及沈的自传大同小异,据沈美娟说,罗广斌听了沈醉的叙述后连称“这个情节好”,他甚至为《红岩》没有写到沈所叙述的情节感到遗憾。罗后来间接参与了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创作,电影在表现徐鹏飞刑讯江雪琴时就采用了沈叙述的部分细节。也就是说,罗、杨在文革前就听到了沈的说法。卢光特与罗、杨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关系,因此,卢在写作《江竹筠传》时参考他们留下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资料或者直接从杨益言那里获取一些口头材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江传》中关于沈目睹审江的情节有可能就来自沈本人。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了。
最后要强调指出两点。第一,即便沈醉真的旁听过徐远举审讯江竹筠,也仍然无法直接证明竹签子的存在,因为他说过自己并没有亲眼目睹到江竹筠被钉竹签子,因此,我们实际上仍然不能确认谁是这一著名事件的目击证人。第二,沈醉的竹签子之说是在著名的《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之后才问世的,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它的独立性和可靠性。
江姐受过的到底是什么酷刑
《文史精华》2004年第5期何蜀/著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
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电影演员于蓝在扮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时,就专门请当年江姐的战友刘德彬详细介绍了真实的江姐的各方面情况)。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虽然江姐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只是基层党组织(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与她同时代献身革命、同样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万,但她却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迹还同许多革命领袖人物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的人物辞条中。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还有不少人要求选江姐……这不能不归功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土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情节编造痕迹太重,被刘德彬提议删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签子“钉手指”酷刑的情节,仍然保留了下来,长期留传,影响深广。
我们看看历史上对江姐事迹的介绍中,对她受刑的介绍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他们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土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做代表向评审会议介绍情况,听候咨询。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可见,在早期的介绍中,江姐所受的酷刑并没有什么竹签子“钉手指”,而只有一个“夹手指”。这个“夹手指”,即刘德彬后来所说的“夹竹筷子”,是通俗的说法,其实它就是古已有之的一种酷刑,名叫“拶”。
拶,是旧时酷刑的一种,以绳穿5根小木棍(比吃饭用的筷子略粗)为刑具,名叫“拶子”或“拶”。行刑时,将受刑者手指分别套人木棍之间,用力紧收,叫“拶指”,简称“拶”。在明代凌濛初所著话本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中,就记载了南宋名妓严蕊遭诬陷后被绍兴太守严刑逼供:太守“就用严刑拷她,讨拶来拶指,严蕊十指纤细,掌骨嫩白……”京剧《窦娥冤》中,窦娥也受过此酷刑,她的唱词中就有“不招认实难受无情拶棒”。可知此刑早在元代就常用了,而且看来多半用于对女性逼供时。在早期介绍江姐事迹的文章中,如实写了她受到的是“夹手指”即“拶指”的酷刑。但是,不久之后,这个酷刑被改成了用竹签子“钉手指”。
1957年2月19日出版的《重庆团讯》当年第3期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江竹筠》(连载之一,编者按称选自即将完稿的《锢禁的世界》),其中描写江姐受刑的情况是:
绳子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子从她的指尖钉了进去……竹签插进指甲,手指抖动了一下……一根竹签钉进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了出来……
1959年1月10日出版的《红领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其中写道:
刽子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对江姐受刑也是这样描写的:
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冷水的声音。泼醒过来,就又钉……
以后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受的这种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样。歌剧《江姐》第六场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在下令对江姐用刑时狂叫着:“把她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
这样的细节,的确给人印象太强烈、太刺激了。因此许多人一提到江姐,就会想到竹签子“钉手指”。
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罗广斌他们怎么可以在宣传烈士事迹时不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苛责罗广斌等人。因为在当年,他们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历史学家,都只是年轻的共青团干部。那时他们的职责和心愿,只是为了教育青少年,为了千方百计启发青少年的“阶级觉悟”和“反美”情绪而进行政治性的宣传鼓动,他们不是作严肃的历史研究,更不懂什么“学术规范”,加上当时强调的是“政治第一”,文艺、教育等等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那样的大气候中,他们难逃历史的局限——请想一想,有的深通历史、深请学术规范的专家学者还有意剪裁、虚构历史来迎合政治需要,更何况他们这样的“激情燃烧”的共青团干部?因此,他们在宣传讲演中没有拘泥于历史细节的真实,想的只是为青少年讲“革命故事”,而且要尽可能讲得生动感人。罗广斌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就是有名的“故事大王”,讲起来更善于作艺术性的加工、渲染。这样,他们在讲演中就陆续加进了一些虚构的、夸张的内容,以后又写到了作品里。
其实,真实写出江姐当年受过的酷刑不是“钉竹签子”而是“拶指”,也并不会就贬低她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当年在“教育(或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下,为了“革命的需要”,对历史真相竟可以随意进行修改甚至虚构?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已经看到,后来有人把20年代安源工人歌颂领导他们罢工的李隆郅(李立三)的民歌改成了歌颂毛润之(毛泽东);把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负责人朱德改成了林彪;甚至把井冈山时期的珍贵文物红军布告上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陈毅的名字用香火烤掉,造成人为的“破损”,只留下党代表毛泽东一人的名字……把这些教训联系起来,不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吗?
历史,毕竟不应虚构——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听说今天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馆的讲解中,已经不再讲江姐被竹签子“钉手指”了。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恢复,也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