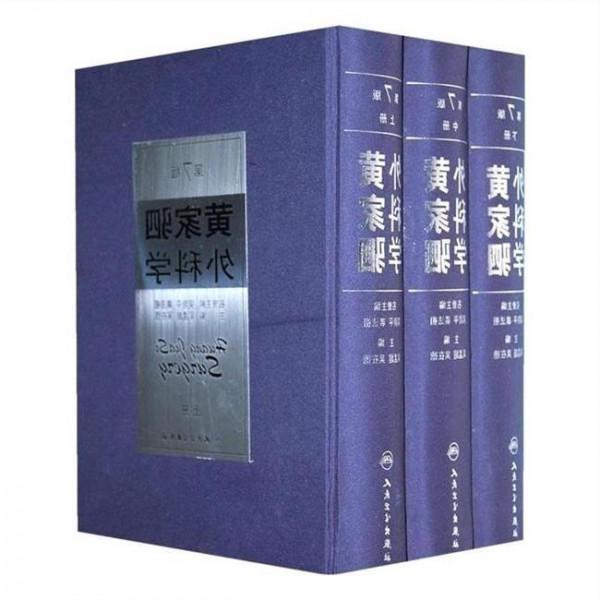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说 吴于廑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吴于廑先生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在此期间,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大师风采,常常在我的脑际浮现,我不止一次地在梦里和先生相见,谈工作,议时事,叙家常,其情其境和先生健在时一样,真真切切。在吴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谨以此文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和永不忘却的纪念。
一、吴于廑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不曾有世界史学科。这门学科的建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建国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历史学领域也不例外。我们一方面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授世界史,一方面翻译出版苏联的世界史着作。
同时在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设置世界史教研室和世界史研究机构。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学习和探索,世界史学科的初步基础已依稀可见。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世界史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世界史编写组的正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和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担任。由这两位当年的哈佛同窗挚友,如今的学术名流共主其事,可谓珠联璧合。
编写组在部分高校世界史讲义的基础上,同时主要借鉴苏联的世界史着作,于1962年编写成四卷本近两百万言的《世界通史》,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继而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和《世界历史名着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史教材体系。
这部既有正文又配以参考资料的世界史着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建树起来,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在这座丰碑的主编位置上镌刻着周一良和吴于廑的名字。
从此,学术界人士习惯地简称这部着作为周吴本《世界通史》。此书为高校世界通史课程提供了足资遵循的教本,被全国高校所普遍采用,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同时也成了社会上广大读者了解世界获取世界历史知识的权威性读物。其社会功用不可低估。
这部书出版4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是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这部书在书店里的销货情况依然不差。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此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断增加。我国一批又一批外交官将要赴驻在国走马上任。但是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新外交官,普遍缺乏世界历史知识。
他们出国前需要补上这一课。同时,由于我国外交局面的打开,社会各方面人士也亟欲了解世界。这一情况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切,要求出版部门提供世界史着作。在当时图书稀缺的情况下,能够提供的只有周吴本《世界通史》。于是在国务院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吴先生主持对《世界通史》进行第一次修订,并很快印制发行,以应社会之急需。那是1972年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恢复招生,对教材的需求剧增,同时社会上读书之风日益兴盛。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在教育部领导下由吴先生主持对周吴本《世界通史》进行第二次修订。新版本投向社会广受欢迎。
这部书从1962年初版到20世纪90年代初,屡屡加印,在30多年时间里,累计印数达40余万部,其印数之多,为其他同类着作难望其项背,其学术权威地位经久不衰。近二三十年,国内先后出版了几部世界通史性着作。
这些着作在学术上有变化有进步有提高,但如果拿来和周吴本《世界通史》仔细比照一下就会发现,其基本历史事实和知识框架,与之相同或类同者并不少见。这说明周吴本《世界通史》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性地位是不易动摇的。
1979年周吴本《世界通史》第二次修订工作,是在北大未名湖畔专家招待所进行的。当时因给周一良先生落实政策的工作尚未结束,所以周先生没有参加这次修订工作。由吴先生主持有各分册主编参加的修订工作完成后,周先生来招待所看望吴先生。
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所以他们二人见面时我也在场。周先生在寒暄几句之后,拿出一封致人民出版社领导的信函给我。信中说,四卷本《世界通史》在编写时,从撰稿到统稿到定稿,吴先生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此吴先生离开武大离开家人在北京工作很长时间,异常辛劳。
后来的两次修订工作都是吴先生一个人主持并亲自动手的。因此,这次修订再版时,建议把吴先生的名字移到主编的第一位置。
周先生说,当初编教材时中宣部规定,凡是北大教师参加编写的教材,编写组的正组长一律由北大教师担任,所以周一良的名字就排在《世界通史》主编的第一位,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所以要改过来。吴先生当即表示不同意周先生的建议。
因为信是写给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所以我不能不把信接过来。这次教材修订工作是教育部领导的,出版社领导阅过信后又转到教育部。经教育部党组研究,认为当下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周先生的主编位置不宜移动,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误会。因此,这次修订再版时,两位主编的位序一仍如旧。
二、吴于廑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向前发展的引领者 周吴本《世界通史》在吸取苏联史学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其错误史学观点也伴随而来,如欧洲中心论,俄罗斯沙文主义,以及世界史编纂体系过分拘守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期框架,把世界史视为各个国别史和各个地区史的简单相加等。
这些错误史学思想,当初并未觉察其不当。事隔多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当反思向苏联学习的得失时,世界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些错误史学观点在四卷本《世界通史》中之存在,并发出清除这些错误观点的呼声。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一次世界史学术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怎样清除苏联错误史学观点和编写一部新的世界通史的问题。这两个论题,前者是告别过去,后者是面向未来。告别什么,明确而具体,而未来新世界通史是什么样子,前景并不清晰。
正当此时,吴于廑先生在武汉发出令人茅塞顿开的声音。
1978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吴先生发表题为《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的学术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世界史学科受外来史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还鲜明地提出建立新的世界史观的主张。吴先生指出,苏联史学之所以有那些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史观之不当。
清除外来错误史学思想固然是必要的,但"破"并不是目的,目的应在于"立".我们不能仅仅停止在"破",因为如果仅止于此,不仅不能弄清其错误的根源,更不能找到我国世界史学科前进发展的方向,而这一点则是关乎我国世界史学科怎样走上科学化道路的问题。
吴先生说,迄今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把各个国别史和地区史汇编起来就是世界史。但这种简单的堆积并不能构成一个世界历史的整体。
世界史不是一个个局部历史相加的总和。为了建设一个科学的世界史学科,必须摆脱沿袭已久的世界史观的束缚,建树新的世界史观。这次报告5年之后,1983年,吴先生以在云南昆明所作的《世界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学术报告为起点,连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同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史卷》撰写概观性前言,为《大学世界历史地图集》(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写长序,还在呼和浩特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的报告,等等,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以10万余言把他阐述的世界史观与世界历史编纂体系,向学术界系统地展现出来。
世界史观对于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犹如人生观、世界观之于人生。吴先生提出的独特而新颖的世界史观,以全球的广阔视野,观察、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从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联成一体的整体过程,从而揭示其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这一世界史观,界定了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规定了它的内容、任务和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突出强调了全局观念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为世界史研究开拓了天高任鸟飞的无限空间。这一世界史观摒弃了以往各种世界史观在知识上的片面性和文化观念上的狭隘性,可视为世界历史新概念。
据此新概念研究世界历史,既可以克服过去世界史学中的种种流弊,又可以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史观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向科学化的新道路,象征着我国世界史研究已摆脱外来史学思想的影响,步入能够独立思考的不惑之年。
因此,这一世界史观一经面世,很快引起史学界的热切关注,并产生广泛的影响。那以后出版的一些世界史着作中,可以看到这一世界史观或明显或隐约的影子,在世界通史性着作中,此前沿用已久的编纂体系也有所改观。
社科院世界史所陈洪进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称誉吴先生的世界史观是"世界史观新理论在我国兴起".更多的人把这一世界史观称为宏观史学,高屋建瓴,博大恢弘。
作为一种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其功用不限于世界史研究,用来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其它分支学科,同样能够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出现新境界。
1993年吴先生逝世后,社科院历史所林甘泉先生发来的唁函中,表示他对吴先生提出的世界史观的兴趣与佩服。他说,他们计划编写一部中国经济史,曾准备当年晩些时候来武汉大学与吴先生面谈,看如何把世界史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吴先生提出的世界史观,其影响还辐射到国门之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史学家李来福在中文史学杂志上看到吴先生的学术思想,怀着极大兴趣,专程来武大与吴先生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认为这一博大学术思想在东方国家的学者中是罕见其例的。
吴先生新的世界史观的形成,是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吴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于1939-1941年在西南联大读经济史研究生期间,在对西方文献的阅读中,随着知识的增长,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与中国做比较,学历史宜作比较研究的思想由此萌芽。吴先生在此思想推动下,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和西欧中古后期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封建统-运动中的作用作比较的论文,可算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起步之作。
1944-1946年,吴先生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继续用比较方法,从君权与法律的关系入手,对中古前期西欧诸封建国家的君权与我国周代各诸侯国的君权进行比较,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并非有君权之始即已如此。
在出现君主专制之前有相当长的时期君权是受约束的,从而批驳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自古君权就是专制主义的论说。吴先生的这一学术观点,构成他的博士论文的主旨,也表明吴先生在运用比较方法上又向前迈出一步。
1947年吴先生回国在武汉大学执教。在一段时间里,虽不见吴先生用比较方法撰写的历史文章刊出,但他对比较方法的思考则向着更高层次的提升于酝酿之中。吴先生在自传中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教学与研究中较多接触古代世界历史,其后参与主编四卷本《世界通史》,因此视野更加宽阔,对历史问题的思量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知晓我国世界史着作中流弊之所在,因此从简单地运用比较方法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问题的比较,进而逐渐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
1964年发表在《江汉学报》上题为《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一部名副真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
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吴先生所阐述的世界史观从此揭开帷幕。
然而当吴先生就世界史观有话要说之时,国内政治形势大变,文化大革命爆发,笼罩着极左思潮雾霾的学术氛围使吴先生欲言又止,沉默无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界的自由空气,让吴先生把在胸中蓄积已久的关于世界史观的构想,形诸文字,喷薄而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吴先生写文章,作报告,给研究生讲授史学史课程,都是围绕着阐述其世界史观而作。
吴先生在用语言文字表述世界史观的同时,还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组建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齐世荣先生主编六卷本《世界史》,以期在科研和着作实践中,把世界史观付诸实施。
在这里尤需一提的是,吴先生在表述和实践其世界史观的十多年里,正是他从七旬至八旬的古稀之年。从1978年起,在间隔不长的时间里,吴先生先后做过脑部、肺部和结肠三次大手术,而后两次手术都是令人生畏的癌症。手术之后还要进行多次化疗。有一次化疗过程中,白血球降至危险的最低值。
有一次病情恶化,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吴先生在很长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吴先生以高龄抱病之身,在病榻上,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持续不辍。当时凡知此情形者,无不为吴先生的敬业与奉献精神所感动,泛起敬重之情。
1992年夏,吴先生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一部分样稿寄给吴先生审阅。吴先生冒着武汉夏季的炎热酷暑,在对样稿看过后,他作为主编,从全书宏观上到书稿微观上都有一些话要说,以期推动全书在既定思想指导下有所提高。
为此,1993年4月,在吴先生80华诞庆祝活动几天后,召开六卷本《世界史》编要扩大会。吴先生在会上发言,讲他事先准备好想要说的话时,瞬间一语梗堵,不及抢救,猝然离世。吴先生就是这样带着他想说而未说完的话,想做而未做完的事,不无遗憾地告别了人世。
吴先生从不满30岁的青年时代开始,到80岁耄耋之年,凡50载,钟情于世界历史科学,潜心于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感佩的业绩。在将来某个时候,当有人撰写我国史学史时,作者会以浓墨重彩之笔,把吴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作出的重要贡献载入史册。
三、未竟之业 这里说一个统计数字。在1992年出版的《吴于廑学术论着自选集》中,共收录30篇文章,其中写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章占有22篇。这个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吴先生的学术成果绝大部分出自改革开放学术比较自由的十几年里。可惜岁月不饶人,如果上天能给吴先生以更多的工作时日,在如今比较适宜的学术环境里,吴先生的聪明才智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创造出更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吴先生写的文章中和他平时的谈话中,屡屡述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关乎世界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以新的世界史观作专题研究。比如,地中海区域在世界史自古至今发展过程中处于何等重要地位?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何以会发展至鼎盛期,以致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几乎都被宗教信仰所笼罩?蒙古人对欧亚地区大规模的扩张征讨活动,对世界联成一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源出犹太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接触中会发生强烈的相互排斥和敌对?而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华文明背景下却能以和平方式使儒释道得以融合?等等。
吴先生说,对这类问题如果能以新的世界史观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于全面深入认识世界历史发展会大有裨益。吴先生之所以屡屡谈及这些问题,说明在他来说,想必是素有所思,成竹在胸的,只是没有来得及动手去做。
此外,吴先生健在时,曾尝试创作一部新的世界史着作,为此他和武汉大学历史系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规划设计了一部名为《郑和与哥伦布时代的东西方世界》的专着,力求用新世界史观,深度揭示15、16世纪由农本而重商转折时期东西方迥异的历史面貌,成一家之言。可是这个设计完成不久,吴先生去世,这部孕育中的专着和上述那些重大历史课题一并成了未竟之业。
屡屡述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关乎世界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以新的世界史观作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