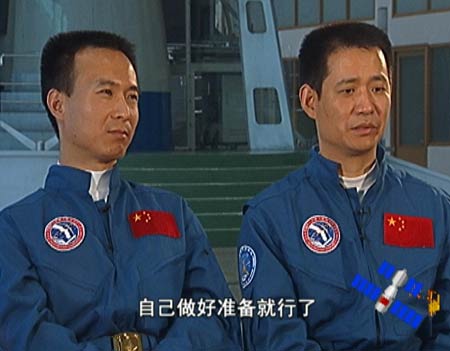孔飞力叫魂 【专访】田海:《叫魂》是本好书 但孔飞力不能只用一个例子来证明观点
田海(Barend ter Haar)对中国历史上的谣言的兴趣始于1980年代他在莱顿大学求学时的博士论文。
彼时,这位日后成为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荷兰学者并不知晓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正在撰写《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虽然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东亚系主任韩书瑞(Susan Naquin)知道他们俩的研究方向有相关性,但她也一直认为这是两项独立的研究。
田海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白莲教。这一中国宗教史上大名鼎鼎的"秘密民间宗教组织"实际上并非指代某一特定群体,而是一种想象——田海得出的这个结论部分论据来源于对明代中期流传的谣言研究,这令他对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谣言大感兴趣。
"一方面这些谣言只是谣言,而且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和官员无法理解谣言是如何以如此快的速度传播的——在今天仍然如此——谣言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捉摸的,因此国家倾向于夸大谣言背后的组织,白莲教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
"谣言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田海在撰写《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一书前就意识到的事。而在真正着手进行研究后,他仍然为口头文化在传统中国的重要程度感到惊讶。在书中,田海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典型故事(谣言)的流变,如老虎外婆、樟柳神、旱魃、剪辫、后宫选秀等,并就其引发的恐慌及民众针对恐慌采取的应对之法,尤其是选择替罪羊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此同时还分析了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对这些故事(谣言)作出的反应。
与孔飞力关注国家和精英群体不同的是,田海对扮演"谣言传播者"角色的民众更有同情心,在他看来,讲故事是人们为变动不安的世界寻求解释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当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时,你能怎么办?"而谣言传播的巨大力量让他吃惊不已,其中最惊人的一个发现是老虎外婆的故事和小红帽的故事存在高度相似性,"在欧亚大陆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相似的故事结构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所以这本书向我们展示的是口头故事的力量。"
谁会是谣言的替罪羊?一个又一个案例表明,某个具有边缘外来者地位的人将会成为受害者,那可能是村子里不受欢迎的老女人、四处云游形迹可疑的道士和尚、鬼鬼祟祟的乞丐、陌生的商人或无论是外表还是行为方式都迥异的西方传教士。
"谣言事关社会变革,事关生活中越来越常出现的陌生人。陌生人被阐释为恶魔或非常危险的生物,所以你要么驱逐他们,要么忽视他们,要么处决他们。"对外来者的恐惧和对未知事物的焦虑是谣言的温床,而谣言的激烈程度会随着人们与社群局外人的互动增加而增加。书中的这一重要结论放在反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当下仍然有现实关照意义。
田海在个人网站自我介绍中说过:"我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展现为何传统文化和文化模式仍然与当下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来说,他是对的——只要人性未变,我们的行事、思考方式就仍将延续过去,万变不离其宗。
界面文化:你是怎样对中国民间传说产生兴趣的?
田海:对我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民间故事的。我称它们为"故事"(stories),而不是"民间传说"(folktales),因为不仅仅百姓会讲这些故事,所有人都会讲这些故事。当然,这些资料都是由社会精英整理记录的,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包括精英在内的共享文化。
我的第一本书,也就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关于白莲教的。我发现"白莲教"这个词不是指一个特定的组织,而是一个想象中的形象。我的论据部分基于对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流传的谣言的分析,我发现谣言其实只是谣言,但有些时候当地官员或当地精英会称之为白莲教。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一方面这些谣言只是谣言,而且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和官员无法理解谣言是如何以如此快的速度传播的——在今天仍然如此——谣言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捉摸的,因此国家倾向于夸大谣言背后的组织,白莲教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
差不多在2000年的时候我想我的材料准备充足了,我开始对谣言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我挑选出了几个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谣言,比如有人偷取器官、偷取他人身上的气、对剪辫的恐惧,等等。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告诉读者谣言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们非常强大。
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地将之作为研究对象,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一些史实。比如1891年(光绪十七年)的江南教案。这其实不是哥老会的阴谋,而只是由谣言错误构成的阴谋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偶遇了小红帽等许多其他的材料,这增添了研究的趣味。
界面文化:在你开始做研究之前,你的主要假设是什么?哪些假设被证实了,哪些没有?
田海:我早就知道谣言很重要,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会发现那么多谣言。这是其中一个。
我没有预料到1891年的江南教案真的只是谣言所致,哥老会是个人们臆想出来的组织。
我肯定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会发现中国的"老虎外婆"故事就是小红帽的前身。我当时想,这真有意思,然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很多的钱去找到更老版本的小红帽故事,因为欧洲的图书馆里没有这些书,我必须花钱购买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微缩胶片,只为了找到我需要的6页纸。这是我为影印材料花过的最多的钱!我大概花了1000美元来购买胶片,那些书页对我的小红帽研究非常重要。
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小红帽是个源自中国的故事,在某个历史时刻流传到了欧洲。我不能确切地证实这个论断,也许西方学者会不同意,如此重要的西方故事实际上来自中国,他们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对我来说这也很意外,15世纪的中国故事和之后在西欧讲述的故事居然拥有相同的故事结构,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非常惊人。
界面文化:关于"老虎外婆"和"小红帽"这两个故事,谣言真的有可能跨越文化的界限从中国流传到西方吗?
田海:对我来说这体现了口头文化和口头传播的力量,整本书谈的其实都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的力量。这不意味着书写文化就不重要了,但的确存在一种纯粹口头的文化,而且它传遍了中国。谣言从南京传到南方或传到北方,有些时候传播的速度快,有些时候传播的速度慢。但这展现了口头文化在传统中国是多么重要,这让我感到惊讶。
(小红帽)的真实性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我惊讶的是我可以通过文本分析证明它。老虎外婆在中国曾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如今我在牛津和荷兰的中国学生当中虽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我们可以证明直到1950年代甚至更晚这个故事非常流行。事实上这是最受欢迎的民间传说之一,你还可以在韩国和日本发现它。我可以证明你能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发现完全相同的故事。这肯定是通过口口相传的。这真令人惊讶。
我最喜欢的发现是,在18世纪早期的中国版本的故事里怪物和女孩之间的对话。女孩问自己是否能出门撒尿,怪物说你可以在床上撒尿。女孩说不,怪物说你可以在床前撒尿,女孩又说不。怪物说你好吧你可以出门撒尿,但我要用你的弟弟的内脏做的绳子绑住你的脚。
我们可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民间传说中看到相似的这三个问题、三个回答。这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是非常接近的故事结构。在欧亚大陆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相似的故事结构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所以这本书向我们展示的是口头故事的力量。
界面文化:谈到谣言研究,中国读者对孔飞力的经典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使用1768年的谣言案例来讨论帝制中国晚期的国家控制问题。你的研究是否受到了他的研究的影响呢?
田海:其实没有。他读过我交给出版商的手稿,我肯定他也不是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对他的作品同样持有批评意见。
我持批评意见是因为他只用了一个例子去证明一个非常大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你有这么大的观点,你需要更多的证据。当然他写得非常好,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不可能写出那样文笔优美的书。这是一本好书,原始资料很棒。他很幸运的是在1930年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史料档案了。他引用的大多数材料都是在1930年代出版的,当然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材料。
他的论点是乾隆使用谣言来控制他的官僚系统,他把乾隆描述成了一个有些幼稚、迷信的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我的资料发现当地官员有些时候是相信这些谣言的,当然不是全部,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乾隆会相信这些谣言并不奇怪,也许他周围的臣子就相信这些谣言呢。我认为在1768年的谣言爆发后,乾隆能够组织起那么多的镇压活动展现了乾隆朝的国家力量。
如果你比较孔飞力的研究和我的研究,你会发现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他想说明的是乾隆时期体现了盛清时代的衰弱,我认为这并不准确。乾隆时期虽然有自己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前现代国家,它就是要面对一些它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这在中国是这样,在英国是这样,在哪里都是这样。
我认为乾隆的这个谣言案例反映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能够在谣言爆发后展开彻底的调查,官员们审问了所有相关人员,发现这只是谣言,然后决定说好吧,这里没有真正的危险,我们可以放下心了。这里的结论是这些谣言不存在真正的危险,这个想法是非常现代的。对我们来说这些谣言不危险,这是个非常现代的洞察。他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实际上就是抱持着清代走向衰弱的传统概念。
清代只是在19世纪非常不走运。有些问题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解决的,比如黄河的泛滥、鸦片战争、难以理解的英国入侵者、太平天国。清朝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不认为清朝像我们所想的那般孱弱。我还研究了很多1768年之后的恐慌事件,比如说光绪二年(1876年)的恐慌事件实际上传播范围更广,恐慌程度更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乾隆时期的例子,官员们迅速高效地回应谣言事件。每个时期都有恐慌的事件发生,政府实际上是很难对付谣言的,即使今天仍是如此。
界面文化:我在阅读这两本书后的强烈印象是,孔飞力关注国家和精英群体,他对人们在传播谣言中起到的作品是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的。通过指认并处决"叫魂者",人们牟取私利,而这样一个冤冤相报的社会则反映了帝制极权的系统性失灵。但在你的书中,你更加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讲故事被描述为一种理解这个时刻变动的世界的方式。你是如何理解人们在传播谣言中扮演的角色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田海:在传统社会,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没有电视和广播,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是现在我们对信息获取的控制力也是有限的,在西方也是这样。通常来说,只有很少的人能很好地掌握究竟发生了什么。
谣言是很容易产生的。当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时,你能怎么办?我对人们有更多同情心,我对当地官员也有更多同情心,在一个县里只有一到两位官员,他们怎么能够阻止谣言传播?这是非常难的。事实上,他们阻止谣言的方式通常是杀掉一些人——无论是传播谣言的人被杀还是一些替罪羊被杀——这样人们就会害怕编造故事了。
我研究了许多案例,我的发现是,我们很难把谣言和国家的强弱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官府就是孱弱的,它也只能是孱弱的,因为只有一到两位官员。国家就应该是孱弱的,只有现代国家是强势的。和穷国相比,更富裕的国家能有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因为获取控制力是昂贵的。
我不指望18世纪或19世纪的清政府能够控制谣言,这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期待。看看美国吧,美国一直有的是一个弱政府,直到1920年代美国都有针对黑人的私刑发生,这也是因为国家太弱,无法阻止种族主义。即使是今天黑人还会因为自己的肤色被杀呢。
在我的书中,我收集了许多案例证据,发现国家的确是虚弱的,但它面对谣言一直是虚弱的。谣言是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有些事件发生了,不是因为某个真实的原因,比如人们在挨饿,或者物价在上涨,而是因为人们以为物价在上涨,或者人们以为有人在剪他们的辫子。这再次说明了口头信息的力量。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研究了五个故事,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在各个朝代不断浮现并引发恐慌。为什么这些故事或故事原型会一次次地重现呢?
田海:我认为大多数人不会凭空发明新故事。在口头文化中,人们习惯于讲相同的故事,因为这就是文化传承的方式。当下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我们会看到人们祈祷。无论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或者新加坡,汉族人的祈祷方式都是非常接近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别人就是这样教他们的。如果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祈祷,我们就很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这和语言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彼此了。为了理解彼此,你需要讲述同样的故事。这是我们看待这个现象的其中一个角度。
在书中我没有过多提及的一点是某些谣言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险、难以证明的观点。比如说我在书中讨论了夜间的怪物,他们会剪辫、会坐在人的胸口上,等等。这些是发生人们将睡将醒之间的真实体验。
在传统社会,夜间是没有电灯或油灯的,你只有蜡烛。蜡烛熄灭时,夜晚是非常暗、非常安静的,当你醒来时你也许会很害怕。当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坐在你的胸口上时,我想你应该会非常恐惧。然后你会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你想起了那些传统故事,你就用它们来解释原因。
我认为这些故事就像教我们如何祈祷的故事一样。它们是我们习得的故事。在西方我们就会有其他的故事了,我们同样会运用那些故事去解释一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当一件事情发生、我们运用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让事情看起来就像故事里的情节一样。
作为西方人,我看待现实的方式会和你有所不同,因为我关注的重点会不一样。我认为故事是传承文化的基本方式,这些故事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它们同样塑造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在今天也是如此。
界面文化:我记得在书中你尝试解释过为了什么人们会编造出那些夜间神秘动物的故事。
田海:是的。想想看吧,人们曾经是住在乡野郊外的,那可不是现代的上海。当你住在中国的乡野,你与动物们的距离是更近的,它们可能是狐狸、猫、老鼠、蛇,等等。许多动物是在夜间活动的,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被它们吓到。
所以你就需要这些故事来解释。在黑眚的故事里,人们说黑眚长得像狐狸、像猫。如果是在现代,他们就会说他们看到的是狗、猫或狐狸。因为当时的人们在故事里了解到黑眚这个威胁,他们用自己对这一威胁的理解重新阐释了周遭的现实。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书面材料对谣言的传播影响甚微。这似乎意味着口头文化的力量——作为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压过了以文字为和读写能力为标志的精英文化。我们要如何理解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和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之间的张力?
田海:这是一个惊讶到我的结论。首先我要指出我不喜欢"通俗"这个词,对我来说这就是"口头"。这很重要。我认为我们低估了口头文化的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如果你研究精英文化,文字就很重要,尽管我们通常忽略文字口头传播的这一面——人们背诵文字,当人们在传统中国学习读写时,文字需要在言语交流中解释。如果你不会书写,你就需要用心记住这些文字。
我认为我们低估了口头交流的重要性,而19世纪标志着一个很大的变化。19世纪识字率提高了,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地区。你能够看到更多的书面材料,它们变得更重要。但如果你把传统中国社会视作一个整体,口头文化一定是更重要的,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笑)。
界面文化:而且精英群体也是可以参与口头文化的,对吧?
田海:的确如此!而且参与的很多。我的一个长期论点和研究兴趣就是比较北京、江南、岭南这三个地区和北欧与西欧(特别是荷兰与英国)之间的差别。在这些地区你可以看到文字的广泛使用,但在中国,文字是被社会中的部分群体使用的。
谣言几乎从来不通过文字在中国传播。人们不会在信中说:"嗨,你听过这个谣言吗?"这封信抵达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收信人想:"哦,我应该跟别人聊聊这件事。"在19世纪已经有报纸了。上海的《申报》是在谣言抵达上海之前报道南京地区的谣言的。
尽管一些人已经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些谣言了,谣言真正在上海爆发却是在一两个月之后。所以口头传播显然比书面传播更重要。但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会在信中写到谣言,而谣言跟随着信件一起传播。这十分令人惊讶,所以我想在之后做更多的研究,讨论口头文化在传统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界面文化:如果我们把谣言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去看,很明显的是人类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动物或其他的神秘生物成为替罪羊。这在晚明时期尤为明显,在当时整个社会前所未有地商业化。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趋势?
田海:我的结论是,当社会更加商业化的时候——明代的商业化程度远甚于宋代——人们会在生活中遇到更多的陌生人。当然在现代城市社会中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但我们在讲的是中国农村,在那里人们通常认识周围的所有人。
当你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认识彼此的社会中时,任何外来人都会被视作一种危险。那是一个人们相信鬼的存在的时代。这些陌生人就被当做鬼,他们不是人。然后人们把外国人当做鬼,在谣言中这些陌生人成为攻击目标、被当做了某种恶魔。
在传统中国,人们是如何对待恶魔的?杀掉他们。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人们也把日本人称为"日本鬼子",背后的概念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恶魔,他们不是人,你就可以杀掉他们。
这不是一种好的思考方式,但这是传统中国非常正常的思考方式:妖魔化他人,然后你就可以杀掉他们了。当然替罪羊的波及程度远远不及西方的女巫大搜捕。我认为谣言事关社会变革,事关生活中越来越常出现的陌生人。陌生人被阐释为恶魔或非常危险的生物,所以你要么驱逐他们,要么忽视他们,要么处决他们。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发现是那些针对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大多数是天主教传教士)的谣言:他们被指控杀害、食用中国儿童。这些故事其实不是由19世纪的当地士绅发明出来的,它们早就存在,只不过之前的指控对象是中国人,然后转移到了西方人身上。
这意味着一直以来西方文献和中国文献中的反西方运动并不是真正的反对基督教,而只是人们把西方传教士当成术士了。也就是说,当地百姓虽然部分理解传教士们在做什么,但他们的行为非常奇怪,他们不理解他们做这些事的真正意义。如果把西方人放到一个已经存在的故事框架内,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理解了很多。对这个问题我期待看到我的中国同行们会有怎样的见解。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在书中描写的谣言历史中,女性,特别是老年女性越来越被污名化为内鬼。这是如何反映前现代中国的性别关系的?
田海:我很确定谣言针对的是陌生人,对于这个结论我有很多证据。关于老女人成为替罪羊,我在两个章节中讨论了,一个是"老虎外婆",我有四到五个例子,然后在"旱魃"故事中又出现了。但这就是我能找到的全部案例了,目前来说证据不足,这可以成为一项新研究的假说。
实际上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假说,因为它可能是真的。我们知道中国崇尚孝道,但不是所有人都想孝顺长辈。你需要照顾你的(外)祖父母,特别是你的(外)祖母,这很费事。她也许很惹人烦,也许总是颐指气使,也许生了重病。照顾她还很花钱,而且她又没有工作能力。这种想法并不好,但的确有人会这么想。我认为那些被视作"老虎外婆"的女人都是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女人。
界面文化:20世纪以来中国见证了巨大的变化。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倡导与中国传统决裂,而全民教育也第一次大规模地培养出了能够读写的公民。上升的识字率和抛弃文化传统会给谣言传播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吗?
田海:我认为谣言一直会存在,在中国会存在,在西方也会存在。我意料到会出现不同的谣言,不同的故事,比如说反日故事或反韩故事。谣言的确有所改变,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互联网、手机和微信,这改变了谣言的性质但谣言仍旧是谣言,它们只不过传播得更快了。谣言传播的方式改变了,也许一些谣言的内容也是。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讲黑眚的故事,但很多中国人相信UFO的传说。
如果你的意思是识字和受过教育会阻止谣言的传播,我并不同意。至少我确定在西方我们仍然在传播谣言。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在传播谣言,我们讲述同事的故事、父母的故事或孩子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它们会流传开来。我认为讲故事是我们与彼此交流的方式,在人们讲故事给别人听后,故事会发生变化,但它们是有一定的变化规则的。讲故事恐怕不是一件存在于过去的事情。
界面文化:实际上,关于器官盗窃和绑架的"采生"故事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到。很多人相信一些乞丐属于秘密的犯罪组织,他们会绑架儿童,盗窃他们的器官。虽然我同意受过教育的人仍然有可能传播谣言,但为什么他们还会一次次地去讲这些老生常谈的故事呢?
田海: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谣言仍然与我们同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些时候谣言里有真实的部分。现在的确存在器官移植,人们会贩卖自己的器官,所以这就会是谣言的源头。处决犯的器官也会被挪作他用,这创造了谣言的空间,因为如果处决犯的器官能被利用,其他人也许也会这么干。
我觉得有些谣言到处都存在。比如说乞丐绑架小孩,在西方也有同样的谣言。在我小时候,我听过的故事是说吉普赛人会盗窃孩子,因为吉普赛人总是偷钱。有些时候某些吉普赛人的确会做一些不正当的事,但并不是说只有吉普赛人或乞丐会做这样的事啊。关于孩子的谣言比较好理解,因为孩子是我们最珍贵的所有物之一;器官也是如此,你可以失去一条腿,但你不能失去你的器官。这些故事完全消失需要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你还会听到新的故事。
界面文化: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外来者的恐惧和对未知事物的焦虑是谣言的温床,而谣言的激烈程度会随着人们与社群局外人的互动增加而增加。这个结论将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反全球化浪潮提供些什么新的启示?
田海:我认为大背景是创造恐惧。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恐惧感在加强。那些居住在富庶的大城市的人在遇到过许多外国人后明白他们也许因为总是随时随地自拍或什么其他原因很烦人,但这就是他们讨人厌的全部理由了。
而那些只会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的人在害怕。反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人们认为这些外国人会争夺他们的工作机会。很多时候这个想法并不是事实,但这就是他们想的。无论真实与否,这制造了恐惧。所以有些人觉得闭关锁国——把外来者隔绝在法国、荷兰或美国之外——才是安全的。
这并不正确,因为这一恐惧机制在国家内部仍然会发生。我认为这种恐惧和我在书中讨论的恐惧是非常相似的。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对我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学习不同的文化。你不需要喜欢他国文化,你不需要接受全部,但你要试着去接受它,竭尽所能地去学习它。所以就西方的困境而言我会提出的一个方案是让伊斯兰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学习中国人的做法,你们在处理回族问题上更加成功。你需要接受他们就在那里的事实,然后你把他们的文化吸收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
学习异国文化、教授异国文化、旅行,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当然这在现在还存在困难,一些西方国家因为经济原因畏惧中国,他们有些时候是对的,有些时候是错的,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恐惧而言——这也是这本书的主旨——你只有通过旅行和学习他国语言文化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