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作品 寻找那支文化的根——评李存葆的散文作品
李存葆最先是以军旅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他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作品为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之后他开始转向散文创作,并一发不可收拾。李存葆之所以在文体创作上进行转变,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当今的社会太复杂了,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
近距离看生活往往看不透,我就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写作能使我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舒晋瑜:《不能只用一种调子唱歌——访军旅作家李存葆》,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9版。。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我为捕虎者说》、《鲸殇》、《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国虫》等散文名篇接连问世并一度引起文坛的剧烈反响。
李存葆的散文作品既有“文化大散文”的气度,也有“生态散文”的质地,但归根结底,“文化”是李存葆散文的核心,正如他所言:“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的圣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
”舒晋瑜:《不能只用一种调子唱歌——访军旅作家李存葆》,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9版。因此,李存葆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他以散文的笔法临摹、挥洒着对中华文化的释解与感悟,与此同时,在对这些文字的抒写中,李存葆又不断挖掘着文字背后的隽永内涵,他总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探寻与纪实中剖析着几经历史淘洗所涤去的、残存的以及更添的东西,并从中寻找着精神表达的视角。
尽管时代的进步一直在改变着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但在李存葆的兼具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的杂糅创作下,我们读到的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寻根中却无奈地发现断裂了的文化之根。尽管“寻根”的创作主题在现当代文学的视阈中屡见不鲜,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浓烈的“寻根”意识下陆续出现的一批“寻根小说”,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在当下人们的生存理念中,“寻根者”所努力寻找的文化之根已被渐渐地改写,慢慢地消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已不再张扬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不再规导原始生命的形而上存在,而是急功近利地变成了生存的手段与辅助器具,乃至是解剖自然、社会的刽子手。
这是一种悲剧,人类也正以悲剧的形式上演着自我、他人、群体,甚至整个人类的悲剧。
李存葆的散文正是在寻根文化的过程中面对着这种“悲剧”的时代性演绎而发出的警世信号,他所捕摄的文化之根既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伦理道德观念,比如“温良恭俭让”,比如“仁、义、礼、智、信”,其中也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在物化需求几乎已经凌驾于精神理念之上的现状下,满一己之需,逞一己之快的生存欲求几近切断了来自这块大地的文化根基,而在对这种“悲剧”的透视中,李存葆正是以“审丑”的方式完成了对“审美”的注解,因此,在文字背后响起的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批判,而且在知识分子孱弱的呐喊之音中也体现了生命个体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维护。
李存葆在《大河遗梦》的《也说散文(代序)》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
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李存葆:《大河遗梦》,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9、34、39页。
在李存葆的一篇篇洋溢着感性的直觉视角和理性的深度思考的散文作品里,我们也看到了李存葆铭刻于心的那种“正义和良知”,当然,这种“正义和良知”也是当下的生存个体所应义不容辞地扛起于肩的重任。
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而《大河遗梦》这篇散文就体现了李存葆对中华民族,对历史文化寻根的悲悯与忧虑情怀。
“黄河”的确正如李存葆所说的,它“早已演变成一种偌大的文化符号,凝结在华夏历史与传统的骨髓中,流动在东方文明的血脉里。”李存葆:《大河遗梦》,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9、34、39页。
李存葆还以李白、段克己、李东阳、查慎行等人的诗句进一步证明了古往今来黄河这天上来客的慑人气魄与雄浑气度,而且,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簿中,黄河既是“东方巨龙”,也是“中华母亲”,它的“符号”性意义远远大于这条河本身。
然而,今天的黄河却断流了,往昔的敬畏之感,拳拳之情所要面对的仅仅是那裸露的河床,是人们在沙雾弥漫的河床上的牧羊、挖沙,更是“时间愈来愈提前,天数越来越增多”李存葆:《大河遗梦》,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9、34、39页。
的断流现状,斯时斯景,李存葆的内心也是干涸的,他无法忍受不断充斥脑海的昔日黄河图景,无法忍受美好梦境在现实里的轰然破碎,于是,面对审美世界里“美”的缺席和“丑”的存在,作者只好以“太阳老了,月亮老了,历史老了。
黄河,你也老了”李存葆:《大河遗梦》,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9、34、39页。来掩饰那个“符号”意义消解后的悲哀。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黄河的“丑”拷问的是人性的贪婪,黄河的“断流”反思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根须的断裂。当然,面对如此现状,李存葆也只能以哀伤忧叹式的诘问理清黄河断流的现状与后果,但对于断流的缘由与改善问题,只能是忧心式的,呼喊式的,因为在当下社会,群体对于利益化要求的生存共识远远超过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文化符号意义,他们看重的是眼下的物欲诱惑,而非历史性的终极价值。
《祖槐》是对一个具有文化魅力存在的“洪洞”的民族脉络寻根,在这篇散文作品中,李存葆的言说方式是十分清晰的,由对“老鸹窝”的“迷瞪不解”,进而二进洪洞,由对农民迁徙的梳理,进而揭开历史真相的面纱,展现出来的是对当今道德滑坡的质疑与批判,更是对生态恶化的担忧和对传统文明断裂的悲哀。
李存葆通过挖掘洪洞的历史,找到了“炎黄子孙”的由来,找到了关于“巢父、许由”的传说,也找到了“接姑姑迎娘娘”的习俗,但在实际上,这种寻找不单单是为了解惑而寻找,更是为了挖开华夏文明的根基而寻找。这里有“三皇五帝”的历史,这里有尧舜禅让的美谈,这里有隐君子的“人格坐标”,这里也有“勤政爱民”、“注重教化”、“闻过则喜”的历史篇章,厚重的文化积淀正如李存葆所揭示的那样,“洪洞,华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这里浓缩;临汾,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李存葆:《飘逝的绝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68、174、12页。
。但是,历史常常在行进中遭遇磕磕绊绊,而我们在“审美”历史、“审美”文化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它们丑陋的一面,劣迹斑斑的一面,“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灾荒”也是一块“恶瘤”,而“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
李存葆:《飘逝的绝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68、174、12页。
因此,尽管大迁徙也伴随着积极因素的产生,但对于“百姓”这个整体而言,他们的迁徙史也是华夏文明的血泪史。当然,时至今日,“迁徙”已经成为历史,然而,面对今天的“污染”、“恶化”、“狂采”、“滥伐”,这又怎不是华夏文明的又一次血泪史?面对着一串串的问号,李存葆即使呼喊“归去来兮”,也只能是一种“默默呼唤”,“梦中寻觅”。
对于承载厚重华夏文明的“黄河”、“洪洞”等特殊历史文化符号,李存葆以置身其中的姿态清理着既感性又理性的自我心理体验,既有着深深的眷恋,也有着浓郁的哀叹,但是对于爱情的态度,李存葆在《飘逝的绝唱》里,相对而言,是清醒的,理性的,是浏览翻阅时的审美,也是置身于外的旁观。
《西厢记》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咀嚼不尽的爱情经典,在李存葆的眼里,它也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寻根。
《西厢记》是“美”的代言,也是对“美”的诠释。不论是“永济”这块滋养“美”的“文化土壤”,还是剧中人物崔莺莺的绝色外貌,张生的憨态可掬,红娘的热心衷肠,李存葆都给了它们“美”的定义,而对于两心相印却遭遇阻挠,几经挫折并最终冲破险阻的崔张爱情,李存葆更是连用六个对“经典爱情”的礼赞方式表达对这种经典爱情的讴歌。
因此,这种“美”既是可圈可点的真实存在,也是流动在传统文化里的精神旗帜。另一方面,“李存葆用雄奇俏丽之笔对《西厢记》的美学意蕴进行绘声绘色的揭示,同时,对大‘丑’进行猛烈的挞伐。
”李钦业:《一曲美的赞歌——评李存葆的大散文〈飘逝的绝唱〉》,载《当代文坛》,2002年第2期,第60页。于是,在李存葆的视线里,王实甫笔下的爱情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被“稀释”了,甚至随着“快餐”文化的到来,它也摇身一变,由“经典爱情”变成了“快餐爱情”,而“崔莺莺”们乐于被“四奶”、“五奶”化,“张生”们则将爱情“儿戏”化,面对“美”的被消解、被颠覆,面对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根基的抛弃,李存葆是无奈的,因此,他最后发出了“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李存葆:《飘逝的绝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68、174、12页。
的质问,由此,在对深陷欲望社会的人们的质问中传达着一位有着沉重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种忧心忡忡的批判口吻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道德良知与警世意识。
李存葆对“国虫”的界定是主观化的,正如他所言,“乃笔者一人之谵语耳”李存葆:《李存葆散文》,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240、239、124页。。尽管如此,他却是在做着对民间众生相的生存状况的寻根。
李存葆对“国虫”的这种界定也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因为蟋蟀在历朝历代也有着自己的文化玩味色彩。从殷商时代“夏”字、“秋”字状“夏蝉”、“秋蟋”开始,中华民族的“蟋蟀”文化史也揭开了序幕。无论是《诗经》的记载,还是唐诗宋词的抒写,无论是高堂之上的宠爱,还是庙堂之下的喜欢,蟋蟀都沾染了文化的色彩,甚至还出现了《促织志》、《蟋蟀谱》、《斗蟋随笔》等专门记述蟋蟀生命、生存、生活的书籍,当然这是与蟋蟀这种小精灵的“歌手”、“斗士”身份密不可分的。
然而,即使这样具有历史文化意蕴的小动物,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今天也具有“金钱”的代偿意义,盛产它的那片土地上也布满了挖掘“金钱”的脚印。而在“玩蛐蛐”、“斗蟋蟀”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窥见虚荣、豪赌、阴险等等这些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词语,由此可见,“玩”、“斗”“国虫”的实质体现的是人性的玩物丧志和阴险狡诈,留给人类的只能是一片颓废的精神荒漠。
因此,面对这样的人性裂痕和精神选择,李存葆在篇末道出了“玩蛐蛐”的“度”的问题,那就是“玩蛐蛐只观其斗而不赌不失其雅,听蛐蛐鸣唱,才是玩蟋人的至高境界”李存葆:《李存葆散文》,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240、239、124页。
。实际上,这不仅是“玩蛐蛐”的“度”,也是众生人性释放的“度”,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而李存葆洞彻是非的这种长远视角体现的既是一己的理想,也是一种对精神理念的呼吁,具有崇高的审美内涵与责任意识。
在《我为捕虎者说》、《沂蒙匪事》、《鲸殇》、《净土上的狼毒花》等散文作品里,李存葆苦苦寻找着他心中的传统观念及伦理道德方面的根之所在,但与此同时,他也以“绝唱”的形式表达了在追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断裂现象。
力大无比,勇气过人的“捕虎者”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却遭遇了“能与虎斗,莫与人斗,有些人心比狼狠”李存葆:《飘逝的绝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68、174、12页。(《我为捕虎者说》)的悲哀,这是与“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老传统相背离而存在的现象;在《沂蒙匪事》中我们看到的是血淋淋的鬼蜮世界,而杀人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平淡无奇;《鲸殇》面对的是鲸类的被捕杀,被灭绝,而这和《沂蒙匪事》里人的生命的消失一样的简单,换来的则是人类的欲望满足;《净土上的狼毒花》面对的是两个世界的叫嚣,一个是人类世界里人们大张旗鼓地对“香格里拉”这块精神净土的寻觅,一个是生态世界里自然万物的喧腾以致失去平衡,两个世界的撞击导致的是“即使世俗的香格里拉,也会像希尔顿所担忧的那样,真的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李存葆:《李存葆散文》,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240、239、124页。
然而追溯历史,我们的古老民族抒写的是一曲又一曲的关于“仁爱”、关于“和谐”、关于“天人合一”的高歌,而且,这些带有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色彩的词语在历史的进程中也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推动着人类向“真”、向“善”、向“美”的境界发展,但纵观今日之世界,人们正以另外的字眼代替他们,这些字眼是“物欲”、“权欲”、“色欲”,而“金钱”则成了整个欲海世界的通关密码。
面对一片狼藉的世俗社会,李存葆不断以冷峻的目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在审视“丑”,审视“恶”的活动中进行着“审美”的探索,尽管发出的是声声叹息,但也是有着伤世、警世的意义。
李存葆的散文作品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寻根与守望,同时也以冷冷的言辞表达了对当下社会风气的不满,既质疑了人们的物欲化要求,也批判了他们对古老文化的扭曲、消解甚至是颠覆。当然,在这些作品里,李存葆在寻根文化的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独特、大气的诗意表达方式,而且字里行间也博采了古典文学的精华,并在时代文化语境的交融中体现了一种“大美之珍”王久辛:《沿波讨源的大美之珍——浅谈李存葆近年散文创作》,载《解放军报》,2001年3月22日,第7版。
,而且这种“大”在于“他博大深远的时空观,在于他广阔的心胸和气度,在于他对大世界的深入理解和观察,也在于他的大憎、大爱、大悲、大喜中的大悲悯与大情怀”王久辛:《沿波讨源的大美之珍——浅谈李存葆近年散文创作》,载《解放军报》,2001年3月22日,第7版。
,因此,从这种在对“大”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存葆对“文化”一词的理解,那是一种涵盖古今,纵横历史的“大文化”,当然也体现了李存葆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根的一种期许,期许着它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根植于中华民族,根植于华夏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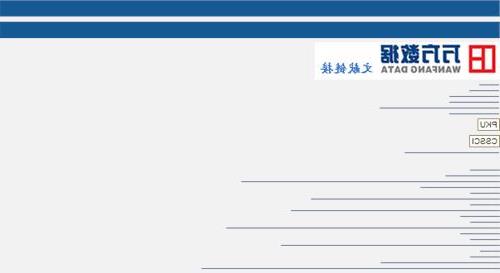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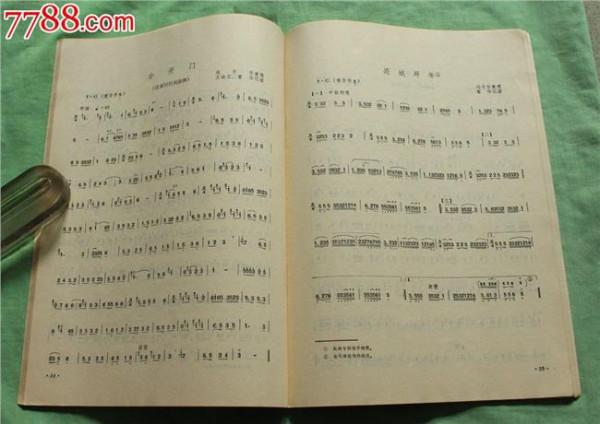




![>李约瑟全名 [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评选]李约瑟:让中国古代科技扬名世界的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d/73/d73e23c9f21c443aa95055b363a945f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