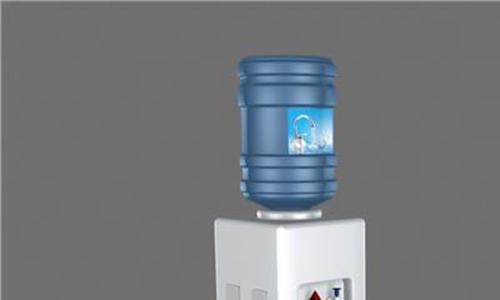云光中与乌兰夫 乌兰夫与战火中的内蒙古文工团
云海苍茫,往事如烟。要想集中回忆一段逝去的往事,就像黑夜漫游草原,茫茫四野,分不清东西南北,理不顺繁纷思绪。然而有时也有例外,虽然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忽然间从脑海里跳出来重新映现,清晰透明,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遗憾的是如遇这种情景,假如不及时捕捉,却又一闪而过,转瞬即逝。我想说的是对乌兰夫同志的印象。我从1946年春天在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初识乌兰夫同志,到1988年12月18日在北京参加乌老遗体告别仪式,整整经历了42个春秋。
在时间表上,1946年是充满喜悦和忧虑的一年。一方面是经过8年浴血奋战,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各族同胞,以狂欢的心情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一方面是蒋介石妄想独吞抗战果实,并且磨刀霍霍以武力相威胁,在人们心头又罩上沉重的阴影,当时的赤峰便是这种局面的典型写照。
街头上随处可见水泥碉堡和弹痕累累的残垣断壁,各式各样的标语,也有各式各样的旗帜。人们都以焦虑的心情担忧着时局的发展。就在这个时候,一颗亮星在赤峰上空腾起,那就是乌兰夫所创办的内蒙古自治学院,它像一块磁石吸引了数百个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青年。
我是1946年春天和几位同学结伴去投奔自治学院的,起因是一张招生简章。明文规定招收有志于从事内蒙古解放事业的各族学生。说明设有政治部和军事部,有本科和预科,有短期生和长期生。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理想的学府。更使我们激动的是乌兰夫这个人物,
从照片上看满脸慈祥,双眸生辉,细长的眼睛和厚实的嘴唇使我联想起先民的血统,他那传奇式的经历更令我们神往。于是,我们决心去碰一碰运气。
出发的晚上,夜幕漆黑,万籁俱寂,只有几声刺耳的鸡鸣。我双手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一床棉被,轻手轻脚地走出家门,想到就此抛下养育我的祖父和孤零零的小弟,难免一阵心酸。这时,大娘从黑暗处悄然向我走来。哽咽地说:“孩子,你放心去吧,家里人我会照看,只是你这一走,不知哪一年才能回来。
”我们唯恐家人阻拦,一律严守机密,不知她是怎么听说的,我只好说:“我只去看看,过不了多久就回来!”大娘道:“家里什么也没有,你就把这个带去吧!”说着塞给我一个小包,我接过来塞进怀里,给大娘磕了一个头,就向集合地点村边的大榆树下跑去。
大榆树下人影绰绰,先前到达的有王惠民、王海山、李鸿贵和李鸿义兄弟,可惜我们几个人中谁也没有去过赤峰,不知该走哪一条路,还是我建议:“从包古鲁村过老哈河,再奔乃林或平庄,到地方再打听吧!”记得头两天还算顺利,边问边走,笑语连天,李氏兄弟带的食物比较丰盛,可能是因为李鸿贵已经结婚,是他媳妇为他准备的缘故。
只有我最可怜,幸好大娘塞给我的小包里除了一块银洋,还有半块月饼尚能充饥。待到第三天下午,翻过一道山冈,远远望见乃林车站,信号旗像是扬着手臂向我们招手。
李鸿义眼尖,看到水塔顶飘扬着的青天白日旗,急促地喊道:“你们看,那是啥?”我们没想到中央军已经抢先占领这个地方,顿时没
了主意,都期待地望着李鸿贵,因为论年龄他是我们这伙人的兄长。李鸿贵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他向我们嘱咐道:“就说我们的家都在赤峰,原在平地泉上学,因为失学要赶着回家去。”
我们临时改变主意,打算绕过乃林从旁边村庄插过去,为此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日暮黄昏才小心翼翼地去进村子。随着一声吆喝,突然几个中央军端着几把刺刀对准了我们的胸口。为了躲避狗洞却又掉进了陷阱,真是叫苦不迭。当晚,我们被锁进库房,加了岗哨。第二天轮流审讯,硬说我们是八路军的探子,而我们反复都说那句话,看不出有什么破绽,只好把我们释放。只可惜大娘送我那块银洋被他们搜去,心中好不伤感。
走进赤峰六道街西头,到处是乐曲飞扬,彩旗招展,一派喜庆气氛。先期到达的同学热情地帮助我们安排食宿。从此便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
4月1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听说乌兰夫院长要来视察,全院师生既兴奋又激动,打扫环境,刷写标语,女生们还换上了鲜艳服装。我们坐在自己的教室里,聚精会神地等待着。9时整,老师喊了一声:“起立!”只见门口走进来一群首长,我一眼认出来,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乌兰夫,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膛,发亮的眼睛,挺直的鼻梁,穿一件军呢大衣,年龄40左右,给人以风度潇洒之感。
他微笑着把我们扫视了一遍,说了一句:“同志们好!”我们忙说:“院长好!”老师向乌兰夫同志介绍着学员们的情况。当走到我的课桌前,老师说了句:“他们就是穿过封锁线来的喀喇沁同学。”乌兰夫特意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