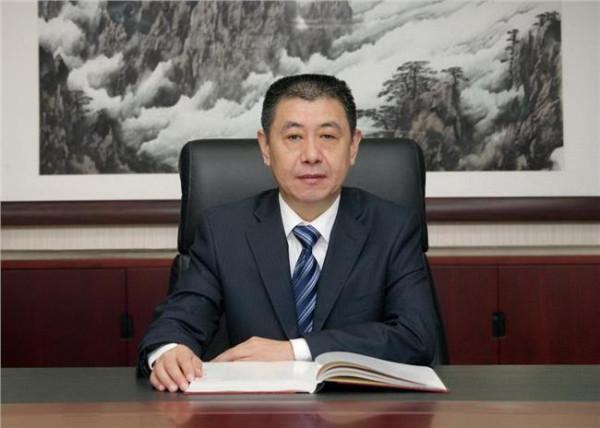李学民散文 【筐篼文学·散文】老黑
老黑不姓黑,只因人长得黑,牙齿黑,人们便喊他老黑。 老黑,烟鬼,从早晨睁开双目,到夜间闭上两眼,除去吃饭,其他时间,烟雾缭绕,烟火不灭。那年头工资低,抽的都是济南两毛来钱的老“泉城”,这颗烟没灭,那颗烟就续上了,用手捏捏烟卷一端,揉掉烟丝,将正在燃着的烟把塞进去捏吧捏吧,含进嘴里又抽起来,往往一天用不了几根火柴。
他夹烟的食指和中指之间,被烟熏火燎的焦黄,似焦黄粘土,又凸起了硬茧;那本来满口的白牙,先开始变黄、又变深黄,又变浅灰,最后便烟囱一般黑了。
说起老黑的烟史,大概这个大院里数他最长,12岁那年丧父,独自赡养着个瘫痪在床的老娘,年小心不小,边上学边种地,苦劳之余,学会了抽烟,家贫没钱,就抽红薯芥子、蓖麻叶子;逢集赶会,来唱戏耍猴玩把式的,他就拣烟头抽。
村里见他可怜,推荐他上了高小,后又出来工作。老黑年轻有力,又有文化,肯吃苦下力,有一年县里搞土地普查,发现他人朴实,善动脑,工作有点子,便调他来城里工作。
老黑没有什么嗜好,惟一就是抽烟,衣服常年就是那么两身,春夏秋冬都一样,冬天无非多上一顶灰色帽子,衣服可以不买,饭菜可以素吃,可烟不能不抽,这一抽就是五十多年。他也曾经忌过几次,但最多不过三天,说是不抽烟了吃瓜子、吃糖块吧,老婆给他买了几回,瓜子也吃了,糖块也吃了,但烟还是没忌死;不抽烟了,他也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便满办公室来来回回打圈圈转,最后转也不管用,脸色涨得发红、发紫,喉咙发痒、干咳,头也觉得肿大发晕,去医院检查,也看不出什么病来,随便拿了消炎药,吃了也没起作用。
老婆就说你还是接着抽吧,同事也说他身体适应尼古丁了,抽烟就会好的。老黑便心安理得一颗接一颗得抽起来,你还别说,烟这么一抽,什么病症真全没了,他又嘿嘿笑着活跃起来。
老黑人好心善,大的小的任凭谁喊他老黑也从不着急,工作也肯吃苦下力,就是不善言辞,因而几十年来,才弄了个副科级,对此他只是笑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抽烟——上班——抽烟——下班——抽烟,周而复始,抽烟风雨无阻,上班风雨无阻。
在这个大院里不识他的人永不识他,识他的人却就那么大一个小圈圈,有数的那些人。我识的老黑,也很尊敬老黑,仰慕他的人品,起敬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无闻的不懈怠工作,尽管我也喊他老黑。
我和他共事那些年里,我所见到的老黑,永远那幅形象:中等偏瘦个子,宽瘦脸膛,短平发,黑褂蓝裤,黑面白帮布鞋,冬天里加顶灰色帽子,迈着碎步,手里永远燃烧着一颗烟卷,走近了,衣服、头发都散发着厚重的烟油渍味儿。
老黑早年娶妻农家,生养一男四女,他在城里工作,妻在农村下力,替他照顾老娘,替他生儿育女。上世纪80时年代后期,他有一悲一喜:悲痛的是他老娘死了,他哭得死去活来,竟然丧期三天没抽一颗烟,亲戚、朋友都吓坏了,这个说黑哥,人去不能复生,你要难过就抽支烟吧!
那个说老黑呀,娘活着的时候你尽了孝道,死了死了,你就节哀抽支烟吧!可是,老黑就是没抽。
母亲去世这年,是个冬天,老黑娘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任谁叫也不清醒。当时老黑正忙着统计年报,急匆匆来了,跪倒在母亲的病床前,悲戚戚喊了一声:“娘啊,我是你的儿子黑子啊!”就这一声,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你别说,十指连心,娘马上睁开了眼睛,缓缓抬起有气无力的左臂,轻轻抚摸着老黑的已经有了白发的头发,嗫嚅地说,“儿子,娘要走了,你爹死得早,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了,你要,你要,你要……”娘没说完,头以歪,人就咽气了。
埋在河崖头上的那天夜里,他坐在娘的坟头一气抽了一宿,夜半了,有人还看到那明明灭灭的蝇头烟火……欢喜的是那年他批下来了工程师,老婆孩子全部农转非,工资也长了,房子也有了,后来孩子也陆续有了工作,又陆续结婚生子,又陆续下岗自己做事,他还照样抽他的老“泉城”。
再后来我便离开老黑,到了外地,长年没了他的消息。有一年有位朋友出发路过那儿,我特地买了两条大“中华”让他替我看看老黑去,那位朋友回来却说,那个单位全部换成了年轻人,一连问了五六个,竟都不识的老黑是谁,他还是多了个心眼,去问年岁大了的门卫老头,门卫说是老黑已经死了三年余了,说着说着,竟唏嘘起来,吧嗒吧嗒直掉眼泪…… 老黑不姓黑,姓迟,是我早年的一个老同事,他要活着的话,今年应该7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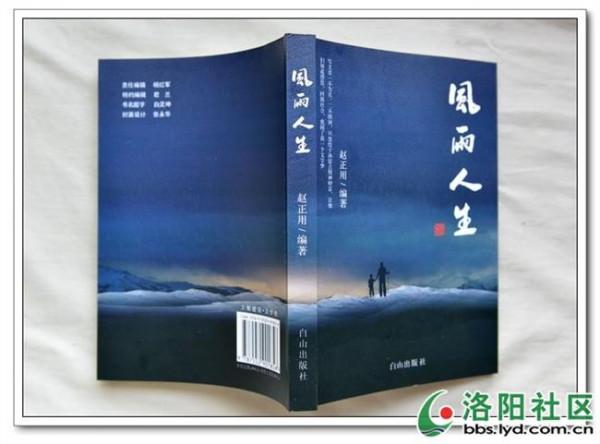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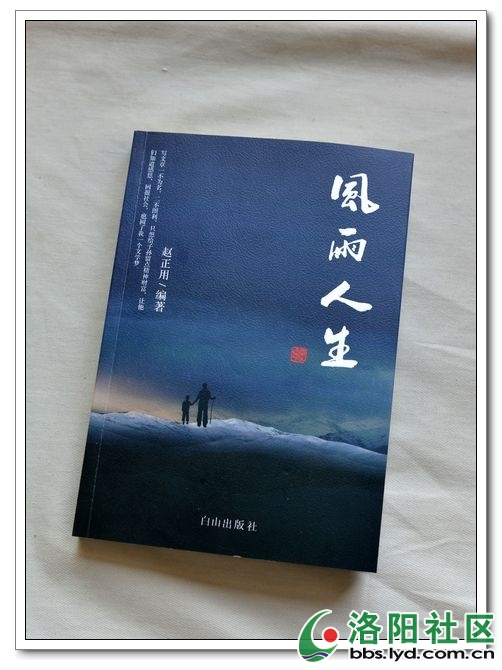
















![>[新闻]中铁四局李学民简历](https://pic.bilezu.com/upload/2/76/2765f0e8010d0d2b1f5c8df94bb77c6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