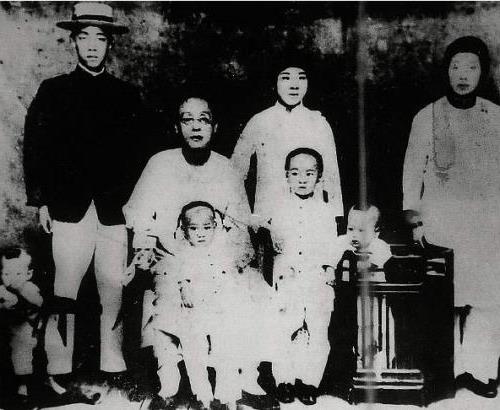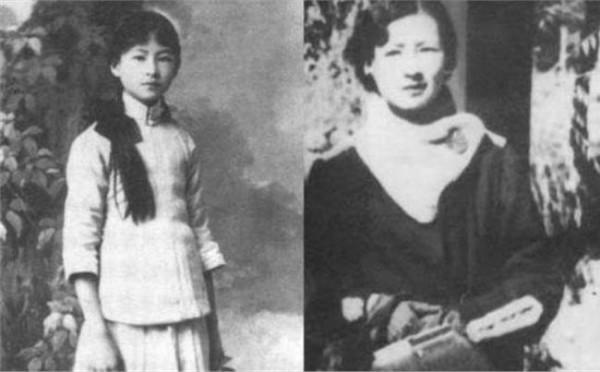林长民与林觉民 说说林长民与徐自华
生于光绪二年的林长民,今年正是140周年诞辰。44岁那年正值人生盛期,却政坛失意,放了个闲差,国联的中国首席代表,远走欧洲两年。寓居英伦时,林长民和徐志摩玩过一场互传“情书”的文字游戏。相约林长民假定有室男子苣冬子,徐志摩反串少妇仲昭,鱼雁往还,情思绵绵。林长民罹难后,徐志摩为追念故人,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披露了其中一封(或只有一封),即有名的《一封情书》。好事的史学家顾颉刚读过作一番索隐,依据徐自华写给林长民的两首词,一首《水调歌头》(和苣苳子观菊):
冷雨疏烟候,秋意淡如斯。流光惊省一瞬,又放傲霜枝。莫怪花中偏爱:别有孤标高格,偕隐总相宜。对影怜卿瘦,吟罢笑侬痴。 餐佳色,谁送酒,就东篱?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只恐明年秋暮,人在海天何处;沉醉且休辞!试向黄花问,千古几心知。
另外一首是《浪淘沙》(和苣苳子忆旧感事词):
久客倦东游,海外归舟。爱花解语为花留。岂比五陵游侠子,名士风流。 秋水剪双眸,颦笑温柔。花前一醉暂忘忧。多少壮怀无限感,且付歌喉。
顾颉刚觉得言辞“太亲密了”,疑心徐自华“或者便是仲昭吧?或不是仲昭而与她处同一的地位的吧?”徐志摩又将顾颉刚的考据发表于《晨报》,并加“附识”,承认“经颉刚先生提起以后,我倒也有点疑心”。由于《晨报》影响很大,由于徐自华与秋瑾人尽皆知的关系,由于顾颉刚考据癖闻名,加上知情的徐志摩跟着疑心,后人便以为林长民与徐自华真发生过“爱情”,不过是“无疾而终”。他们从徐自华的词作里读出,“虽然很含蓄,不失江南闺秀的矜持,但徐自华柔情蜜意的属向已是昭然若揭。”(见蔡宏伟《听桐阴声唧唧》)
这到底难以坐实的,诗无达诂,靠诗意证故实,总不免见仁见智。顾颉刚所谓亲密之词“偕隐总相宜”云云,如题所示,都是咏物,非关人事。词家情怀自然不能排除的,但并无情爱缠绵。徐自华唱和林长民的长短句还有《剑山人苣苳子为题拙稿感而有作》、《和苣苳子东京万翠楼避暑原韵(二章)》、《秋暮感怀再和留别韵寄苣苳子》。若他俩确是一对恋人,题目就不大会这么明标出来,不像西方或后来的中国新诗人,喜欢作品之前奉上一句献给某某某。
柳亚子称徐自华、徐蕴华姐妹为“浙西两徐”,徐蕴华也有《水调歌头》(和林宗孟词人观菊):
蓦地西风起,簾捲夕阳楼。问花何事晏放,可是为侬留?冷眼严霜威逼,回首群芳偏让,比隐逸高流。容易华年老,莫负一丛秋。 待把酒,拼沈醉,度吟讴。珊珊瘦骨,更将佳色胆瓶收。笑口纵开须惜,只恐秋光轻别,对此暂消愁。但愿明年景,依旧赏清幽。
也有《浪淘沙》(和宗孟词人忆旧感事):
裘马访蓬瀛,仙侣相迎。四弦水调冠新声,省识青蛾堪闭月,恰称香名。
蒿目感苍生,漫赋闲情。请缨破浪待功成,双桨好迎桃叶渡,名士倾城。
词语的亲密不亚乃姐,词牌、题目均雷同,大概作于同时同地,甚至可能出于同一情境。林长民与徐蕴华是诗友,就如徐自华仅是诗友,姐姐充其量是林长民的一位红颜知己。
林长民对徐志摩毫不隐瞒自己往日恋情,真有其事,徐为何说明“他却不曾提起过徐自华女士”。苣冬子、仲昭通信之际,徐当面问过,仲昭究竟是谁?林长民笑而不答。下次再问,林长民才释疑:“事情是有的,但对方却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我当时在难中想着她也是有的,但交情却并没有我信上写的那样深。”徐志摩则说,“我关于‘仲昭’,所知止此”。此处林、徐的话都打了折扣,林的折扣或许是徐代他打的。1923年夏天林长民南来西湖畔,信告徐志摩,欲在杭州租赁房子,拟供伊人之用,“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其交情深浅还用说吗;而此情此事徐志摩一清二楚。徐志摩打个折扣,想必有不便明言的忌讳。其时徐自华仍健在,且近在咫尺,“数千里外”之言,显然又排除了她的恋人身份。林长民是才子,徐自华是才女,两人过从仅在惺惺相惜。至于两人政治识见不尽相同,于袁世凯态度上尤为径庭。
大概是写了这封“情书”,以及他那传诵很广的诗句“万种风情无地着”,朋友们戏称他“恋爱大家”。嘲讽意味很浓的这个外号,不应作通常的误解。后来林长民在北京的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恋爱与婚姻”的精彩演讲,留下两万余字的记录稿,不见一点轻佻猥琐言词。他描摹爱情心态:“那事前的用情,仿佛早起准备去赏花,就是足迹还没有涉到花园已经觉得眼底有了春色,鼻底下有了清香。那事后的用情,仿佛是饮过醇酒,醉里觉得梦境迷离,浑身都有温和舒畅的气象,又仿佛是念过好诗歌,背诵了几百回,越含咏越有味道,有时便忘了诗句,感触了什么情境,胸中更有无限的诗意。这种种用情缠绵婉转处叫做情结,或是断的,或是续的,都算是爱情。”这般秀丽文字,非学究似的伦理学家所能道出。演说更有诸多真知灼见,大胆的,超前的,继承传统的,即使今天读来仍不乏启迪。研究中国近代婚恋观的历史,近一个世纪前的这个文本,不失为足具价值的史料。
◎ 陈学勇,南通大学教授,著有《旧痕新影说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