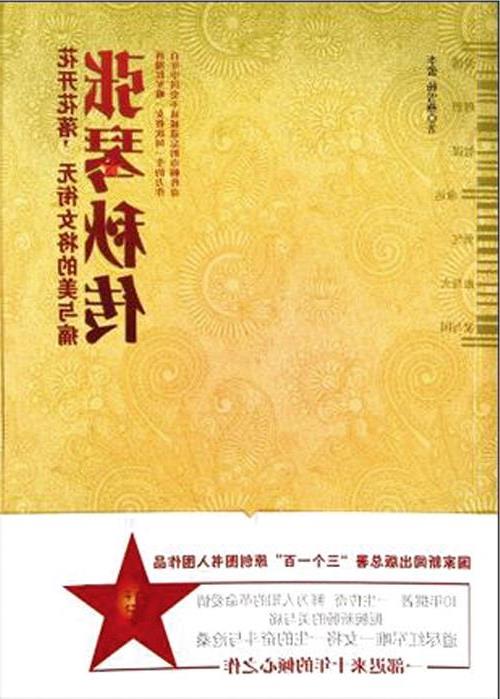张琴秋的后代 49年后的陈昌浩和张琴秋
2、张琴秋组织了新家庭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了突然进攻,陈昌浩一家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做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中的一名重量级人物。
他被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苦力。身在异国,陈昌浩的心依然留在了国内抗日战场上。他不停地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谁也没有给过他只言片语的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
他很快就穿上苏联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3人找回莫斯科,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
陈昌浩立即向苏共中央正式递交申请,要求回国,苏共中央回复说,他回国,必须有中共中央的调令。陈昌浩只得留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
这一期间,他和莫斯科姑娘格兰娜组成的家庭中又增加了最小的儿子祖莫。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
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仿佛当年的革命战友们早巳将他遗忘。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前去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强烈愿望。蔡畅回国后,他望穿双眼,结果依然如故。
(陈昌浩送儿子祖涛由苏归国前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昌浩欣喜若狂。陈祖涛回忆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我陪父亲在高尔基大街上买东西,他高兴啊,那一天特意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戴着礼帽。
还对我说,‘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次我总算可以回去了!’” 他托每一位来莫斯科的老战友给中央带话,希望能尽快回国工作,可是,他的每一次要求,总是渺无音讯。
陈昌浩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1948年,苏联方面又请他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10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这部辞典后来成为在新中国的俄文学习者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部辞典中的经典。
陈祖涛回忆说:“1951年初,我父亲主编的《俄华辞典》终于完成出版了。父亲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大使等中央领导人签上名,送给他们做纪念。
厚厚的一大摞啊,全是我一个人扛到大使馆去的。” 俗话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这一次,北京城里的中南海终于有了回应。 “祖涛,你父亲回国的事,毛主席总算点头了。”1952年4月里的某一天,陈祖涛突然接到莫斯科同班同学、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电话。
“确实吗?”陈祖涛不敢相信。 “我爸爸告诉我的,还会有错?” 陈祖涛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不久,离开祖国13年之久的陈昌浩终于携格兰娜和祖莫踏上了归国的列车。
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让他倍感温暖,对他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来自党中央的信任更宝贵的了。 当年的老搭档徐向前当时担任着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
为欢迎昔日老战友陈昌浩的归来,为人处事从来低调的徐向前破例在自己的寓所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倪志亮、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名在京工作的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他们分别巳经多年的“老首长”。
因为前面有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去前门火车站迎接陈昌浩归来垫着底儿,所以大家也就不存在什么顾虑。
再说,建国初期,万象更新,党内军内的政治风气很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后来那样复杂紧张。 席间,红星闪耀,觥筹交错。这一大批共和国的将军政要,其中还有好些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者的军人们,争相上前与陈昌浩敬酒,欢迎他的归来。
陈昌浩频频举杯,笑答酬酢。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同时也是让陈昌浩强作欢颜,而倍感难堪的一刻。 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4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
短短六七年时光,是他人生最耀眼的巅峰阶段。这巅峰上下洇染着烟火和血色,也给他镌刻下了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早就牢牢地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徐向前寓所宽敞的大客厅里,落魄的陈昌浩也处处显露出落魄之相,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手下的军长、师长,如今共和国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将军政要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当他的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出现在大门前时,他更是既尴尬,又愧疚,赶紧主动迎上前去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
我……我对不起你呀!” 张琴秋却大度地说:“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它了。我真要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也是你过去的老部下,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
” 陈昌浩一声惊叫:“啊,苏院长!” 苏院长就是河南潢川人氏苏井观,他是天津海军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红军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在通江时期,就担任王坪红军总医院院长。
建国后参予了卫生部的创建工作,此时是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与苏井观应当说早就有了缘分,只不过往后推迟了五六个年头。陈昌浩随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病。一晃两三年过去了。
张琴秋一直等待着陈昌浩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可是忽然传来消息,陈昌浩竟然与一个莫斯科姑娘同居了!当张琴秋确认这一消息千真万确后,她果断地向中央写出报告,请求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 张琴秋与陈昌浩离婚后不久,一直暗恋着张琴秋的苏井观,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苏井观此时在陕甘宁边区晋绥5省联防军卫生部工作,他比张琴秋小1岁。张琴秋在4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委员时,苏井观担任总医院院长。这位知识分子也像张琴秋一样多才多艺,不仅医术高明,唱歌演戏打蓝球,样样在行,其性格与张琴秋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当沈泽民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苏井观由对张琴秋的同情很快变成了爱慕。但在面对与自己上级的爱情的时候,平时活泼开郎的苏井观却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一直不敢主动向张琴秋表白,最后眼睁睁看着“花落旁家”。
而这一次,爱情的火花在他心中重新燃起,两人知根知底,原本就有感情基础,很快就相爱了。 1943年春,张琴秋与苏井观幸福地结合了。
婚礼在柳树店五省晋绥联军卫生部苏井观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4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从延安特意赶去向他们表示祝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4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这时苏井观已经38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1岁,都已不再年轻。与张琴秋、苏井观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因在重庆而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他们表示庆贺。
陈昌浩梦寐以求想回国效力,而最初国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表现出来的中兴之气也的确让他无比振奋。可是,几年之后,事情渐渐地变得令他担忧起来。毛泽东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权威巳经坚如磐石,对当初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部下也开始不放心起来。
随着“高饶反党集团”、“萧克、李达、郭天民反党宗派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清洗,再加上军内对刘伯承的批判,以及铺天盖地的“反右”、“反右倾”运动,使身戴罪枷的陈昌浩感到不寒而栗,昔日的老虎自觉地变成了绵羊,过去的锐气荡然无存,他深居简出,谨言慎行。
并且在一些无法回避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公开地、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3、欲行不敢,欲罢不忍 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靠着“三自一包”这一剂灵丹妙药,很快使嗷嗷待哺的中国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 大地回春之际,陈昌浩负责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发行了,组织上给了他一次较长的休假。
不少老同志都劝他回湖北老家看看,还说:“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 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不曾回过老家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了。
1937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英山县,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也仅是通知母亲和刘秀贞把祖涛带到汉口旅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 就在这次休假期间的某一天清晨,陈昌浩出了他在王府井附近的住所红霞公寓,沿街长跑锻炼时,忽然拐进了景山公园。
他知道家住景山后街的张闻天,每天清晨都在景山公园锻炼身体。陈昌浩对于是否回老家探亲,很想听听久经历炼,比自己更加老成持重的张闻天的意见。
时过境迁之后,这一对当初为了不同的政治识见而挺身于风口浪尖,曾经搞得来剑拔弩张的大人物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早已在历史的长河里烟消云散。由于编译工作方面的关系,两人之间过从甚密,近些年为了理论上的探讨,几乎时常见面,恳切交谈。
张闻天如此温良谦恭,谨言慎行,却仍然在庐山会议上闯下了一场塌天之祸,被解除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邃智的脑袋上被扣上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顶黑帽儿。
其夫人刘英和儿子虹生亦受到株连,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可身遭厄运的张闻天却不肯赋闲在家尸位素餐,被罢官后,几经写信申请,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孙冶方手下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特约研究员”。
连续3年大饥荒过后,1962年早春日转清明的政治气候,使他这个“特约研究员”又豁然开朗了许多,钻研政治经济学的劲头较之以往更足了。 张闻天听陈昌浩说明来意,想也未想便说:“好啊,昌浩同志,有张有弛,文武之道嘛。
辛苦了这么些日子,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陈昌浩说:“不少同志都劝我回湖北去一趟,我正犹豫不决呢。” 张闻天不禁摇了下头,抽抽眼镜说:“你当年的那股子刚劲怎么一点也没有了?怎么回国后短短几年工夫就把脾气改了?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陈昌浩吗?” 陈昌浩自嘲地笑笑,说:“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嘛!
”随后才说,离开老家30几年了,他当然想回去看看。可是,武汉地区有不少4方面军老同志,他这脸上烫了金印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见他们;即使回到湖北,人家不好办,他也难为情;再说,那些昔日的老部下假若真地张罗起来,他受人厚爱,今后也无法回报……总而言之,思想上顾虑重重,感到欲行不敢,欲罢又不忍。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张闻天挥挥手,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可顾虑、可犹豫的?犯了错误,你不仍然在努力地为党工作吗?你陈昌浩还是陈昌浩嘛?就像我张闻天,不当官了,还是张闻天嘛!
把你过去的刚劲拿出来,趁这大好春光,赶快回老家走一趟!” 陈昌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昔日的战友与对手,心中汩汩涌腾起一股暖流。 陈昌浩知道,张闻天这几年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比起自己在延安受冷落时的境况更加凄惨,可他却丝毫没有消极遁世的念头,仍然是一副拿得起放得下的坦荡胸怀。
陈昌浩不无感慨地说:“闻天兄,你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在张闻天的鼓励之下,这年5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亲之梦。 令陈昌浩既担心又感动的事情果真发生了。
在武汉军区和武汉市委工作的陈再道、宋侃夫等老部下听说他要回武汉,唏哩哗啦邀来了一大帮原4方面军的老战士聚在一起,欢迎他们昔日首长的归来。 席间,不少人谈到往事,尤其是西路军的遭遇和延安批张运动,虽然语多节制,但一个个声音哽咽,热泪盈眶。
陈昌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既害怕这样的情况会给前来欢迎的老部下们带来麻烦,又深为老部下们表露出来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最后,他站起来,痛心疾首地对大家说道:“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
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我过去对不起毛泽东,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大错。
西路军时打了败仗,我作为主要领导难辞其咎。但党中央毛泽东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提高。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
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很不错的了。
同志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在面对着济济一堂的老部下们讲话的过程中,他曾三次深深鞠躬,以表疚愧之情。 当事人言之恳切,耳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而一些含冤负屈、牢骚满腹的老战士,同样被感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在汉期间,宋侃夫特意派车把陈昌浩的结发夫人刘秀贞接到翠柳宾馆,让这一对离散多年的夫妻见了一面。 过去的夫妻,如今成了革命同志,让陈昌浩好生感叹。 面对刘秀贞,他满怀内疚而又不无感激地说:“秀贞,我这次能在武汉和你相会,多亏了张闻天同志,还有宋侃夫……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很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