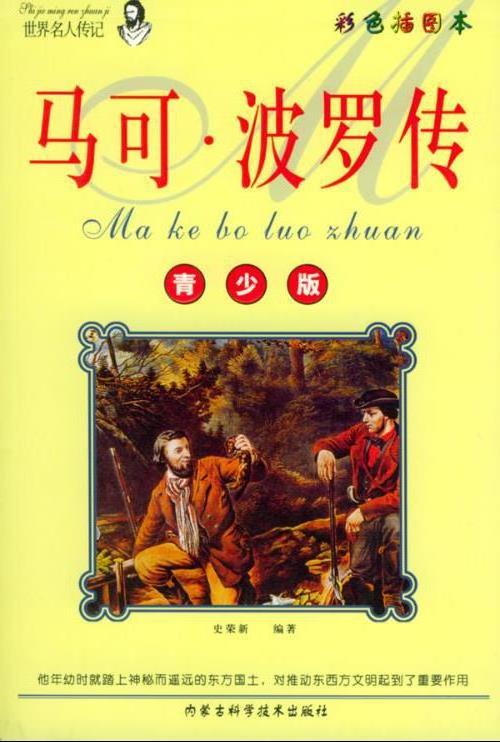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下)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 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 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 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 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
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 〕。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
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
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
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
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
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
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
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
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
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
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
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
”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
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科学院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
《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
《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
2.余士雄:《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988年7
3.王苗、石宝琇等:《追踪一页历史——重走马可·孛罗进入中国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6开本,116页。这是一部图文并茂、以彩图为主的书。1991年,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记者们想
四、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的同人们完成他们的追踪任务到达终点站北京时,正值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劳动人民宫隆重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
他们躬逢其盛,欣然参加。
会议由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到会的有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扬州、泉州、厦门、大连、成都、新疆等地学者50余人。意大利学者人数最多,近20名,多为大学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马可波罗的后裔波罗·帕多莱基亚教授,长相颇似《游记》中的马可画像,还有热心中意友好事业、被称为“小马可波罗”的记者、作家威尼斯人马达罗。前者以其祖先曾亲临中国的业绩感到自豪,并表达了对中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的向往,愿继承发扬其祖先所开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谊。
后者做了一个题目很长的报告:《百万:关于人类友谊和团结的一个特殊事例如何导致一个关于普通贪婪的事例》。《百万》是《游记》的名称之一。全文大意是,马可波罗怀着友好、真诚和尊崇的心情写出了一个伟大、勤劳、文化发达、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纪后却引起了殖义者的贪欲,他们为了寻求黄金,征服、破坏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玛雅和阿兹台克两个王国。他说:“历史是‘若干事例’的奇异综合,每个事例对其他事例是独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严格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马可波罗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样的。”这一辩证的看法很有见地,虽然他并未对《游记》作任何考证和阐发。
其他意大利学者的论文有《马可波罗访华后中国和东方对意大利的影响》、《马可波罗和中国》、《马可波罗时代在华的意大利人》等。
中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
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 〔6〕参见《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原刊于《南开学报》1982 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原刊于《环球》1982年第10期, 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论》及《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
〔7〕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第二节是对王文的答辩;第一节是对西方怀疑论者的概括性评论,要点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见于中国记载;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诸人的书中也多未提及;说马可书抄自波斯的《导游手册》,但未举出何处抄自《手册》,论者并未见到《手册》,只是揣测之辞。
--博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