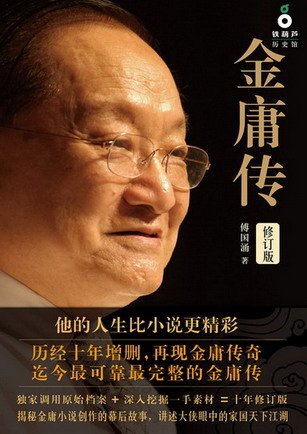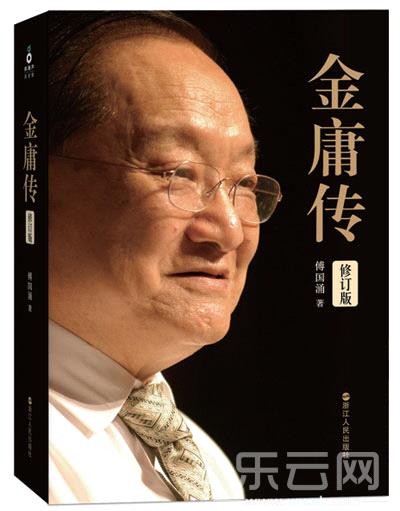傅国涌的文章 傅国涌:一个民族最有尊严的部分 就在国文老师身上体现出来
语言和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两大创造,而语文教师手里拿着语言的金钥匙。
准确地说,“语文”应该叫母语。从晚清到民国,“语文”先是叫国文,后来变成了国语,今天叫语文。但无论叫什么,都是教母语,其实就是一个母语课。语文教师这个职业,本来是一个庄严、神圣的职业,在过去的中国,事实上也非常神圣;如果说今天不再神圣了,是因为母语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知识点,被碎片化了。这是语文今天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碎片化。
第二个问题,我称之为狭隘化。语文原来是非常丰富的,它指向真善美三个维度,但是我们今天往往把语文狭隘化为文学,更多的时候只是把语文当作审美的,而忘记了它同时指向人类不同的精神侧面。
今天,无论是在我们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还是在我们课堂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语文,都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语文,都不是它本质的属性,都不是它应该有的那一个面目。所以手中拿着母语金钥匙的语文教师,在今天中国的地位,也远没有过去那样高,他们被限制在课堂,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教学范围里面,而不再被赋予承担更重要的文化的功能。
前些年,我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血色湘西》,其中有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湘西那个地方,每年端午节都要祭屈原,那么谁有资格出来念这个祭文?不是掌权的,不是带兵的,不是有钱的,权钱势在这个时候是派不上用场的。
能念这个祭文的,是当地最有影响的国文老师。这篇祭文要由他来念,这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尊严。语文,或者说母语、语言,本质上要体现尊严。它最内核的东西,是它的尊严。若是没有了尊严,这个语言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和价值。
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最有尊严的部分,就在国文老师身上体现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最后一课》,理解一个民族不再有机会学习自己母语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沮丧、失落、痛苦、忧伤。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把母语看得至高无上,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选入《古文观止》的那些文章,几乎已成为中国的象征、文化的代言,历代的读书人都要向这些文字致敬。
这表明语言本身即具有超越性,它能穿透时间,而帝王的权力只能管一个时代。但今天语言已经被降低到一个工具性的角色,不再承担什么文化使命了。
当一个时代把语言的功能缩小、窄化为审美的一个维度时,我们已经把指向思想、指向其他精神维度的东西给忽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流文化当中,流行的文体是“《读者》体”,尤其在高考作文当中,《读者》的文体成为被认可的首选文体。
“《读者》体”是什么?我称之为“伪抒情”的文体,它带有一点小感触,一点小议论,一点小哲理,也就是“于丹体”。这个时代,语文的败化在文体中的表现,就是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励志的、矫情的、伪抒情的文体大为流行,里面是空的,外面用一种空洞的词汇包装起来,其实从里到外都是空的,传递着一种伪道理、伪伦理,都是伪的。其本质就是一个轻飘飘的假大空的东西。
但是,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处境下,人还是可以有自己作为的。我想起一个画面,如果大家看过《围城》的电视连续剧,钱锺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就是在这里拍的,这条长长的走廊,是民国早年的一个学校建筑,就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里面,今天保存完好,已经成了文物。
当年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朱光潜曾经在这里教书,他有过一番美好的回忆。当年,朱光潜与丰子恺、夏丏尊、刘薰宇、朱自清等人,都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儿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
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这段回忆,呈现了他们在春晖的课余生活,那是怎样一种放松、自足的状态,他们聚在一起喝一点黄酒,或一杯清茶,一起聊天,就在这样的聊天当中,他们的作品都出来了。
朱光潜在这里写出了一生中最早的美学论文,夏丏尊在这里开始翻译那本《爱的教育》,朱自清在这里写出了一些散文,他们都在这里开始了新的人生。
特别是丰子恺,他画出了他一生中最早的漫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幅“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人散后”的意境,几乎就是这帮老师在一起聊天之后的场景。当然他有艺术的想象,他们的房子都是湖边的小平房,还没有他漫画中那么好。
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学老师,他们可以在这样一种放松的状态下,展开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这是一个能给人尊严的环境,能给人自信的环境,能给人可能性的环境。
也是在那个时代,包括丰子恺在内的那一帮人,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丰子恺的漫画中有许多对教育的批判,大剪刀像剪冬青一样将人剪成一样的高低,用一个模子铸造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可以用那样的方式,直言不讳地表达他们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里他们的尊严和自信。那个时代的社会空间给他们提供了可以自由地批判、想象、写作,自由地创造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能生可能,就像苹果树上结苹果一样,你不能在苹果树上结出个西瓜来。
回到语言。已故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在1988年底,处于困境当中时如此说:“言语是万物之始,言语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所以我把语言看作是人类的一个重大创造,它的重要性,甚至在制度之前。
电影《一九四二》中有一句台词,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蒋介石问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次河南旱灾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的回答是: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实际上死了大约三百万人。面对政府统计与实际死亡人数的落差,这个时候语言还有它的尊严吗?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语言仍然是万物之始。
《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创造世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不是“做”,而是“说”。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是“说”出来的。我曾经说人类有一个嘴巴,嘴巴有两大功能,中国人只用了一个功能,叫“民以食为天”,一个曾经历饥荒的民族,会强调吃的功能;但是在西方国家,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他们强调的是“民以说为天”。所以说言语是万物之始,也是从《圣经》里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哈维尔继续说:“言词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宇宙生命形态的本质。精神、人的心灵、自我意识、概念思维及归纳的能力、了解世界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我们的处所的能力、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亡以及在这种认知下继续活下去的能力——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以言词为介质,甚或是由言词所创造出来的吗?”
这段话可能有点抽象,他常常用一种非常绕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但是他一直都是围绕着语言这个轴心展开的。他是一个剧作家,后来成了总统,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剧作家,所以他想问题,都是从语言出发,他把语言看得非常重要。
中国也有一位知识分子在一篇文章《从自由出发》中讲道:“在揭示一个人的人格时,语词可以是最弱的证据,也可以是最强的证据。它是最弱的,因为说假话、说大话是那么的容易;它是最强的,因为在某种特定的境遇下,一个人说什么、如何说、多说几句还是少说几句,当下就全部决定了他全部的命运。此时此地,语词即其人。”
说什么不说什么,多说什么少说什么,就是你全部的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语言的力量是最强大、最重要、最关键的,在特定的境遇下,它可以决定你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