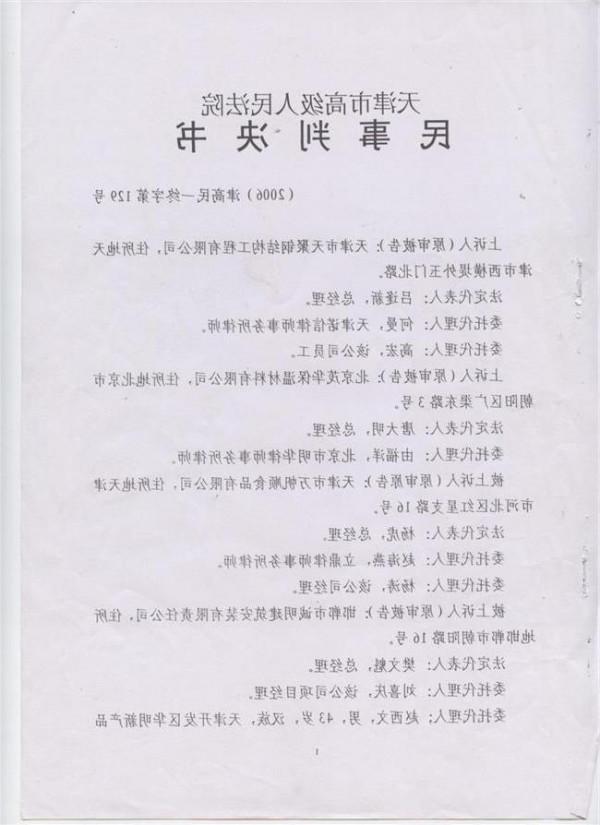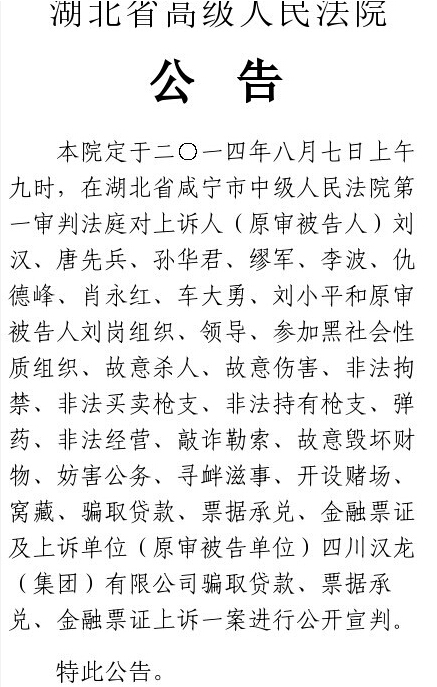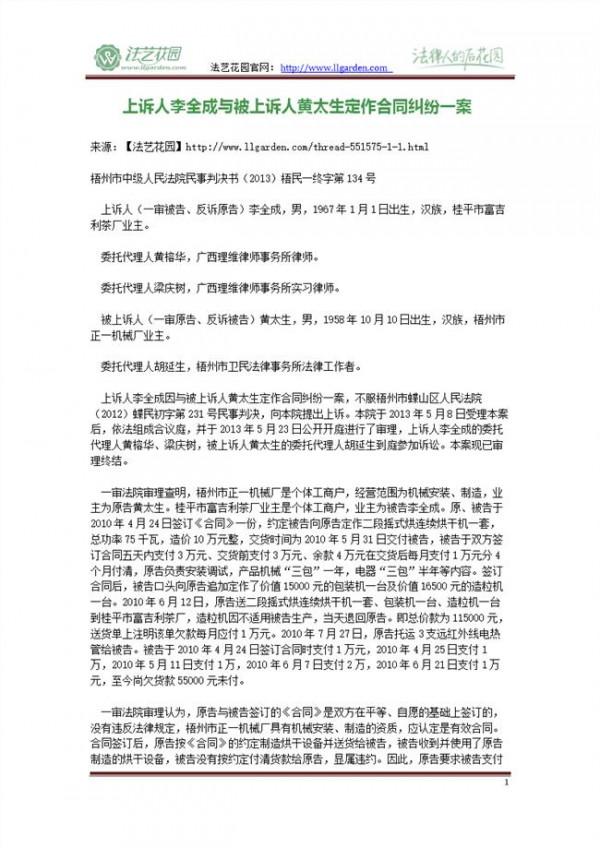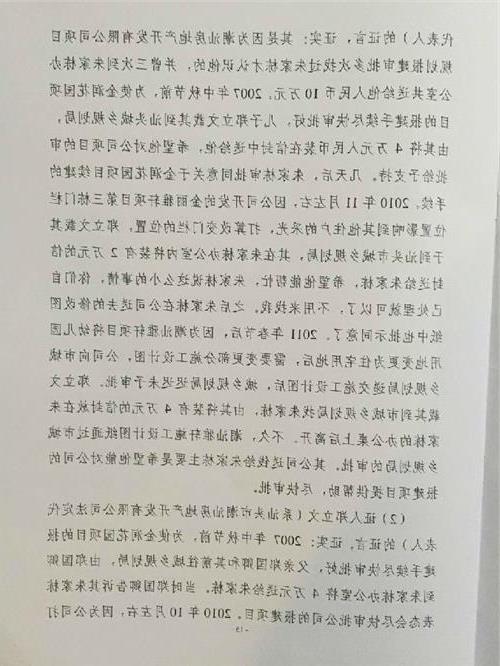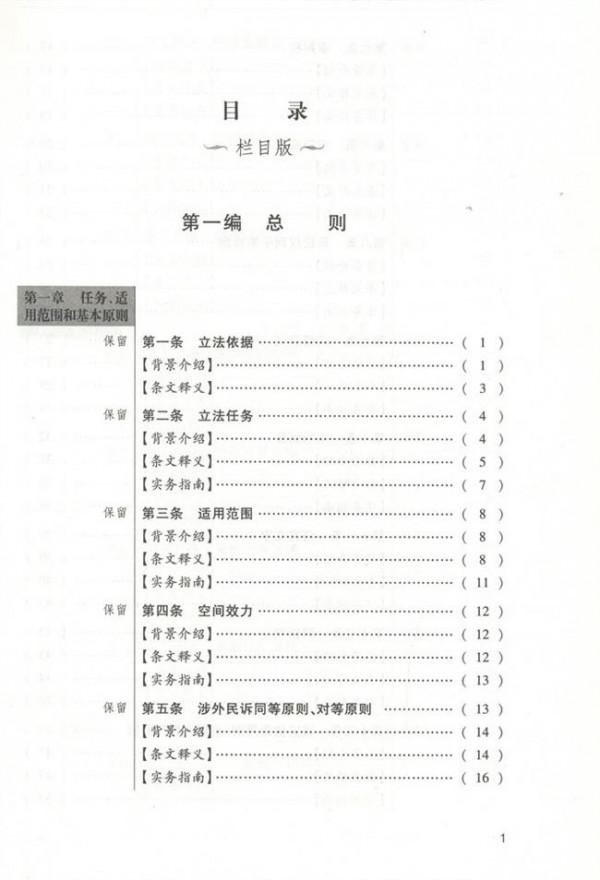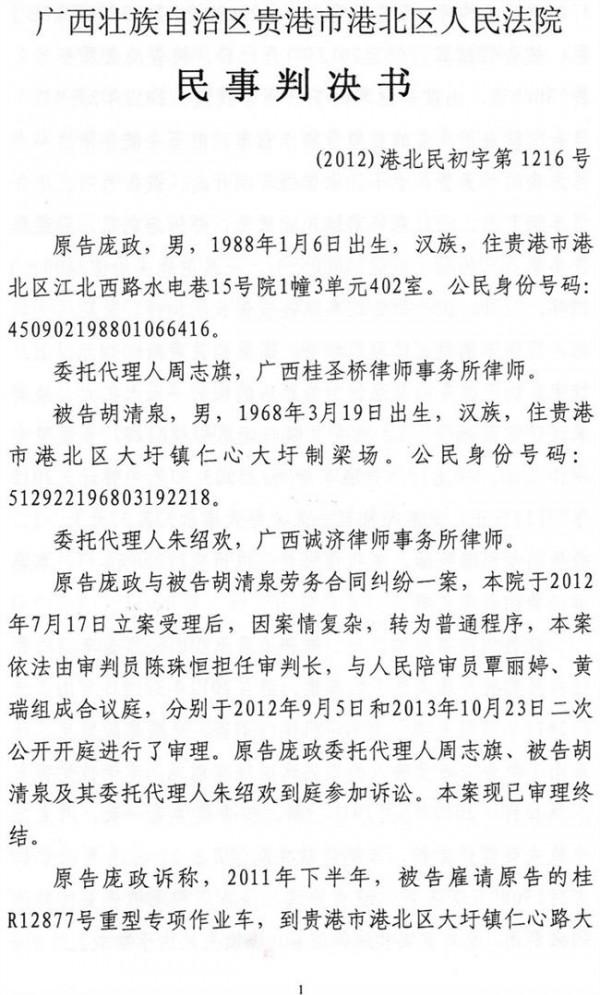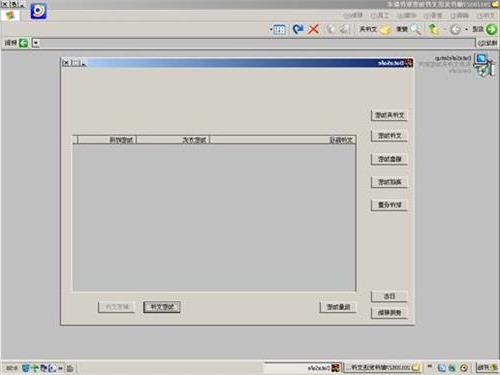田文昌刘涌 因刘涌案受质疑 律师田文昌谈专家论证书的是非
互联网上正流传一篇名为《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的文章,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列为四大腐败帮凶之首。在代理刘涌案之后,没有哪个律师像田文昌这样引起中国公众这样大的争议
本刊记者/韩福东
田文昌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在早年的公众记忆中,他更多是站在弱者这一边,如代理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等。而近年,他的当事人却多是位高权重的官员,或身家亿万的老板,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福布斯富豪杨斌和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等。
没有任何一件案子使田文昌受到刘涌案这样的质疑。刘涌案从死刑-死缓-死刑的一波三折,也让田文昌在舆论的赞赏和质疑之间跌宕起伏,在“正义的卫道者”与“邪恶的帮凶”两种角色间转换。而在最高法院提审刘涌案之时,人们注意到,一审和二审中刘涌的代理人田文昌,并没有出现在辩护席上。一时间,对田及其命运的议论和猜测就更多了。
2月1日下午,田文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坏人也有接受辩护的权利
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你以前是平民律师代表,专门宣扬正义,现在则专门为贪官、不法资本家、黑社会头目辩护,觉得你的形象变了。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田文昌: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律师角色定位的误解。“坏人”也有接受辩护的权利,律师只要依法辩护,就是正义的,是通过司法公正来维护正义。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律师都只为弱势群体辩护,也不能要求一个律师只接一种类型的案子。即便贪官、黑社会分子也有自己的权益需要维护,不能随意处置。
律师的参与本身就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维护。律师的职责就是依照法律最大化的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很多人其实对我个人也不了解。10年前我的确代理了一些针对强权者如禹作敏的大案,但并不仅仅是这些,我也为一些“坏人”做过辩护。现在,我不仅仅为杨斌、刘涌辩护,我也代理弱势者的案子。
新闻周刊:每年找到你的案子大概有1000个,你能接多少?接案标准是什么?
田文昌:我现在一年也就接二三十个案子。找上我的案子没有小事,工作量太大。
我接案时比较注重的,一是案子要比较典型,目前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都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案子是疑难杂症,比如在证据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有分歧,有一定难度,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一定的价值。我从学者的角度考虑多一些,很简单的案子,我一般不接。
另一方面,从本意上,我愿意接那种确有冤情的案子。其实,对一些非常敏感的案子,并不愿意接,虽然接过一些,但实际上推掉的更多。
新闻周刊:收入多少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标准吗?
田文昌:我接的案子刑事和经济纠纷的民事案各占一半。从收入上,肯定经济案子多,我若光办刑事案子,连这个律师事务所都养不活。有人说我办一件刑事案子收上百万甚至千万。我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传出来的,反正我是没见过。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
其实这些敏感案子我真的不想接,他们都是通过有关部门、通过熟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一而再,再而三;我偶尔接几个。在收费角度,我没那么多考虑。但我不会因为收钱少,我就不负责任。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认真了,所以惹了一些麻烦。
专家论证书的是与非
新闻周刊:在办理案件中,你时常邀请法学专家论证,出具了对你的当事人有利的专家论证书。这一点在学界和民间都引起很大的争论。
田文昌:这种争论是有一定误区的。人们(包括我)最反对的是行政干预司法,但是专家的法律意见书却与行政干预不同。首先,专家的法律意见书代表的是一种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权力,不可能产生干预的作用。其次,因为我们国家的司法环境、司法人员素质以及立法水平都不尽如人意,这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我们在具体的案件上,会产生一些歧义。请专家论证只是在理论上寻求一种参考。
我在十几年前就搞过专家论证书,到现在已采用了很多次。最初采用专家论证书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代理承德一个企业家的案子,之所以请专家论证,一来这个人比较冤,二来案情也确实比较复杂。当初这个企业家曾被四罪并罚判了18年,官司打了三年,最后他被判无罪。
凡是遇到有难度的案子,我们律师事务所内部就有讨论制度,如果内部讨论之后还觉得有难度,我们就请专家论证。这其实是针对疑难问题向专家请教,这也是对案件负责的一种表现。
新闻周刊:向专家请教后的结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律师手里,而是递交到了法院,法院又有很多人是这些专家的学生,因此有人认为这实际上会对法官的独立审判产生影响。
田文昌:这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这么扩展起来的话,学生、老乡、同学等都会干预司法独立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专家本身没有那么高的地位。这和行政权力不一样,如果行政机关的意见递交到法院,肯定要受到质疑,专家意见书只是用来说明我们辩护的理论根据,供法院参考,不会对法院产生任何约束力。司法机关有时也请专家论证,也是作为一种参考。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会根据专家意见作判决的。
新闻周刊:有人说,律师提供给专家的材料都是对他的当事人有利的,专家在短时间内听了一面之词,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田文昌:在请专家论证的时候,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都交给他们了,包括公诉方用以支撑起诉的材料。在法律意见书上,都列明了专家做出这种法律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材料的目录。这表明专家意见只对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负责。这一点我们的做法是很严谨的。
专家的论证意见有两种体例,一般来说,在专家意见一致的情形下,出具的是专家论证意见书,如果专家的意见不尽相同,则出具论证会纪要书,把各种观点都客观地反映出来。
新闻周刊:如果专家论证意见书有对你的当事人不利的观点,你会怎么办,会交给法院么?将不利于当事人的观点递交法院,是否有违律师的职业道德?
田文昌:这要看具体情况,有时论证中专家会提出一些探讨性的不同观点,我们也可以交给法官参考,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参考。如果专家一致认为当事人有罪或某些问题不能成为辩护理由而律师也赞同这种意见,我们会向当事人明确观点,告诉他们有哪些问题是不能成为辩护理由的。这样做既能保证我们辩护的质量,对当事人也是一种交待。而对于一些证据和法律关系很清楚的案件,也不会请教专家去论证。
我没有寻求过案外干预
新闻周刊:律师拥有权力机关的人脉资源,对律师是否意义重大?在司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的情境下,这种资源对律师办案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田文昌:的确有帮助,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大声疾呼反对的。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新闻周刊:有消息说,在办理刘涌案的过程中,你给辽宁省委、省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审理刘涌案。这种希望通过党委、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审判的行为,你觉得这样做适当吗?
田文昌:刘涌案我都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向上级司法机关逐级反映情况并未超越程序,恰恰是律师的权利。我并没有通过私人关系去寻找个别领导人的案外干预,更没有权钱交易。
新闻周刊:有的律师在办理案子的过程中,为给当事人争取一个正当的权益,而利用自己在权力机关的人脉资源,也就是通过人治的手段解决了法律问题。作为一个律师,你对此有何看法?
田文昌: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从理论上来讲,这是违背司法原则的,我不赞同这样做。但实践中,有的人如果确实为了追求一个公正的结局而不得不采取了这种方式,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这正是我曾经谈到过的“怪圈”问题,也正是我们应当努力消除的现象。
在中国做律师很难,明明这是个冤案,通过各种方法纠正过来了,能说他做错了么?也是不得已。但如果是利用权力机关的人脉资源颠倒黑白,循私枉法,那就非常可恨。这种做法我是深恶痛绝的。
律师的角色定位
新闻周刊:律师的职责道德要求他争取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可是,在为当事人服务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职业伦理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田文昌:事实上,职业道德与公共利益在形式上有时会有冲突,但在总体上却并不冲突,这要看从什么样的高度上来分析。
新闻周刊:你是说,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冲突?
田文昌:关键是怎么理解这个冲突。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电视剧塑造了一个正面律师的形象。剧情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儿子品德非常差,拒绝抚养他的父亲,父亲就将他告上法庭。后来法庭判决这个儿子败诉。当时这个儿子就在庭上训斥他的律师:白给你那么多钱,你还让官司打输了!当时这个律师非常潇洒地说:我根本就没想让你赢。说着从西服兜里掏出一沓钱,还给了他的当事人。
电视剧在歌颂这个律师,但这种宣传是非常负面的。从道德上讲,这个律师的当事人的确需要谴责。但法律上,这个“逆子”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对他的判决也应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能凭道德义愤而为。如果不经过审判,也没有人为他代理,凭什么标准去评价他的行为呢?能否说律师为这种人代理尽职尽责就违反了公共利益或社会道德呢?
事实上,更多的案子并非那么是非分明,每个人的道德观念也是有区别的,所以才需要法律评价,需要法院判决。国家之所以设立律师制度,正是通过以对抗与制约求公正的方式来实现司法公正,也正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充分尽职尽责,恰恰是其依据职能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
田文昌:生于1947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起从事律师工作,1995年创建京都律师事务所,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现为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