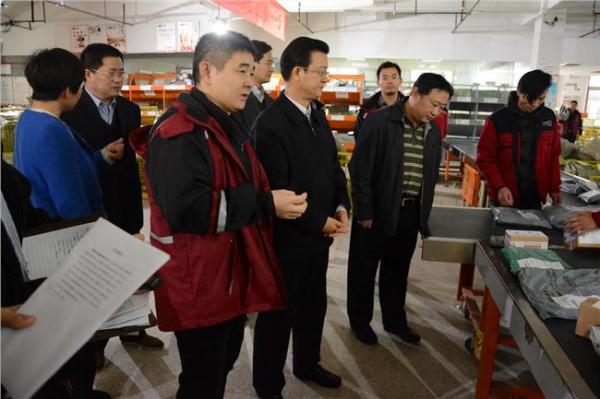杨洪基多大年龄 专访杨洪基:最大愿望是继续为部队多唱几年
新华军事:杨老师听说您的声乐知识当时都是自学的,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能跟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吗?
杨洪基:我是1959年4月参加工作,当时是在大连歌舞团待了三年时间,一直是靠自学,把一个声乐大学本科生至少需要五年学习的知识学完。
当时学了以后没觉得就能用上,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三年的自学对我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唱了很多著名的歌剧,这些是我一个没上过大学、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如果不下这些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
还有就是声乐,60年代初的时候正好有一电影叫《新人在歌唱》,是前苏联一个男高音歌唱家演唱的,男高音唱的棒极了,当时我们非常羡慕,每天学习模仿。我们的团长见到我就说你们挺用功,但成天自己光练不行啊,得有老师教,我给你找几个老师教。之后团长经过多方打听从上海请了一个叫李梦熊的老师来培养我,我跟他学习了一年半。
现在我除了实践、在舞台上的锻炼之外,最基本的东西,我的发声方法都是在这三年打下来的基础。
我觉得人应该懂得感恩,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团长,他是个作曲家,还有就是那个声乐老师,当时真的是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教的。现在我唱歌很多人还很不相信,说怎么你就学了一年半,怎么唱的这么准确,而且声音这么浑厚,音乐学院五年才能教出一个学生来,还不一定能唱的好。
新华军事:杨老师你的歌唱事业有什么遗憾吗?
杨洪基:我第一个遗憾就是没上大学,没文凭。第二个遗憾就是一些应该感恩应该报答的人我没能去报答他们。
比如说我在大连歌剧团时的团长,他在八十年代就去世了。他去世时我正下部队演出,当时一去就是四、五个月,那会儿也不像现在,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的通讯联系。从部队回来之后,过段时间之后我说回家去探亲去,一到了大连,我说去看看我的团长去,我的同事就说他已经去世了。我说怎么不告诉我呢?他们就说怎么跟你联系啊,写信你那也没人接,也没人回信。当时我根本不在北京,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其次就是我的声乐老师,他生活在上海,我每年只要到上海我都会去看他。我记得2002年国庆前夕,上海开一个国庆音乐会。音乐会完我就去看我的老师,结果一看老师躺在床上了,李老师一辈子没结婚,住在一个小鸽子楼里。他就躺在床上,我看了就说,李先生你怎么了?他说,前阵子我住院了,街道把我送到医院住,我不愿意住在医院,就回来了。我当时感觉老师的病挺严重的,那会因为我马上得回北京要去台湾演出,我给他留了2000块钱,给他买了个电视机,他电视机坏了。我说从台湾回来了我还来看你。结果等我从台湾回来之后接到一封信说我的老师已经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每次去看老师都会给他几百块钱,一千块钱。如果是现在的话,条件好了,能更好的去报答他们。
还有一个就是对我的母亲。我母亲是92年去世,那天正好请了假回家,买了我母亲爱吃的水蜜桃、奶油点心。我坐晚上的火车,早上到锦州,我母亲跟我哥哥住,我侄子去车站接我时脸色不好,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等一到我哥家,一进门我哥就说咱妈半个小时前去世了,没赶上。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给我母亲争了一口气,是她教育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做坏事,多为别人着想。我觉得我没有辜负她。我这辈子没有害过人,我觉得这点我对得起我母亲的。
新华军事:那您在大连歌剧团的演艺事业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
杨洪基:到了1962年,突然宣布大连歌剧团解散了,当时我就没主意了。跟我们团长说,解散了之后我上哪去啊,是不是还回大连歌剧队去?团长说,你别回大连去了,你的条件非常的好,留在大连可惜了,你得到北京去。我说我不认识北京的人啊。团长说,别着急,我给你联系。
他当时就给总政歌剧团发了一个电报,当时就是说我们歌剧团要解散了,这有个人才,你们赶紧派人来听、来看,假如说让别的单位调走了,你们再来就晚了。电报发了没两天,总政就来了一个导演,崔永昌,他是《柯山红日》中扮演杨坦穗,当时就拍板,就定了要。当时是十月份,差不多调令十二月份就到了。
1962年12月份我就去北京了,也没拿什么行李,当时我是第一次离开家,也想来到部队这个集体,但心里也没底,适应不适应的也不知道。但是等真到部队了之后,很快我就体会到这个集体的温暖了,当时我在四分队,男中音分队。我的分队长跟我结成一帮一,每天晚上来我宿舍问有什么能帮上的。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到非常的温暖。
新华军事: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下部队是什么感觉吗?
杨洪基:1963年我第一次下部队去新疆部队去慰问,我们的战士非常可爱,感觉一下子就跟战士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战士们非常朴实,他们刚从四千多米的昆仑山上下来,脚冻伤了手冻伤了,有的受伤的在医院里躺着,看着心很疼。
我就问那些小战士,在前线打仗苦不苦?战士们说,苦是苦,但是真没时间想这些,前面见了敌人什么苦不苦的就都忘了。说的真是让我感觉我们的战士真是太可爱了。
那次下部队是三个半月,从南疆走到北疆,坐着卡车,自己带着行李。感觉部队的生活很温暖,同志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好,这些战士非常可爱。
新华军事:听说您下部队有个专门的工具箱,跟我们分享一下工具箱的故事吧。
杨洪基:第一次下部队我就看到战士们的头发理的非常糟糕,一块一块像“梯田”一样,我就问他们,这头发是怎么弄的。一个战士就说,都是大家相互理的,也不会理,就拿着推子推,之后就这样了。
从部队回来之后我跟谁都没说,自己去市场买了套推子,想着再下部队能给战士们理理发,虽然不能经常理吧,但想尽量能给战士们多做点事。买回来之后就拿我们的同志做实验,有几个同志配合得还不错,可是手动推子没掌握技巧也理了几个“梯田”出来。练了几次之后觉得还可以,也拿的出手了,第二次下部队之后就拿着推子去给战士们理理发。这一理就是24年。
这个也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战士这么可爱,我就想怎么才能多为战士们做一点事情。
新华军事:那您下部队这么多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杨洪基:在保卫南疆的战斗中,我们到老山去的前线最近的地方是离边境两公里处,这时候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偶尔还能听到枪声。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天晚上我们给一个突击小分队演出,当时跟我们讲就是这个小分队连夜就要派出去,我们为他们唱几首歌送行。当时唱完歌我要了杯酒,给战士们送行。
当时是30多个人,我给他们敬酒,这些小伙子们非常乐观,他们说,没事,等回来再敬。
第二天我们就撤离了,后来我就很关心,就问怎么样了,回话是30多个人,就回来了14个人。每次说到这里我都会很难过,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小伙子。
从那以后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些部队的战士啊真的是非常可爱,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兵,有时候到前线去人家还跟我们说,这里很危险,你们去了之后流弹也可能砸到你,怕不怕啊。但实际上我们真是没什么危险,战士们对我们保护的非常好,都是选择最安全的地方让我们去的。可是我们的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很多同志却牺牲了。
我们文艺兵的唱歌对他们就是很小很小的奉献,我们做的这点奉献真的是算不上什么。
在1979年的时候,我下部队去珍宝岛慰问。在珍宝岛晚上给战士慰问,当时觉得非常好玩,有树有山,在树丛里面建营房。
但是晚上灯光一打开,蚊子蛾子满天飞。在那我是第一次尝到蚊子的滋味,当时正唱歌,一个蚊子就飞进我嘴里去了。我也不能停下了,蚊子不知不觉就吞下去了,回头想想觉得恶心。但是又一想我们只是在那待一天,蚊子蛾子往脸上扑,而我们的战士们常年累月在那里,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后退。当时感觉给战士们唱歌真是非常幸福。
新华军事:杨老师听说您今年71岁高龄又跟随团里去下部队演出了,跟大家说说您这次下部队演出的感想好吗?
杨洪基:今年我们去福建演出,这么多年福建我去过很多次了,最早去还是1971年。
现在我在台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希望还能有机会再为你们唱歌。
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迟早要退休的,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退休前多给战士们唱唱歌。我们的战士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不管多累,在下面热火朝天的看演出,我们在台上表演也非常振奋。
我们团的同志也是非常可爱,他们中很多同志都是为歌唱事业奉献了终生。现在有些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很多也退休了,很多都不在舞台上了。
我就感觉这些年轻的老的同志都非常可爱。我们下部队演出,有时候白天演出了四五场之后,晚上去吃夜宵炊事班的同志们还没看演出呢,就再给炊事班的战士们再演一场。我真是觉得我们团里的同志们非常可爱,也挺心疼他们,嗓子这么唱也是受不了的。我问他们能不能坚持到底,真的是没有说不行的。
新华军事:杨老师最后一个问题问您,您去年被评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您这么多年为兵服务,那您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杨洪基:其实我真的觉得给的荣誉太高了,我只是踏踏实实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的都是很平凡的事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事迹。我自己对我的评价就是踏踏实实做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最主要的事。
我今年七十一岁,现在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一个好的身体,能够继续为部队多唱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