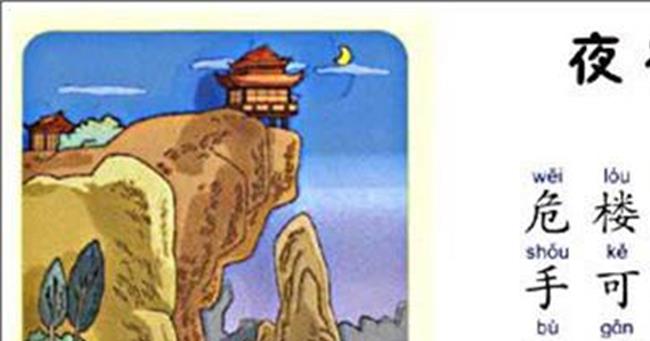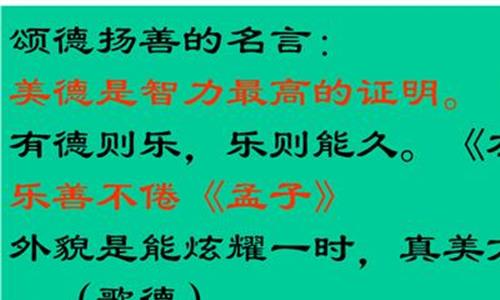杨炼大海停止之处 杨炼:从大海停止之处开始
长发,黑皮裤,和带着自信微笑的脸。杨炼给我的印象,就是浪迹天涯的行吟诗人。
这位八十年代著名的“今天派”诗人,自1988年出国以来,游历二十多个国家,不停地写诗、朗诵、演讲、教书。去年,收录他近年新作的诗文集《幸福鬼魂手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几年前出版的两部作品集《大海停止之处》和《鬼话·智力的空间》也于不久前再版。春节前夕,记者见到了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的杨炼。
记者:九叶诗人王辛笛先生最近去世了。他们那一代和你们这一代被冠以“朦胧派”之名的诗人,代表了两个时代的新诗高潮。你觉得你们这两代之间,有没有渊源?
杨炼:其实是很有渊源的,但是,这种渊源需要我们用时间来发现。辛笛、穆旦他们那一代诗人很早就自觉地探索新诗的语言、形式,并写出了非常成熟的新诗。而我们在“文革”的经历之后面对的是历史、文化、语言的废墟。我们试图返回纯净的中文,透过诗歌的意象反思传统,反思自己在“文革”的经历和历史的怪圈。这,也直接涉及到对语言的思考。
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社会关怀是不够的,今天回头来看,八十年代的大部分诗歌,语言意识简单、感情层次幼稚,很多经不起重读。我自己在经过多年的海外漂泊后,越来越觉得回归几千年来的中文传统,重建诗人独创性与传统之间联系的必要。
记者:在海外漂泊这些年对你有什么影响?
杨炼:我出国其实很偶然。1988年我和妻子接受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邀请,到澳大利亚,然后去了新西兰。1989年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住在国外的时间似乎会很漫长,最初可以说是非常的担忧,也可以说非常的恐惧。
因为我对身处在绝对陌生的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中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记得1990年,中国留在海外的作家在瑞典第一次聚会。刘索拉在台上演唱,她把北京的一句大白话“什么人哪”,用她的那种音乐方式重新处理……我坐在那个小剧场里,感受特别强烈。
原因在于,在海外那样一种处境下,突然听到这么一个词儿,而且我们当时的处境完全可以用这个词儿来代替,确实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时作为“中国作家”好像结束了,作为是否是“在海外的作家”还是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地理上的悬挂或悬置所致,而是文学和思想上的一种悬置。所以那种处境对我来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感受是深刻的,也因此构成后来写作的一种基调或基础。
记者:找到这种基调或者基础,我想你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
杨炼:是的。1993年的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在我的写作上占有重要意义。那一年顾城自杀,我不久前在纽约写了《黑暗们》。回国之梦越来越渺茫,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见尽头。在西方这片陌生的土地,没有语言的环境,到底能否走下去?能走多远?前途茫茫。
那真是我在国外最黑暗的时期。可是,也许就像佛家说的当头棒喝,绝处逢生,到了非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那个从不可能开始的开始,才是真的开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澳大利亚悉尼城外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涛声自脚下传来。
岩石的尽头,正像日子,“尽头本身又是无尽的”。流亡者的“无根”生涯,在冥冥中让我盯视着自己出海——自己在自己之内出海。于是诗的最后一行“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就来了。这首诗,给我漂泊的困惑一个确认: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我终于找到那个人生的形式。
去年8月我参加约旦国际诗歌节,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有一次对话,我就说到,远离中国使我更深地理解了中国,以及中文。是这些年对英文的了解,让我在比较中意识到中文的特性,它独特的局限和可能,这不仅有助于我新的创作,甚至使我理解了以前的作品。
记者:那么,你对中文的特性,到底有怎样理解的呢?
杨炼:在语言的层次里,我一直反复强调中文性。中文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是它跟欧洲语言最大的区别。语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载体。中文语言的非时间性,和中国历史的循环感之间,到底有没有某种必然的关联?谁为因谁为果?都是我们写作中必须思考的东西。
我希望有意识地使用这种非时间性,去表达处境和命运的不变这样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没有中文的这种特性,我就几乎无法表达那样的诗意。当代世界的多元化和多角度赋予了我们绝对国际化的状态。我们只有通过中西文化、语言的比较,通过多角度观察,赋予中文新诗以新的要求和生命。
记者:这是不是你的使命?
杨炼(笑):我不使用“使命”这个词。但其实是有的。中文的传统延续了这么长时间,到现代突然转型。当代中文诗,一开始就面临绝境:不仅是外在条件的贫瘠,更在内部人为的空白——切断文化传承的有机联系,标榜反文化的“文化革命”。
语言、传统、诗歌的历史感和形式感所包含的评价标准,都曾被割裂。这就要求我们探索,将新诗在中文之内的可能性挖掘到极致。我自己最近反复强调,要重建从楚辞、汉赋、骈文、律诗传承下来的我称之为中国文学形式主义的传统。
如果把你所说的使命扩展到中文之外呢?这种转型的探索,对于其他文化也是有极大启发性的。以前俄罗斯一家文学杂志记者采访我,他说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回归普希金。我说到对语言再发现的可能性,他们都非常兴奋。我在阿拉伯,情况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产生的意义,其实是远远超出中文之内的。(彭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