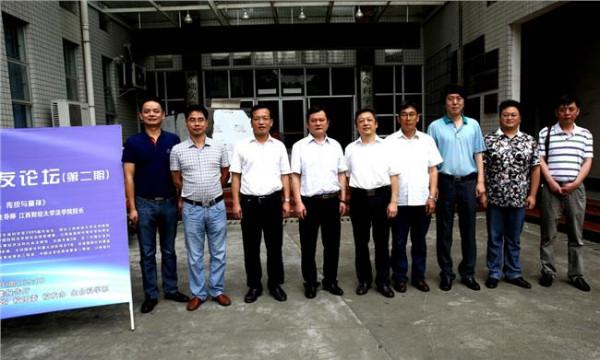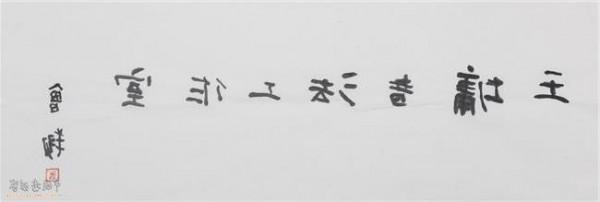刘艳红丈夫 【法治周末】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夫妻:东南大学周佑勇和刘艳红教授
周佑勇、刘艳红夫妻两人都先后获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这实属中国法学界的传奇和佳话。20年来,这对伉俪在科研道路上相互砥砺、相互扶持,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学术伙伴
文/图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发自江苏南京
在刘艳红于2014年2月21日获选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后的几天里,来自四面八方的赞誉挤爆了她和丈夫周佑勇的短信、微信。
刘艳红和周佑勇都是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的教授。难得的是,在妻子成功获选之前,周佑勇已获得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一家“双杰”,堪称全国法学界的佳话!
3月1日,在南京一处约好的地点,坐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的周佑勇聊起妻子获选的事依旧很兴奋。戴着一副银边大框眼镜的他,举手投足间都显得非常稳重,而身边的刘艳红则活泼开朗,不时在一旁打趣。
事实上,即便是得奖之前,刘艳红夫妇也绝对算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同为湖北人,同年同月生,大学本科同一个班,同在武汉大学成为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样学术成果丰硕、获奖无数。
在私下里,他们被学生们称为“神雕侠侣”。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对夫妻的的确确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彼此相互帮助,尤其是互相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
法学家夫妻的青葱岁月
“70后”的刘艳红和周佑勇爱情萌芽于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佑勇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刘艳红则是团支部书记。而这一切的发端,用周佑勇的话说,就是“突然有这么个女生吸引了我”。
“假装无意地制造机会,接近‘犯罪目标’。”刘艳红回忆起青葱岁月使用的也是刑法专业的“法言法语”。在她看来,周佑勇这位狂爱学习的校级优等生并不擅长追女生。
周佑勇则解释说,此时的中南政法鼓励学生报考研究生,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在共同的考研过程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证据是:最后二人都没考上研究生,但是“家事”谈成了。
1994年,在毕业两年后,周佑勇考上武汉大学硕士的第二个月,刘艳红、周佑勇正式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未立业先成家,成为同学中结婚最早的一批人。
在刘艳红看来,周佑勇“天生就是搞学问的人”。因为当大学里大部分人还只知道玩的时候,周佑勇已经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了,而且有多篇发表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当时,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周佑勇说,醉心于学术既有老师的鼓励也有自己的兴趣。看着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一种惊喜,也能感觉到成就感。
上世纪80年代末,正值大学期间的周佑勇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我觉得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到那个时候的确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个对体制、机制的反思和思考。”周佑勇说。
刘艳红则直言自己学术是受到了周佑勇的带动——虽然自己因为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但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甚至觉得写文章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他天天在家写,我一个人没人陪,在他的鼓动下也开始学写文章。但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他手把手教我,给我改,帮我定框架。”刘艳红说,大概有个两三年,也正好是硕士阶段,就慢慢上路了。
而在周佑勇看来,刘艳红有着很好的学术天分,学术敏锐性非常强。他举例说,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刘艳红的硕士论文《罪名确定的科学性》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还发表在了法学界顶级刊物《法学研究》上。“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进入学术界,而且起点这么高。这对我的鼓励特别大。”刘艳红直言。
在这个过程中,周佑勇也给了刘艳红巨大的帮助。在刘艳红去北京大学攻读博士之前,他坦言自己“花的功夫比较多”,主要是为了帮助妻子思考问题,要看很多书。逐渐地,这种帮助成为了相互扩大视野的交流。周佑勇解释,尽管自己主攻行政法,妻子主攻刑法,但法学是相通的,而且两个人从不同的学科去思考问题的视点也不相同。
“学术标签”的产生
刘艳红感到,在北大读博的3年半给自己的影响是终身的。北大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刘艳红的学术兴趣,也历练了她独立自主勤于思考的学术品格。
“在那个过程,我觉得自己实现了一种涅槃,从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学术,到毕业时彻底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完成了一个转身。”刘艳红说。
“实际上我俩有共同的感觉,读博之前都是一个起步阶段,读博之后经过训练,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规划,而不像以前只是懵懵懂懂地搞研究。”周佑勇有着相同的看法,“要有一种学术的延续性。”
周佑勇的研究就是从行政法的原则入手,进一步扩展到行政裁量。他表示,做学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从原则到裁量有一个学术的传承性。这样逐步在规划自己的研究,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走向深入,有影响力,取得重大的成果。”
刘艳红说,在博士毕业后的发展中,周佑勇给自己的帮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文章如何去写,而是从相互的交流变成了给自己压力。
“他说你没有代表作,没有自己的亮点,没有让人一提起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的成果是什么的那样一个作品,你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学术标签。他老这么唠叨,唠叨了好多年,我特别的痛苦。”刘艳红笑着说。
在周佑勇的督促下,经过苦苦思索的刘艳红决定把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由犯罪论到刑法观,由基本理论到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然后在抽象的理论研究之后过渡回来,将之贯彻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
“我就慢慢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自己坚定一点,那就是,要做的话就要做到极致。”从2001年博士毕业后的十多年里,刘艳红就一直专注于同一个问题。
2009年,刘艳红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实质刑法观》为名出版,并迅速引起了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自此不但成为了刘艳红个人的学术立场,更成为了刘艳红特色鲜明的学术标签。2013年,该成果更荣获第六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对于我们来说,写一篇文章很容易,发表也很容易,有的人发几十篇、上百篇。但没有代表性成果,写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周佑勇解释说。
刘艳红觉得,目前不少学者都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印记。“在这点上,我挺感谢他的。我有个缺点,容易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成果多,但他老是打击我,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些问题。”刘艳红笑着说。
重建东大法学院的艰苦时光
在学术上勤奋努力的同时,刘艳红和周佑勇的教职生涯也在不断突破。2002年,在武大博士毕业后留校执教的周佑勇晋升为教授,一年之后,刘艳红也被引进到武大法学院,并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丈夫同时成为博士生导师。
刘艳红的学生、曾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刑法博士、现为东大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的欧阳本祺说:“在武大,大家给周老师和刘老师起了一个名字叫‘神雕侠侣’,因为他们当时是全国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夫妻。”
2006年,在东大校长易红的推动下,东大决定恢复成立法学院,并向全球招聘院长和知名教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周佑勇决定迎接挑战,告别在武汉大学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生活。刘艳红则支持了丈夫的想法。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不能光自己做,要带动一个团队来做,这样人生的价值更大一些。所以觉得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法学院建起来。”周佑勇说。
尽管有决心,重建东大法学院的挑战还是超出了周佑勇夫妇的想象。从生活上到工作上,他们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从亲友温暖的江城到人生地不熟的南京、从一流法学院的平台到一个全新的法学院、从创业的理想到严峻的现实……其中的种种艰辛只有周佑勇夫妇默默体味。
开办法学院时,学院的软件、硬件方面都极度匮乏。根据东大理工强势、法学薄弱的特点,周佑勇在强力引进人才的同时,提出了“交叉性、团队式、实务型”的办学思路,依托学校的理工强势学科来发展法学学科。在东大的每一天,周佑勇都在承担着繁重、艰难的工作。东大法学院副书记高歌说,时常挂在周佑勇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事情没有做好,怎么能休息呢?”
欧阳本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周佑勇为了法学院建设牺牲很大,包括自己的学问。“他到东大之后,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法学院的建设上,两年的时间头发都白了很多。”
刘艳红告诉记者,自从来到东大之后,周佑勇基本不管家庭,“家对他来说主要是个住的地方”。家里的一切周佑勇从来不需也不用过问,因为刘艳红完全帮他解除了后顾之忧。
对于妻子的支持,周佑勇总结说:“她把所有家庭上的事全部承担下来,给了我很大支持;她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出了一大批成果,带动了整个刑法团队,还经常把院里的年轻老师聚在一起,给予指导和鼓励,减轻了我很大压力;她对院里的一些发展也常常提出一些看法,对我能够形成院的发展思路有很大的帮助。”
在学校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周佑勇夫妻的努力下,在全院老师们的团结进取下,东大法学院从弱到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2013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法学一级学科评估中,东大法学院名列全国第29位;在具有硕士授权的51所高校中位列第1名。成为中国法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
稳重与灵动
就在工作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之时,周佑勇选择卸任东大法学院院长,出任东大社科处处长。接手东大法学院的正是妻子刘艳红。
但是在刘艳红看来,行政工作远没有学术工作对自己有吸引力。接手法学院院长后的刘艳红还在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还在向周佑勇抱怨,入职后的一周中,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坐在电脑前。“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她说。
“后面理顺了就好了。”周佑勇说,“你要想想另外一个贡献和责任,要带动一个团队做,不仅仅你个人做,你要为每个院的老师提供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年轻老师,去推动他们的发展。”
在刘艳红眼中,丈夫的优势是稳重,而且一头扎进学术后,“基本上出不来,就像演员入戏一样,根本没有出戏的时候”。她用灵动形容自己,却也反思“韧性不够”。但让她庆幸的是,周佑勇帮助自己磨炼了心性。
而每当妻子发表学术成果的时候,周佑勇是最高兴的人。“反复去读它、看它,觉得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必然有它的独特性和亮点。有时候她发表完了她自己就不看了,但是我却反复去看。”他眼中的妻子,给自己带来了活力,不仅文笔特别好,而且学术理论性和批判性也很强。
严肃的法学研究之外,周佑勇夫妇俩坦言对生活的要求不高,“简单就好”。在放假的时候,两人最大的乐趣是能够看看电影和肥皂剧。
虽然自己对生活要求不高,但是夫妻俩却对自己的学生倍加爱护。“我们师兄买房,周老师都特别关心,会尽其所能借钱相助,以缓解难关。”周佑勇的一位博士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刘艳红的博士生储陈诚也告诉记者,自己刚来东大的时候,刘老师就问他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张罗着托一位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夫妻二人特别喜欢在散步中交流工作和学术中遇到的问题。周佑勇说,特别是在来东大后最艰苦的前几年,二人的交流极大地减缓了自己的精神压力。
采访快结束时,周佑勇夫妇对记者反复提及:“我们的成长,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前辈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同时,在这对夫妻看来,“十大法学家”只是一项荣誉,得到了,当然高兴,但与此同时,也不应看得太重,因为它并不是学术的终点。学术之路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学问做得还远远不够,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今后我们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