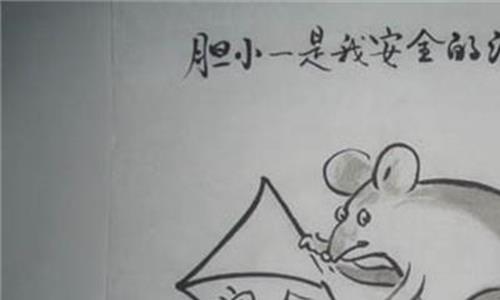惠英红我的一生 专访惠英红:我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两生
没想到,打出来的效果出奇得好。这些年,惠英红没有练过一次拳,也没有做过专门的训练,她平时的运动最多就是跑步。也许是十几年的调理,身上的旧伤都渐渐平复,反而让身体达到了最好的状态。一个动作,她曾经在《霸王花》系列中尝试过,但失败了:先用威亚吊起来,在空中打横,做一个旋子,然后落地,起身踢腿。一整套动作连续完成,对腰部的力量要求很高。以前她做的时候,因为腰部有伤,总是不够漂亮利落。这次特意为她请了替身,惠英红在旁边看着,觉得不太满意,干脆亲自上阵。没想到连拍七个Take,次次OK。“有些东西是你一旦懂了,会了,一辈子都不会丢掉的。”
戏里,五枚师太要把咏春的学问、套路统统交给严咏春,这个角色由新人白静饰演。许多许多年前,惠英红也演过“咏春”这个角色。如今命运交错,她在白静的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功夫片中,女子和男子对打,力量上必然吃亏,每次打完手痛到不行,垂在那里发抖,然后用冰水敷上、消肿。这次,惠英红很明白,自己是衬新人的。“以前就是因为有人陪衬我,才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新人,只有我们这些老鬼,会发展吗?不可能了。”
因为这一次勇敢的尝试,又有不少功夫片找到惠英红,其中包括陈可辛()的《武侠》。开拍第一场戏,她和甄子丹()()对打。一上手,甄子丹()()就喊:“红姐,你宝刀未老!”
“只要活着,永远有机会”
究竟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对于惠英红,她的人生,远比戏来的精彩,“我的一生是别人的两生。”也许有一天,她说如果有机会,会定下来写写自己的一生。她愿意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些不平衡,那些迷失,以及找回平衡,迷失回归。
惠英红出身高贵,满洲正黄旗人,直到现在山东诸城还有“惠家庄园”。父亲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文革时处境危急,带着妻妾子女逃到香港。家道中落,父母只好随便搭一个木屋。三四岁时惠英红就在红灯区要饭。一条街上,有上千个妓女,每天都打照面。很多女孩子为了钱,为了毒品去当妓女、吧女。看透了太多的生死,太多的悲哀,太多的苦难。“有一个大姐姐,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但一个小时之后,她就在酒吧门口口吐白沫,死掉了。看过这种,我还会去吸毒吗?不可能,我一点也不接触,也希望身边的人都不要接触。”
富家子弟落难,比穷人更加不济,不得已先后将四个孩子卖到戏班谋生,排行第五的惠英红成了长女。那一年惠英红刚刚六岁,已经跟着妈妈在码头向美国大兵兜售口香糖,聪明乖巧的她颇受大兵喜欢,生意极佳,竟然就靠着这点活计一年年长大。
70年代经历大萧条后的香港,如同一座妖兽都市,逼仄的贫穷与惊世繁华比邻,更是鱼龙混杂的江湖滩。十四岁,惠英红进入夜总会表演歌舞,三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大导演张彻看中,收为干女儿,成为邵氏签约艺员,月薪五百。这样,不足二十的惠英红,靠着聪明,好学,能吃苦,开始打拼自己的另外一段人生,由此,惠英红靠“打女” 的身份扬名立万。
人生自有起伏,惠英红称之为小小波浪。1990年代末,功夫片势头走低,文艺片崛起。“感觉突然大门关上了。”这个时候,惠英红接到剧本,一看都是第二女主角?第三女主角?很多都是姐姐,然后是阿姨,然后是阿妈。“当时很介意、很生气、心理不平衡。”她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失落:“为什么?很多为什么。越多为什么,越是看不开。”
于是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躲在家里,恨自己。突然有一天,她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吞下很多安眠药。是因为事业进入低谷吗?我试探着小心的问,“事实上,我的事业没有进入过低谷,我是害怕自己变成不是花旦,我害怕自己年老。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叫做年龄的号码,我心态很年轻,可是外界都知道你的号码大小,外界的流言蜚语让你一下子无法面对。”惠英红一字一句非常清晰的跟我说。
好在,抢救及时,惠英红醒转过来,看到自己爸爸妈妈哭得红肿的脸,回忆顿生。“就觉得自己很自私。我很解脱的走了,把更大的痛苦留给了他们。如果真的走了,其实我杀了很多人。再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走?我不是缺钱,我不缺家人。我朋友也跟我说,三十有三十的漂亮,四十有四十的精彩,五十有五十的味道,为什么不能享受每个阶段?一生只过一个阶段,那多无聊。”
豁然开朗后的惠英红,有了重生的感觉,生命似乎刹那间焕发了光彩,以前看不到的美好,所忽视掉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都觉得异常珍贵,“让我感受到了,人世间,最重要的是爱,不只是男女之爱,还包括家人、朋友的爱。其实什么情感都需要老时间去经营,这是我这几年做的主要功课。其实,一个人要去死,是最难的事情,这件事情我都能做到,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抑郁症的伤痛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但惠英红过去一直不敢打开心扉跟人讲述这段历史,直到最近,“现在我能够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这样能够帮别人,如果谁有缘,能够看到、听到这个访问,能够帮助一个人,总比一个人都不去帮要好。所以,我希望能给有过和我一样困惑的人一些建议,告诉他们,只要活着,永远有机会。只要你去行动,做不了一百分,做到五十分,你都是赚了。你走错了,就没有机会再回来,就是零。我曾经笨到这个地步,我希望别人可以聪明一点。”
“哪里是演,而是从心里跑出来的东西。”
其实,真正令惠英红重归影坛的是许鞍华的一通电话。
多年前,两人曾有机会合作,但因为惠英红的合约问题,失之交臂。恰逢许鞍华()筹拍《幽灵人间》,其中有一个母亲的角色,很适合惠英红,因为不是大制作,也不知道惠英红会不会推辞,许鞍华亲自电话:剧本非常好,上次没有机会合作,希望这次可以。惠英红马上应下来:没问题,以前是别人不给拍,现在我自己拿主意,当然好。转而又问:你为什么找我?对我有信心吗?许鞍华说:我从来对你都有信心。惠英红感动万分,“我那么红的时候她没找我,现在她来找我了,世事难料。”
昔日的惠英红又回到了观众视野,并且这一次,多了许多的暖意。朝着目标坚定行走,不惧怕,亦不知退缩,她说,我不管是客串或配角,只要角色难演,能显示出我的演技,我就挑这样的角色。拍何终宇恒的《心魔》,剧本到她手中时,导演说:角色很难。惠英红一看:“有什么困难?角色有精神病?没问题,我自己病了很多年。”
很多镜头,都一次完成,导演也不知道惠英红会怎么演,灯光打好,机器架好,任她发挥,没想到成了极致。“我的人生见得比较多。遇到什么题材,就像是在抓中药,这个,那个,放进去。角色是人,我也是人。把自己放进去,根本就没有惠英红。所以哪里是演,而是从心里跑出来的东西。”
邋遢混沌的母亲角色使惠英红再一次修得正果,她获得了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配角、第十六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女演员、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又拿到了第四十六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时隔三十年,沉浮良久的惠英红再度拿到了那份渴盼已久的荣耀。沉甸甸的奖杯捧在手心,只有惠英红自己更能感受其中的分量,“记得第一届得奖的时候,笨得不得了,奖杯拿回家的时候,还抱怨,这是什么啊,不如给我钱好了,所以到第29届再拿的时候,特别激动,像个新人一样,我还管医生要了心脏药,因为心跳很快。其间,我有多少次盼望得那个奖,每一次金像奖提名,我的压力都特别大。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当我再一次站到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我很懂得那个酸甜苦辣。同样的奖项,对待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无论是在全盛时期还是在低调的今天,惠英红演起戏来,总是有些沧桑落寞的意味,就算是再强势的女中豪杰,镜头前回眸的一刹,也都会流露出一丝楚楚可怜的风情。或许就是这一点点的幽怨,使她多了许多值得深思回味的底蕴。“这些年,我变了很多,以前开工对我最重要,其他的都是其次,十几二十年没有出去旅行过,现在反而不同,我每年都会跟公司说,一定要给我时间和家人朋友去旅行,生活上完全改变,以前满脑子都是赚钱,年纪大了,对物质看得越来越淡。”
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惠英红,愈发从容而自由,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停下脚步的女人。对于惠英红,50岁还太早,爱远没有止息,舞步犹在飞旋,在她美丽依旧的眼眸中看不到一个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