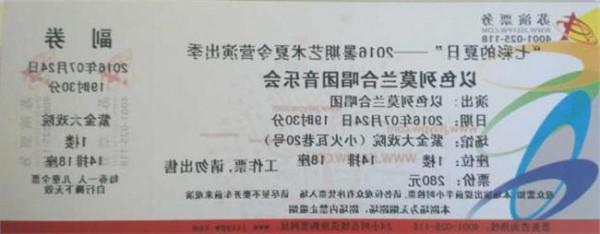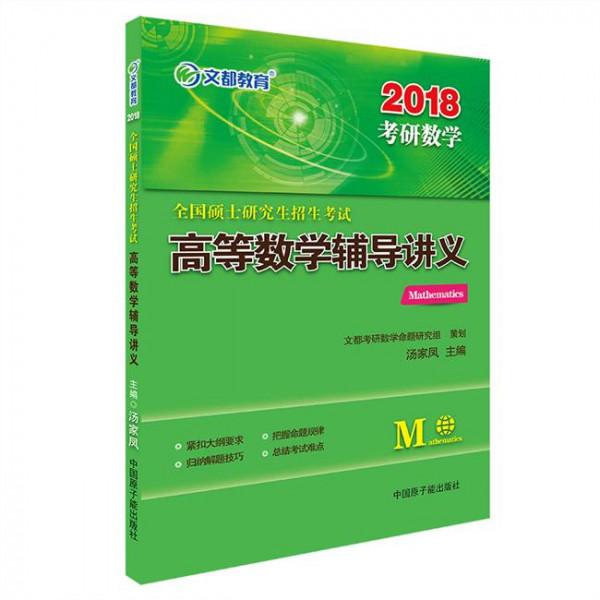张幼仪于凤至 关于三个女人的感性认识: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一]
徐志摩原配夫人张幼仪自述 [美]张邦梅整理 谭家瑜 译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是中国近世第一桩文明离婚案,当时可谓朝野震惊,舆论大哗。而在张幼仪这位中国第一位承受文明“灾祸” 的弱女子眼中,其来龙去脉又是如何?这里节选的是她的侄孙女对她的访谈,这次长达5年的访谈,后来成了一部传记《小脚与西装》。
沙士顿的中国主妇 我们搬到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大学大概有六里远,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
狄更生已经帮徐志摩打点好学校里的一切,徐志摩就替我们料理一些事情。我们租了间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 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我英文,我从开始就想学了,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她要走的路太远,当时我字母已经学了一半,会读“早安”和一点点会话。
我事后才纳闷,为什么我没有坚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让我继续上课。不过,那时候,有太多事要忙了:要买东西、打扫内外,还要料理三餐。
那时我没想过我们夫妻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我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
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着公共汽车去校园。
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我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
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家,然后就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了。
起先我以为是徐志摩需要那笔房租;现在回想起来,又认为大概是郭君一直独居,而徐志摩告诉他,住在一间有人烧上海菜给他吃的房子,日子会好过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独处。总之,郭君住进另一间卧房。
在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间房当书房。郭君不像徐志摩那样常去康桥,而整天呆在房里用功。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话,有时候他会和我一道去市场,或是到新货铺帮我取些东西。我感谢有郭君为伴,至少他会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
不过,有一次他带我去康桥看赛舟,还有一次带我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我们非在白天看电影不可,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本来我们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哦,好吧!
于是我们掉头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电影,结果去了别的地方,这件事,让我并不舒服。
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来府晚餐的女客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我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
” 我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所以我很惊讶,可是我只对徐志摩点了点头,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 他说:“早一点”。 我就告诉他五点吃饭。
他说:“好。”然后匆匆忙忙理发去了。 我那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饭。你知道我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我以为我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 打从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时,我就知道他藏了个秘密。
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与那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
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
他们信里写得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只晓得徐志摩要带个年轻女子回家吃晚饭。我只猜他有朋友事实上也是如此,而且想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吐露这事实。
他大可以干脆一点,向我宣布她是谁,然后叫我接受她,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就算我给他生了儿子,他是有资格拥有别的女人,不管是像老爷那样和她们玩玩了事,还是娶来做小老婆都行。 徐志摩要我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我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我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
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徐志摩显然也会如法炮制。 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所以比我有学问多了。
我料想她会讲流利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那她家人是谁?是哪个地方人?他们认识谁?她兄弟又是何许人? 有一会儿,我想到徐志摩女朋友说不定是个洋女人。
他认识不少洋妞,说不定迷上了她们豪放的举止,大笑时把头往后一甩的姿态,还有穿着露出脚踝的裙子的模样。可是我很快又打消这念头:不,那不可能,没有外国女人会同意以二太太的身份嫁进一个家庭的。
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于是我发誓,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
说也奇怪,我竟然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干脆叫她明小姐好了。 我惟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
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我差点放声大笑。 我们四人(连郭君在内)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明小姐说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长大的,而且提到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几家人。
她父亲在外交部任职,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明小姐家里这么新潮,肯让她单身到海外求学,为什么还把她的脚缠了。
徐志摩把我给弄糊涂了,这难道就是他从两年以前到伦敦以后一直约会的女人吗?为什么是她?他老是喊我乡下土包子,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她那双脚,就显得比我落伍了。可是,她受过极好的教育,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这种女人的话,他为什么不鼓励我上学?为什么不让我学英文?为什么不帮忙让我变得和普通大脚女人一样新潮?为什么徐志摩想和这女人在一起的程度,超过想和我在一起的程度?我并没有双小脚,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书,我学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女人一样多啊!
我恨徐志摩想在家里多添一个她。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喂。于是我脑海突然掠过一个念头:徐志摩要我去打胎,是不是想把这个女人带进家里?想到这儿我都想哭了。
他要离婚 吃过晚饭以后,徐志摩把明小姐送到火车站,郭君回房休息。我那个晚上被搞得心烦意乱,笨手笨脚慢吞吞地洗着碗盘。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厨房洗碗。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对他气愤、失望、厌恶之至,差点说不出话来。
我洗好碗盘以后,徐志摩跟着我走到客厅,问我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 虽然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
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我就说:“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他把脚跟一转,好像我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地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 这是徐志摩头一次对我提高嗓门,我们那间屋子骤然之间好像小得容不下我们了。于是我从后门逃了出去,感觉到夜晚冰凉的空气冲进了我的肺里。 当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徐志摩还在客厅用功。
不过,到了三更半夜,他蹑手蹑脚进了卧室,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时候拉到了床单,而且他背着我睡的时候,身体轻轻擦到我。我虽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却有一种这是我们身体上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在向我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挥手告别的感觉。
事后我们有好些天没说话,虽然这一点也不新鲜了,可是我还是觉得那种死寂快教人受不了了,徐志摩那天晚上说话的声音在我脑中回荡不已。以前他从没那样发过脾气,这很明显地表露了他沮丧的程度,而他在要求我离婚的那一刻,已经把我们生活的次序破坏掉了。
我现在没办法拿捏他的脾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我怕他再提高嗓门;不说话的时候,我又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这样。有天早上,他头一次没吃早饭就走了,我从屋子前的大窗看着他踩着自行车踏板顺着街道骑下去,心想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不告而别 这样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徐志摩就像他当初突如其来地要求离婚那样忽然消失了。他第一天、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没回家,我都还以为他可能去伦敦看朋友了。
陪我买菜的郭虞裳虽然还住我家,可连他也不知道徐志摩的行踪。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
我知道,要是徐志摩早就计划离家出走的话,他至少会记得带他的书。 一个星期过完了,他还是不见人影。郭君好像猜到事有蹊跷,有天一大早便带着箱子下楼说,他也非离开不可了,说完就走。 这时候,怀孕的身体负荷让我害怕。
我要怎么办?徐志摩哪里去了?我没法子睡在与他共枕过的那张大床上,也没办法在觉得自己不会尖叫失声的情况下,穿过一个个房间。我完全孤立无援。 回想在硖石的时候,当日子一天天变暖,附近的西湖出现第一只游船后,我们就会换上轻薄丝绸衫或棉纱服,佣人也会拿来一堆家人在夏天期间用来纳凉的扇子;在他的托盘里摆着牛角、象牙、珍珠和檀木折扇,还有专给男士用的九骨、十六骨或二十四骨的扇子,因为女士从不使用少于三十根扇骨的扇子。
有的扇面题了著名的对子,有的画着鸟、树、仕女等。 我们一整个夏天都用扇子在空中扇着,天气逐渐转凉以后,就把扇子收在一边。所以中文里面有个形容,可以拿来形容被徐志摩孤零零丢在沙士顿的我:我是一把“秋天的扇子”,是个遭人遗弃的妻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考虑要了断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我想,我干脆从世界上消失,结束这场悲剧算了,这样多简单!我可以一头撞死在阳台上,或是栽进池塘里淹死,也可以关上所有窗户,扭开瓦斯。
徐志摩这样抛弃我,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后来我记起《教经》上的第一个孝道基本守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岂毁伤,孝之始也。”于是我打断了这种病态的想法。这样的教诲好像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有天早上,我被一个叫作黄子美的男子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说他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又说他从伦敦带了个徐志摩的口信给我。我就请他进门,倒了杯茶给他,以紧张期待的心情与他隔着桌子对坐。
“他想知道……”黄君轻轻皱着眉头,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徐志摩说的话那样顿了一下说,“……我是来问你,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我没立刻作答,因为这句话我听不懂。最后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
” 黄君喝了一小口茶,若有所思打量我的头发、脸孔和衣服。我晓得他准备回去向徐志摩报告结果,一念及此,我就火冒三丈,突然顶起下巴对着他发言:“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你大老远跑到这儿,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 然后我就送他到门口,坚定地在他背后关上门。我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