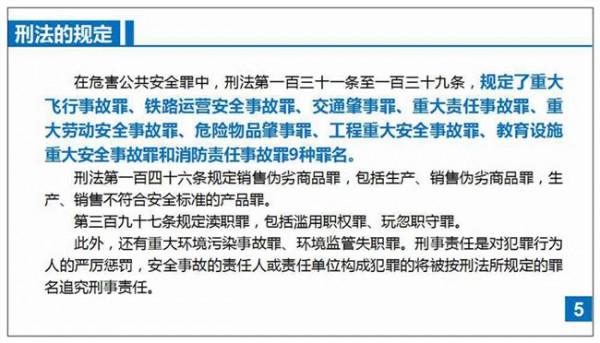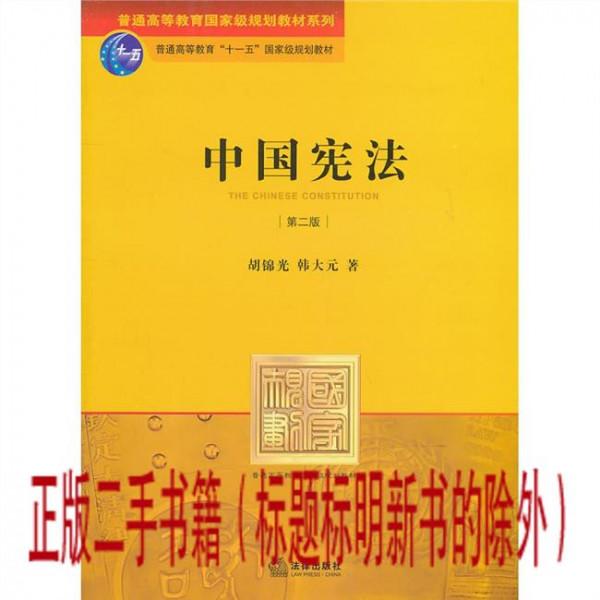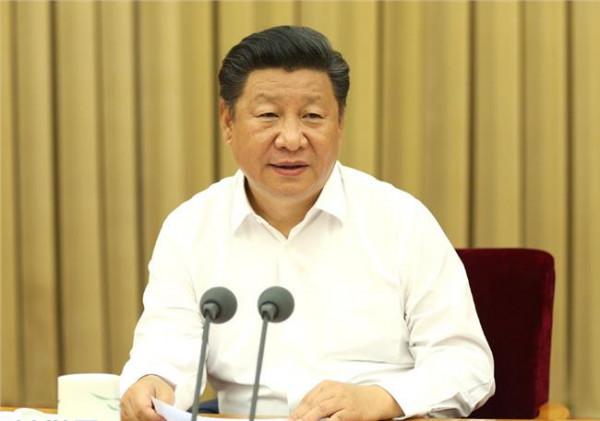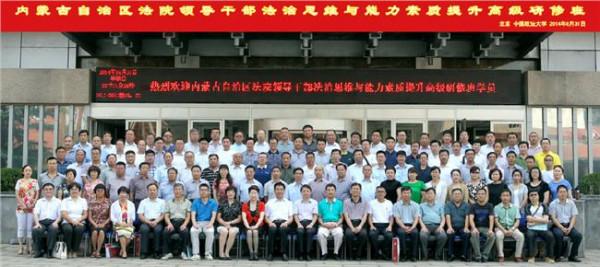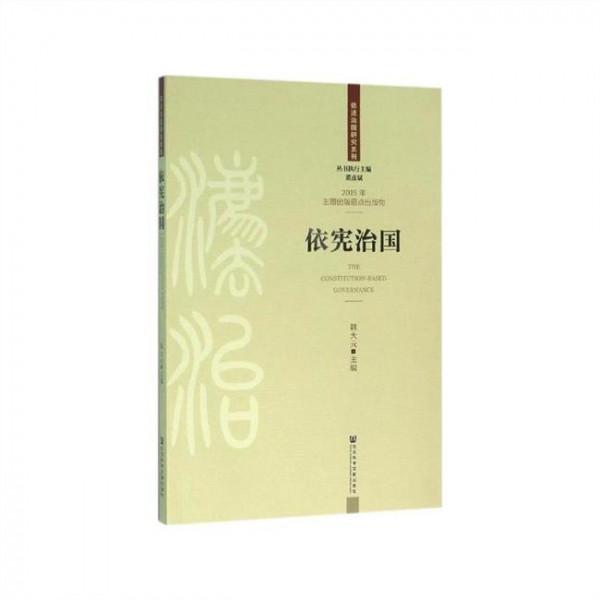中国宪法韩大元 韩大元: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
摘要: 宪法与民法具有不同的调整对象与功能,但在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上民法受宪法的制约,成为宪法的“具体化法”。本文以学术文献为基础,梳理了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历史演变,力求为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合理解释提供学理基础,倡导通过学术对话寻求学术共识。
关键词: 宪法 民法 本土化 公法 私法
从法学史的发展与法律文化传统看,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即“陌生人”阶段、“母子”阶段、“分化”阶段与“回归宪法”阶段。四个阶段的划分主要以宪法与民法关系在学术演变史上的相互影响为基础,以学术发展脉络中出现的学术观点主要学术评价依据,在近百年中国法学的发展中孕育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与不同的理论。
但学说作为“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学术或者思想。在宪法与民法关系上,中国法制近代化是首先从宪政理论移植开始的,宪法学说自然也起源于清末初。
从学说史的视角看,宪法与民法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宪法的发展为民法提价值基础与规范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民法的发展不断丰富宪法学说的内涵,使国家、社会与个人在“公权控制”与“私权保护”的整体框架下形成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
可以说,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学说成为中国法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法学的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目前,中国法学界对宪法学说史、民法学说史的文献梳理和学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从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的视角研究宪法、民法等学科发展的成果不断推出,但真正从学说史的视角对百年来的宪法与民法学说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仍显不足,整体的学术积累并不成熟。
如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发展背后存在着相互互动的内在价值以及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但根据目前的研究资料,无法对两者的内在机理以及对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学术逻辑进行系化的评价。
这是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面对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当代命题,我们需要回归历史,寻找本国的学术传统,提升学术的自主性,推进法学研究的“学术化”。本文旨在梳理宪法与民法关系演变的学术脉络,力求为科学地编篡《民法典》提供一些学说史的参考。
一、1949年以前的宪法与民法关系
1949年以前的宪法与民法关系很少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很少引发学术争论。这是由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主要受到罗马法系的影响,学术界大多承认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在这种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较少直接涉及宪法与民法关系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两者总体上处于“陌生人”阶段。
(一)早期民法学著作中的“宪法问题”
日本学者富井政章在《民法原论》一书中认为,“民法之名称乃日儒箕作麟祥氏翻译法兰西法典始用之,法文又发源于罗马”[1]。而箕作麟祥翻译的时间是1870年。此后日本的杂志、著作中使用“民法”一词,如1874年黑田行元著的《民法大意》、1875年东京裁所编撰的《民法撮要甲编》、1876年何礼之译的《民法论纲》、1880年平田东助译的《独逸民法通论》、1884年小野梓[2]著的《民法之骨》、1896年冈松参太郎著的《注释民法理由》、1898年松波仁义郎等著的《帝国民法正解》等。
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起草本国的民法草案。
“民法”一词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尚未有定论。笔者发现,最早使用民法一词的是1887年的《申报》。1887年7月4日《申报》刊载《风雨送行图记》描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其中提到“由官司省撰民法刑法二书,专以法兰西律”。
此后,民法一词多次出现于晚清报刊,并作为一门课程列于学堂章程。1901年5月16日《申报》刊载《张季直殿撰謇变法平议》,其中提到“德国民法至备至精”;1902年10月3日《申报》刊载《增改现行律例》,其中提到“法律之学有国际法有民法”;1902年10月10日《申报》刊载《京师大学堂章程》,其所开设课程包括“民法”和“商法”;1904年《东方杂志》第2期和第5期分别刊载的《派遣游学类志》和《日本法政速成科规则》,均提到“民法”和“国法学”课程。
1905年《东方杂志》第8期刊载的《修订法律大臣伍沈会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折》将“各国宪法”和“各国民法”同时列入法律学科的必修课程。
中国民法学在兴起过程中借鉴了多个国家的民法学理论和制度,其中日本民法学对中国民法概念、理论体系的影响最为突出[3],而梅谦次郎[4]为影响中国民法学的日本学者的代表人物。梅谦次郎精通法语,参与起草日本民法典和日本商法典,被称为日本民法之父,创办日本法政大学政法速成科为中国培养大批法政人才,推荐弟子松冈正义协助清政府起草民法法典,推荐弟子冈田朝太郎协助清政府起草刑法法典,推荐弟子吉野作造担任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和北洋法政学堂教习。
1906年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夕,梅谦次郎游历中国两个月,会见了很多王公大臣和封疆大吏,讨论法典编纂和预备立宪问题。严献章、匡一、王运震、周大烈、陈国祥、孟森和东方法学会,曾翻译过梅谦次郎的民法学著作,且这些中文译著都多次再版。
1905年严献章、匡一和王运震根据梅谦次郎的讲述编译并出版了《民法总则》一书。该书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民法学教科书之一。梅谦次郎在该书中极简练地归纳出民法的基本属性,即“民法者国法,非国际法”,“民法者私法,非公法”,“民法者实体法,非手续法”,“民法者普通法,非特别法”,“民法者随意法,非命令法”。
[5]他在论述民法为私法非公法时认为,“民法为私法中范围最广者,故一般私法之原则多定于民法,民法与公法时有密接之关系,然以民法之本旨,以保护私权为目的,故其本体皆目之为私法”。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设立的修订法律馆继续从事民律草案的起草工作,1925年完成草案,1929至1930年间陆续颁布民法典总则、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和继承编。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在继续翻译外国民法书籍的同时开始自主地编写民法学著作,同时思考民法与宪法、民法与政治等相关的命题。
1917年朝阳大学出版了系列法科讲义多达33本,包括钟庚言著《宪法讲义大纲》、程树德著《比较宪法》和余棨昌著《民法总论》。1925年第32期《现代评论》刊载一篇书评,介绍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一本民法学著作,即《中国民法纲要》。
该书在民法学背景下专门探讨宪法问题,并将之作为第四部分,与亲属法、民法、商法并列。1928年欧宗祐编的《民法总则》中谈到民法的法律地位时,引用了德国新宪法、奥地利新宪法的有关规定,并简单介绍了宪法与民法在法律地位上的相互关系。
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法学译著比例逐步减少,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明显增多,出版的各类民法学著作、讲义、教材达八十余种,体现了民法理论的“本土化”趋势。
1930年朱采真在《民法总则新论》“自序”中呼吁“建设中国法学派的法学基础”,主张“公法和私法融合”,认为“一部中国式法学论著对于一般读者比起那些欧化或日本化色调极浓厚的法律译作,也许容易引起亲切的情操,这情操是足以鼓励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精神”。
朱采真在讨论民法的渊源时,针对国际条约能否成为民法渊源这一问题,主张可通过在宪法予以明文规定的方式来确定国际条约能否成为民法渊源及其效力等级。[6]
在思考中国本土的民法理论时,学者们积极探讨与中国宪法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代表性的学者是李祖荫。[7]1930年他在《中华民国新民法概说》一文中专门比较了“民法与宪法”“民法与刑法”。关于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李祖荫认为“民法者,人民生活之宪章也,社会生活之基本法也,人民权利义务之准据法也。
以民法与宪法比,则宪法为国家生存的根本法,占公法领域之大部分,民法为人民权义之准据法,占私法领域之大部分,无宪法不能构成国家,无民法不能保护人民”,同时提出“革命的民法,公法化的民法”命题。
[8]其中“无宪法不能构成国家,无民法不能保护人民”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区分了宪法与民法的功能,但“无民法不能保护人民”的判断实际上为后来的“宪法与民法同位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即今日争论的一些学术命题“民国”时期的学者早已有所论述。
当时,宪法与民法关系主要是围绕公法与私法关系而展开,并与法律的社会生存意义具有关联性。有的学者认为,公法私法二元化是外国的理念,中国不应承认。1931年刘陆民出版《中华民法原理》。萧步云为该书作序,称该书作者刘陆民“有志于树立中华新法系”,“不承认有绝对权利”,“不承认公私之区别,以实现人类平等之生活,须减轻公私法的差别,而使公法大众化,此为近世德意志共和国新宪法与苏俄新民法公布以来有力之思想,当然有巨大之价值”。
刘陆民在书中也提到“德意志瑞士新民法中亦有不少公法的内容,若苏联民法更可直称之为公法”。[9]
如果宪法与民法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何区分宪法问题与民法问题的界限?当时部分学者们也做了一些理论思考,如丘汉平在《民法第一条疏义》一文中研究民法典第一条中的“民事”一词的含义,认为“民事”既“别于刑法事件”,又“别于行政事件”,还“别于宪法事件”。
他对于“别于宪法事件”的解释是,“别于宪法事件,宪法与约法同为国家之根本法,其不同者,在于制定之形式及时间之久暂耳。基于宪法发生之事件,非民事,乃系政治问题,即使与民事有关之事件,也属宪法问题。故宪草中之种种人民权利义务,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规定。盖权利义务虽为宪法所承认,但却可依法律而限制也”。[10]
到了20世纪40年代,民法学著作中涉及的有关国家、公法、三民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本位等话题成为民法学者关注的课题,其中包括对民法与宪法功能的理论分析,如1943年郑毓芳的《论民法社会化》、1941年中岛弘道的《个人主义民法之过去及将来》、1946年杨文杰的《所有权限制》、1947年杨宗德的《论民法之社会化》。
1944年黄右昌出版的《民法诠解总则编》就“民法在法律的新分类中之地位”这个问题,提出“民法为根本法(或译准据法)”的命题,“民法者,规定人类私权关系的根本法也,根本法有二,一为宪法一为民法,其他非宪法的附属法,即民法的附属法。
故在今日,不能称宪法为公法,民法为私法,而称两者为一种根本法可也”。[11]
根据笔者对文献的梳理,“民法也为根本法”的命题最早出自于这本书,对后来的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缺乏体系化的论证,也难于成为自圆其说的学术概念。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民法学界一方面进行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法的比较研究,另一方论证宪政体制下的民法社会功能问题,即民法社会化与宪法化问题,代表学者是刘陆民。
他在《论民法社会化与宪法第二十三条》一文中提出宪法效力与民法自身功能的正当性问题,认为“但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如果后其他实体法而产生,或因综合政治上的异见,顺应当前政治的情势,而其立法精神,与其他实体法,绝然异趣时,则预期法律的适用,不发生违宪法否的疑问,是亦甚难解决的问题”,同时认识到“德国以前的民商法,及其他各实体法,其基本观念,也显然不能与魏玛宪法上的个人基本权利义务观合辙”,“与宪法上基本权利抵触的,是否于宪法施行之日,即失其效力?”[12]这种论述开始涉及民法如何接受宪法审查问题,强调民法的基本观念不能与宪法相抵触,提出民法命题宪法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