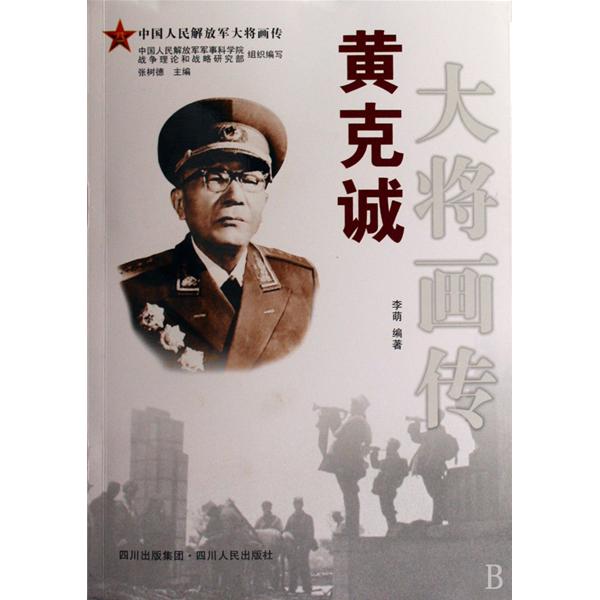许光达大将的子女 从许光达大将任其亲弟弟饿死看毛主席的伟大
在饥饿和死亡边缘挣扎的农民,还随时要遭到非人的毒打和凌辱。 大跃进以来愈演愈烈的打人风,现在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右倾的结果,是使一大批正直的干部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他们鉴于前者的“教训” ,面临来自上面的高压、下面极端恶化的现实的多重压力,乞灵于粗暴恶劣的方式支撑局面,否则他们也免不了被打斗,死亡的几率也更高——干部毕竟有多吃一口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在死人最多的1959底到1960年春年,极少有反映死人问题的官方资料,大部分情况是在1960年年底到61年年初整风整社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而当时的资料,又对死人的原因作了很大的歪曲, 将其统统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或者说不敢)从路线政策上找原因,甚至不敢提“饿死”二字,有关崇庆县五江公社16管区的一分材料说: 去年腊月社员朱克伦因病不能坚持积肥工作,向[队长]粟某某请假未准而哭了起来, 当即被粟发现,晚上召开会议要朱讲哭的道理,朱被赫得屁滚尿流,粟即以随便屙屎屙尿,有辱公共食堂为名, 将朱打倒在地,乱踢一阵,并在严寒季节罚站三个钟头。
朱克伦因此得病趴床不起。病中60 年正月14日朱到食堂称米时,又被粟以样子“褛垮垮”打了一顿马鞭子,这样朱便一病不起 于60年2月24日身故。
如果说朱克伦之死看起来还象是挨打所致,以下的两个例子这样说就很勉强了。 59年冬月初4,社员粟子明,因在田里拿了斤半红萝卜被粟当众打了几个手心,并将粟子明推到柑子树下跌伤腰杆,……冬月底因扫食堂走迟了一步,又被粟打了一顿,以后病势日渐严重,于腊月29日死亡。
社员粟蒋氐(70多岁)因迟到食堂一步,未赶上开饭时间,被粟 鬃打了几腚子,隔三四天即死去。
(见崇庆县委工作组:《粟明章材料》1960年8月2日)。 邛崃道佐公社第二书记杨树楼及该社三管理区主任汪齐松的违法乱纪案件,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当年29岁的杨树楼解放前曾是邛崃平落乡绸缎铺和纸扎铺里的学徒,1952年入党,他“侮辱贫苦农民” 的妙语是:“穿件破衣裳,62个疙瘩,不搞生产去赶场,买一砣肉夹在胯底下,血都跟到胯胯流,回去洗都不洗,丢在茶壶罐罐头煮来就吃。
”据说他亲手打过的社员有66人,打人手段有捆 绑、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数人围住一人推来推去。管区分支书记朱正林在党员大会上被“逗”后几天不能出工,女社员郑本兰被“逗”得“屎尿流了满裤子”。
社员吴天清等3人到法院告杨打人,杨便把他们打成“反动小集团”弄到大会上斗争,并当场宣布“管制劳动”。杨却因为“工作有能力”,1960年10月调太和公社升任第一书记。
有杨书记带头,全社干部打人成风,最厉害的是三管区“当过伪军”的主任汪齐松。据材料称,该管理区二中队43户社员,被他打过的就有40户,其中6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12岁的女孩汪木林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
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胡豆,小队长吓唬他 “等汪齐松回来再说”,汪齐青吓得上了吊。群众见了汪齐松“就如老鼠见了猫”,小孩哭时只要说声“汪齐松来了”,马上就要住声。
据工作组的调查,被汪齐松打死的有5人,打后1至2月内死的6人,3个月后死的11人,打残废的2人。 杨树楼、汪齐松违法乱纪东窗事发,是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到省里。经省公安厅和县委工作组在道佐公社三管区调查,证明控告“基本属实”。
但是,把道佐公社三管区惊人的死亡情况, 归罪于杨、汪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据工作组统计,全管区1958年11月建立公社时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迁入11人。
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5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 ,三个饿得偏偏倒倒的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
社员汪齐洪 、廖文兰(女)等6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三四月份,连到仓库运口粮的劳力都难找了。
干部派工,社员说:“我都不晓得哪天死,干一阵又怎样,死了还不是给野狗吃”。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 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近40%。(见6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佐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