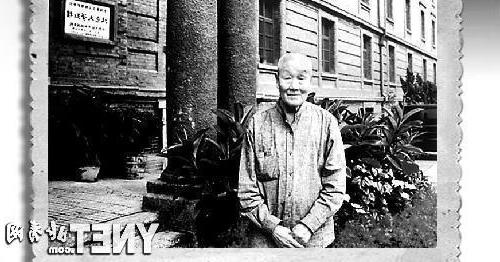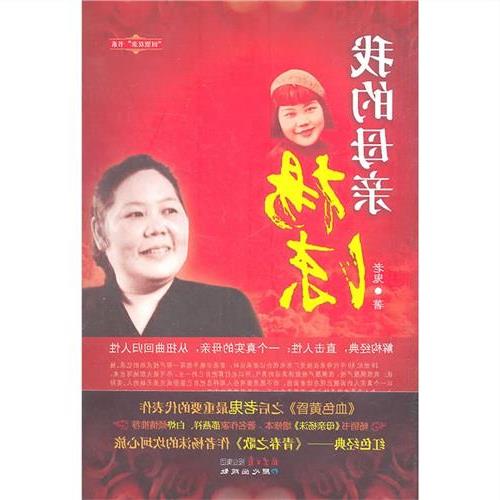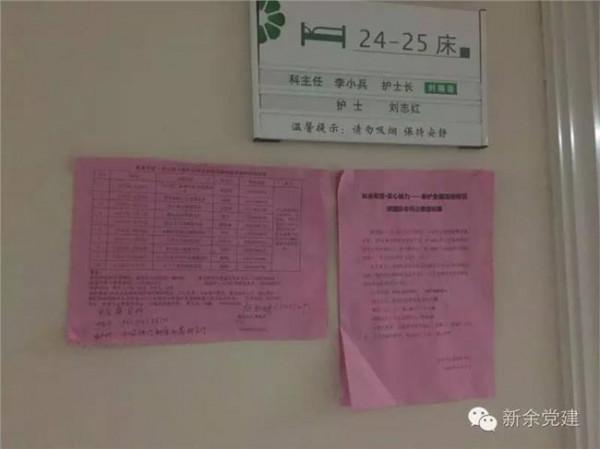张中行与杨沫 往事追忆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
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却正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相恋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他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当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因此,经人介绍认识了杨沫。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
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理,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确实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很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
裂痕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缺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京。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张中行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晚年,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所言极是。
分手
1936年去香河教书,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家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京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母亲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母亲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扫地。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京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年)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