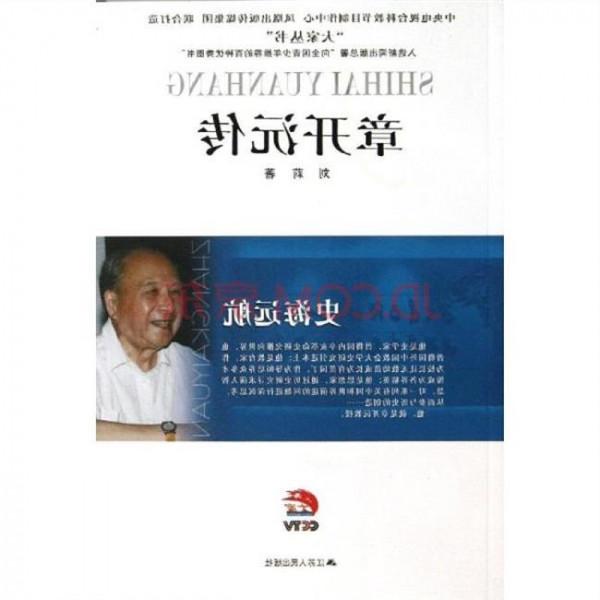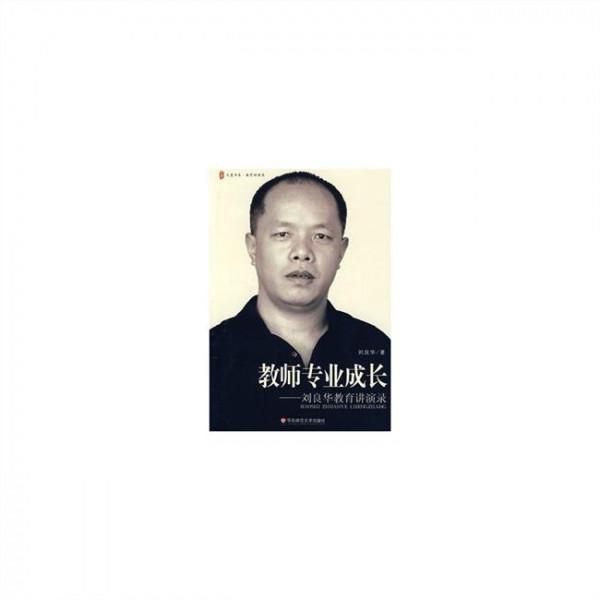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教师阅读 |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最近在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台湾版书名《最后的贵族》),数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作者写这本书也许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但作为万千读者之一的我,受到的最大触动,是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在集体荒唐的环境中,如何保持个人的不荒唐?如何以微弱的一己之力对抗灾难的洪流?如何坚持做人的尊严?这本书记录的很多人都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安庆市枞阳县人,生于重庆,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毕业。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主席、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二女(母为李健生),现为作家、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现居北京守愚斋。
储安平 ——“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弗洛伊德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可以作为储安平一生的注解。他是一个单纯直白到毫不畏惧的人,但“一切畏惧都是从不畏惧开始的。”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不畏惧,让他能直白地指出当时“党天下”的状况,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但历史的公正评判远不是一时能够做出的,正如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所说:“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
章乃器——“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书中写章乃器给我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他的一次穿着。文革时期章乃器和章伯钧有一次难得的会面。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书中还写道康同璧的一次生日会,参加宴会的女宾们“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章诒和非常纳闷,因为当时连花衣服都被当成“四旧”取缔了,她们怎么能这么打扮?
原来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穿衣,体现了一个人的精气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一个人的内在。“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
康同璧和罗仪凤——有的人只在生活优渥时保持优雅和仪式感,而有的人即使三餐不继,仍不会放弃这两样东西。
章诒和有一段时间曾经寄住在康同璧家中,一次闲聊说起来想吃西餐,当时康同璧家已十分拮据,就连准备待客点心的钱都要从早餐费里一点点扣除。但是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答应在家中吃一次西餐,但是要给她足够的时间准备,书中对这餐饭是这样写的: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坚信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一丝不苟地准备一次西餐的人是一个贵族,即便他在经济上落魄,他在精神上也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章诒和——大多数人善于为自己所做的坏事找借口,只有少数人会痛苦地自省。
作为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曾经在四川的一所监狱里进行劳动改造,出狱后她与聂绀弩有过一次谈话,说到了几年的劳动改造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反省了自己在监狱里的一件事。当时由于告密可以减刑,监狱里告密成风,有一个叫张家凤的女犯人由于改造态度不好,成了众矢之的,监狱的管教干事知道章诒和文化程度高,就派她每天跟在张家凤的后面,拿着纸笔记录她的反动言行,后来张家凤被判了死刑。章诒和在书里写到:“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章诒和非常直接地对聂绀弩说出了自己的“罪责”,尽管聂绀弩告诉她“错不在你”,章诒和仍然说:“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潘素和张伯驹——一个人因自己的行为遭受灾难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在遭受灾难以后,他仍然能继续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
章伯钧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后,全家人都受到了社会的排挤。有一次,章诒和的母亲在路上见到了一个名叫辛志超的老熟人。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180 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
章伯钧死后,情况更是恶劣,几乎没有人登门拜访,这时却有一对老夫妇敲响了家门,就是张伯驹和潘素夫妇。
母亲说:“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
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
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
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一个真正的人,往往会忘记计较自己的得失,因为他们的生命中有比自己的得失更为重要的东西。
黑暗的时代,往往会激发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但也能显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书中写的这些人,给我的触动实在太大太大,我从没把这本书当做历史书来看,它所记录的是作者往日生活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的经历与国家、政局息息相关,他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历史,但更为珍贵的是他们本身。
我也从没认为作者的记叙有多么客观,她用的是一支饱含感情的笔,尽管一再克制不让过多的怨愤流露出来,但你可以看出她有多爱自己回忆中的这些人。这些人有缺点,但流逝的岁月把这些微不足道的缺点抹去,留下的是他们最动人的品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