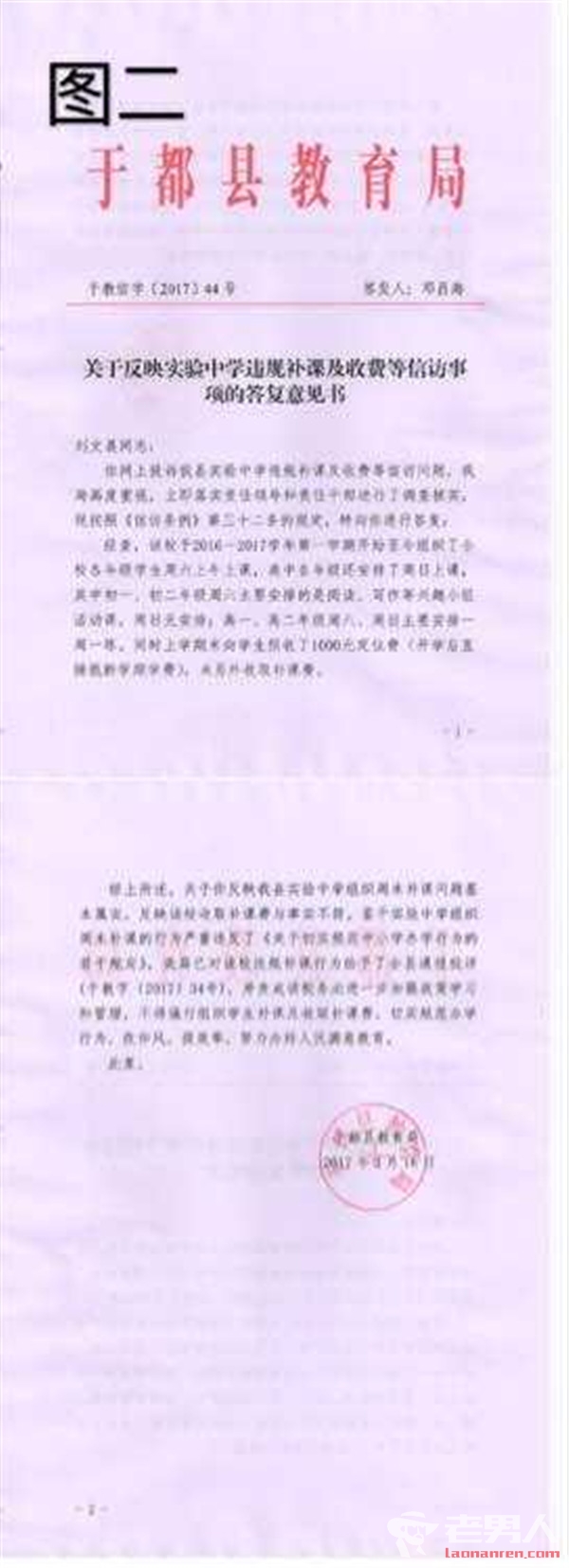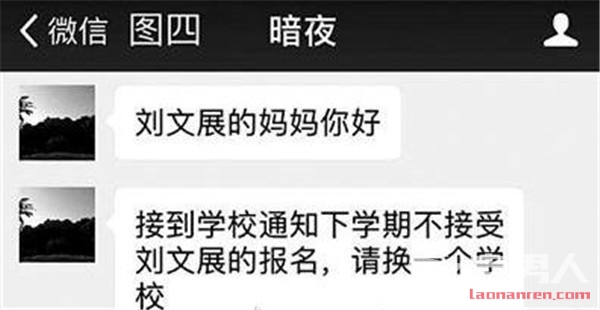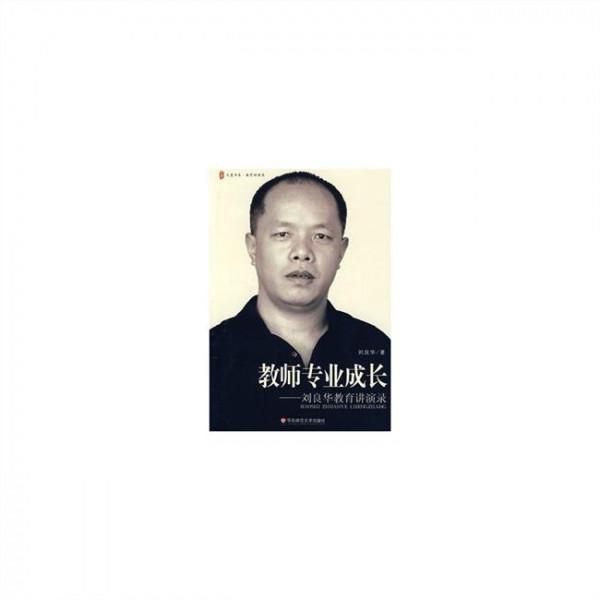刘东生的学生 伟大的科学家与教育家——怀念刘东生先生
二〇〇八年初春我因心脏病正在北医三院住院,不久突然得知刘东生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十分震惊与悲痛。我作为刘东生先生的“编外”学生已经整整50年了。我是1958年认识刘先生的,50年来从没有间断过接受他的指导。1959年我因身体原因不能出野外,就参加了刘先生主持编绘的1/400万全国黄土分布图的工作,当时我对黄土知之甚浅,在学习与编绘黄土图的过程中得到刘先生的直接指导,同时也得到丁国瑜、王克鲁、朱海之等各位先生的帮助。那时的地质所第四纪室还在城里北大红楼,我每天早晨去,下午回北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黄土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和多位先生建立了友谊。刘先生不仅指导我们绘图,还经常为我们讲授有关第四纪方面的知识,并把他亲自拍摄的许多黄土照片拿给我观赏,而且还让我带回北大复印作为教材使用。
刘先生在科学领域为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与敬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地对黄土地层及黄土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对黄土的基础调查和室内分析开始,逐步深入到黄土的内涵研究,他高瞻远瞩将相关的学科引进到黄土研究之中,加深了对黄土的了解,并提出了中国的黄土是陆地第四纪沉积中最完整、最富含环境信息的地质载体。他重视科技手段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建立了黄土与古土壤层的更叠,划分了新的黄土分层、年龄及生物演化等一系列新观点。在此基础上,将黄土与全球性的深海岩芯、极地冰岩芯进行了对比,从而建立了全球性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国际对比标准,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认可与信服。他坚持科学考察,足迹踏遍全国及世界各地,甚至在年事已高的时候还亲赴南极、北极、南沙群岛,并多次赴青藏高原考察。他60多岁时还亲自到瑞士Heller教授的古地磁实验室做实验,这在科学界实属罕见。
刘先生思维敏锐、高瞻远瞩、学识渊博、勇于创新、著作丰硕。他将气候学、土壤学、生物学等学科溶入到第四纪研究领域,扩展了第四纪研究的深度和范畴。刘先生到老年时期将他多年的研究硕果与丰富思维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总结出许多富有哲理的理论。他是真正的“大师”级科学家,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
他曾担任INQUA的主席及两届副主席,是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数十年来的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在他老人家主持下的中国第四纪研究得到了飞跃发展,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与他善于团结世界上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密切相关。刘先生是第一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地球科学家,是第一位获得国际泰勒环境奖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其它许多重要科研奖项。他是第四纪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刘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出色的人才,同时他非常关心高等学校的第四纪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他对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寄予了很大期望,希望北大的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建成为国家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现以我个人的切身体会,回忆刘先生在北大的工作和对我个人的教导。我常说:“我是刘先生的‘编外学生’,我自知我这个学生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但我自始至终确实是按刘先生的教导尽力去做的。
”五十年前北大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安排我担任新开设的“第四纪地质”教学任务,我心里非常紧张,我已有的第四纪基础仅仅是听过苏联专家巴甫林诺夫和袁复礼先生的系统讲课,让我上台讲第四纪确实很吃力,而且第一次是为古生物专业的学生讲授。
当时我认识刘先生不久,那时我年轻也不知“害怕”,就向刘先生谈了这个难题。刘先生鼓励我大胆承担此任务,并且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教学资料和讲课要点。把他亲自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照片借给我复制,在我编写的教材和参考书中新使用的黄土照片几乎都是刘先生早年拍的。
此外,他把他亲自编写的第四纪教材(打印的)全部借给我参考。并且经常把他自己的有关参考书委托马宗晋先生带给我使用,甚至他还亲自去借裴文中先生的几本古生物图册让我参考,在我编写的几本教材中新引用的大角鹿、披毛犀等复原图都是取自裴先生的图册。
我借用这些参考书使用的时间往往很长,用1~2年才归还。在此谨向马宗晋先生表示感谢!在我讲课时遇到难题经常写信向刘先生请教,有时我去地质所当面请教,刘先生总是耐心的给予指导和支持。
有一次讲到意大利的Villafrachian标准地层,我找不到具体的剖面,在一次会议上我趁机请刘先生帮忙,他说:“我一时也想不起来,让胡长康帮你找找吧”!
像这样的指导和支持真是数不胜数。在此还必须提到,当时王克鲁先生对我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指导,他常把自己的论文和资料借给我用,有时为我讲解他的想法,在蓝田考察时更是对我关照备至,谨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我的第四纪教学逐渐走向成熟,这与各位老师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刘先生叮嘱我,搞第四纪地层必须有古生物基础,让我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按照他的指导争取各种机会学习哺乳动物化石,后来还学到了一些孢粉及微体化石的知识,充实了教学和科研的能力。
刘先生是北大的兼职教授,多次来北大讲课,每次讲课一口气讲4个小时,就是我们年轻人都会感到吃力,何况刘先生已进入老年呢!刘先生讲课时精神集中,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每当我有第四纪课的学期,他就利用这段时间为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师们讲授第四纪。特别讲到早年时代一些老学者们的考察与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更引起我们的兴趣,使我们更多的了解了第四纪研究的早期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真是“名师一点,胜读十年书”!刘先生讲课时着重讲解当前国际第四纪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希望年轻人能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思想,为第四纪研究做出新成绩。有几次在北大讲课时间达到4~5周,最后一次是在1995年春,四节课间基本不休息还站着讲,讲累了就喝点茶。这时刘先生已78岁高龄,竟然还是那么精力充沛,不过那次讲课为了保护刘先生的健康,每周都由胡长康先生陪同前来。刘先生的讲课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刘先生是北大的博士生导师,1985年高校扩大招收研究生,我们很希望刘先生在北大培养博士生以提高研究的水平和质量。经过同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多次协商,最终得到了批准,北大特聘刘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当年北大招收两名博士生包括第四纪地质与环境科学各一名,我和陈静生做刘先生的助手。其中石宁在刘先生的指导下重点从事古地磁研究,后来经刘先生推荐,他赴瑞典留学并获得了良好成绩。
除了上述具体的教学之外,他还多次对我说:“你在教学和科研中有什么要我帮助的,如请国内外学者来北大讲学等等,我都可以帮你们办到”。老师对北大第四纪的支持和期望,使我非常感动。
刘先生特别重视国际交流和合作,鼓励年轻人了解世界,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我曾亲自聆听刘先生的名言:“要想获得一流的学术成果,就必须与国际一流的科学家合作”。他完全实现了这一宏伟的理想。1982年我国对外开放不久,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首次派代表团赴日本访问,主要成员是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和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而刘先生建议我参加,一方面代表高校,另方面也是为我提供对外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我得知后心情很激动,当时这是连想都不敢的事。在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期间,刘先生把我找去,他说:“你在北大从事第四纪地质教学多年,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如第四纪古气候、古海面、以及新构造与火山等等,希望你这次去日本能多发挥些作用”。老师的期望和要求鼓舞了我的勇气和责任,这是国家的代表团,绝不能有损国家的形象。我在日本做了学术报告,参观了许多第四纪地质剖面和活火山,同时学到了不少人家的先进的研究成果,开阔了眼界。
刘先生不仅仅只是参加第四纪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的指导。而且他主动参加北大的社会活动和大型会议。1995年冬北大召开各系博士生导师大会,刘先生主动前来参加会议。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他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咱们专业的庆祝会在哪儿开会?什么时间?到时我一定去”。5月5日晨我亲自去迎接刘先生来北大,他同我们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共同举行庆祝会,并与师生们合影留念。此外,他还同他们老一代的地学家另外聚会表示对百年大庆的祝贺。
在此我要郑重说明,刘先生虽然多年应聘为北大的兼职教授,但却一直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义务培养人才。
在改革开放之初,自1979年开始我应聘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在的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第四纪地质,开始在林学院旧址,不久迁到玉泉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址,此处距北大很远,每周一次讲4小时,早7点出发,中午1点多才回到家,感到很疲惫,我连续讲了数年,后因北大的教学任务繁重,就提出谢绝应聘。
当时研究生院的师资缺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的负责人向刘先生提出请求,刘先生知道后就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教学任务重,今后研究生院的课由我们两人分担讲授如何?一人一半,我讲前半部,你讲后半部”。
我感到很惭愧,当时就同意了刘先生的意见。那时刘先生已是高龄,工作繁忙,竟然在百忙中为研究生院亲自培养人才,实在令人敬佩。
为了不失掉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每周按时去听课,直接聆听他的精彩演讲,这使我又学到了更丰富的第四纪知识。在他讲课时对该系负责人说:“到北大去借曹家欣老师编写的第四纪讲义40本,作为大家的参考书。” 这是刘先生对我的鼓励和信任。刘先生为研究生院亲自讲课多年,直到他的晚年才由他的弟子们接任。他为我国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付出了毕生精力,其精神之伟大令我终生难忘。
这篇回忆谨向我的老师刘东生先生表示深深地怀念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