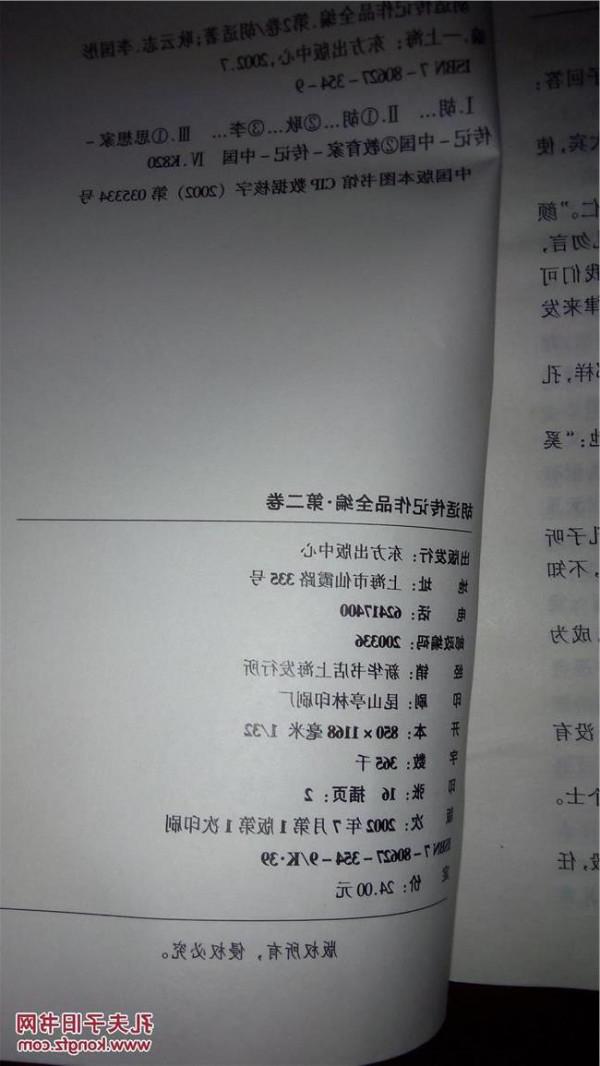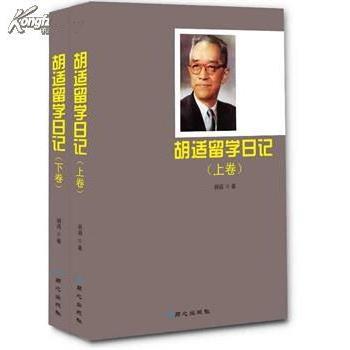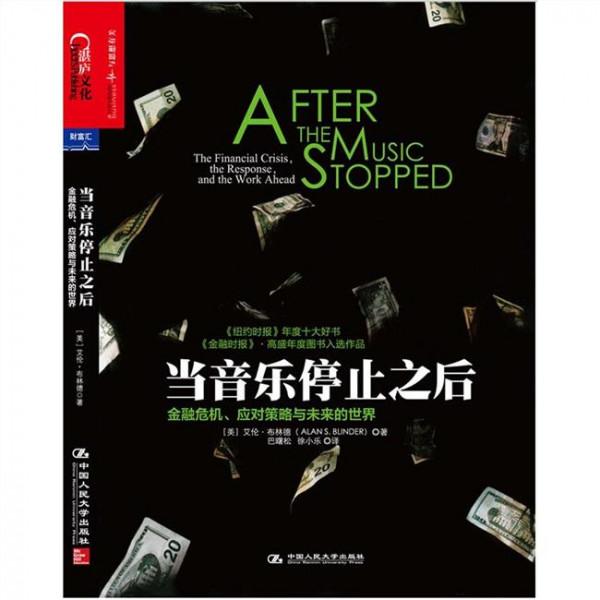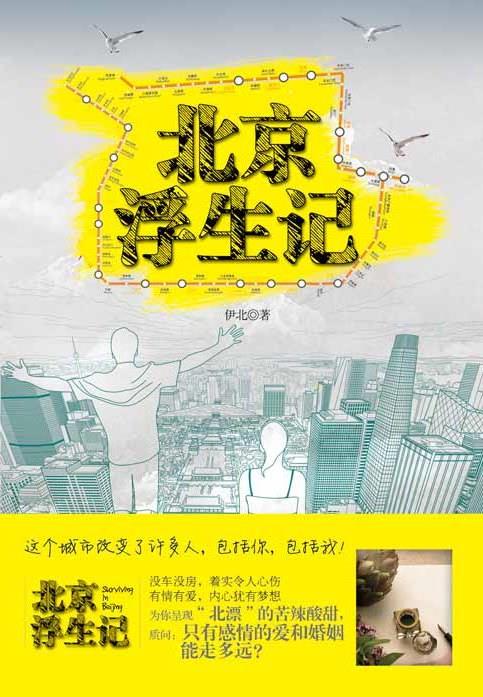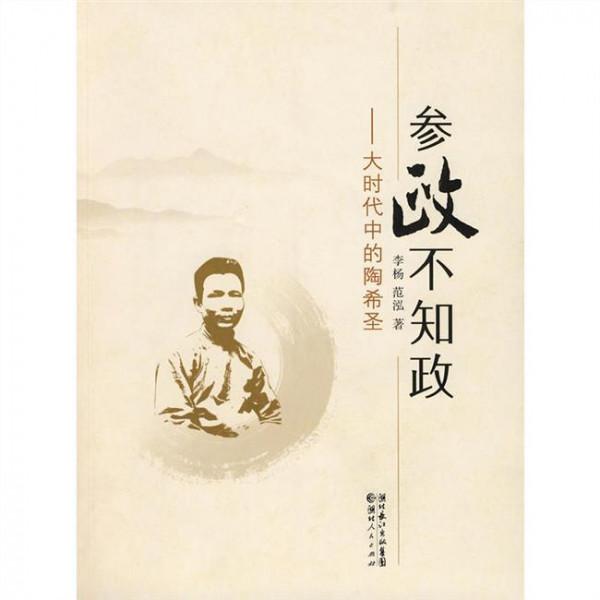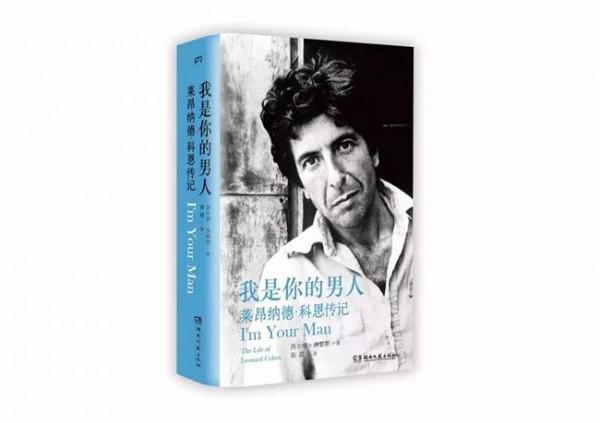最权威的胡适传记
《舍我其谁:胡适》以传记的形式,追踪胡适从小学到大学全部求学过程,细节详实、丰富再现“中国思想界第一人”如何长成。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用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说话,澄清以往关于胡适的许多重大误会,作者通过比勘不同版本,阐释《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背后的真相;重新塑造“上海时期”胡适的思想状态,挖出被胡适淡出乃至完全湮灭的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修身进德的焦虑。
“我的理想是希望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他的学术、思想、生活与事业,并透过这部传记,来重建胡适所处的社会、时代的风貌——不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功成名就于斯的中国大陆也好,还是他留学、访问、持节出使、以至于流亡的美国也好,甚至是他龙困浅滩以至于终老埋骨的中国台湾。”江勇振的这部传记虽未全部出版,但第一部面世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誉为“学界公认最权威的胡适传记”。本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江勇振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2006年)。
最新著作《舍我其谁:胡适》预计共分五部。第一部,从1891到1917年;第二部从1917到1927年;第三部从1927到1937年;第四部从1937到1942年;第五部从1942到1962年。
所有的“人云亦云”、“胡云亦云”,都先要推翻
锐读:胡适其人、其文对您有何影响?为何会选择他为研究对象?
江勇振:我在台湾成长的阶段,由于知识、思想才开始萌芽,胡适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潜移默化方面。他的文字隽永、思路清晰。在那看似理性的语言之中,其实蕴藏着无比感性的诱力。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对研究胡适开始动心了,倒是迟迟不敢动手。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恐惧。胡适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不但著作等身,而且涉猎极广,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能自成一家,树立典范。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知识有限,无论中学或西学都比不上胡适。终于能克服我的恐惧来研究胡适,是因为我找到了新的观点,可以重新诠释胡适。
锐读:可否用一句话来形容,胡适在您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的哪一句话,最打动您?
江勇振:胡适是一个天才加努力的人。他聪明过人、悟力超群,能取人之长、化为己用。胡适很擅长于铸造一些隽永、动听、令人难忘的词语。留美的时候,他曾创造了一句格言:“捕捉感觉、印象最好的方法,是用语言文字去把它表达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他所说的:“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现在最喜欢的是:“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锐读:这部传记,据说计划出版5部,每部50万字,为什么规模会如此之庞大?
江勇振:我在〈前言〉里就说了:这个写作构想“下笔不能自休非其咎也。所有的误解、传说、人云亦云、胡云亦云,套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都需要先去‘推翻’、‘打倒’。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抽丝剥茧、解构之余,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诠释,并重新编织出一幅不为胡适所预设的图案所羁、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团锦簇的胡适的一生。所有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予岂喜辞费哉?‘予不得已也!’”。
不能让胡适牵着鼻子走
锐读:这本书腰封写着一句话:“颠覆余英时、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等名家旧说。”请问相比之下,您的这部胡适传记的创新点有哪些?
江勇振:腰封上的这句话是出版社促销的用语,是出版后我才知道的。当时我建议用胡适说的那句:“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我希望这本书里,确实是用了“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至于是否真的做到了不让胡适牵着鼻子走,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锐读:对于上述提及的几位胡适研究专家,您有没有很推崇哪一位?或者说,哪一位的某个观点让您最接受不了?
江勇振:学术的成长是累积的。没有前人的努力,后人是不可能后来居上的。我们在援引、补充、修正前人的成果的时候,会有好恶之心自然是难免的。但最好不要让它浮现到台面上。同时,我们也须体认到自己的努力,让后人去援引、补充、修正、批判,甚至推翻。这是学术进步的轨迹,也是学术能日新月异的基础。
锐读:您说:“研究者必须要能入胡适的宝山,得其宝,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宝山主任收编为他的推销员。”那么,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对于胡适经过修饰的《四十自述》《胡适日记》这类传记资料,您以怎样的标准来取舍?
江勇振:胡适的《四十自述》、日记等自传资料自然是传统方法学上所说的第一手资料。但所谓的第一手资料也都是建构的产物。要如何能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还是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胡适在留美的时候常常用来砥砺自己的话是:不要以耳代目。
这也就是说不能人云亦云。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到底是说了什么,一定要自己去看过才算数。我们研究胡适,也必须去读胡适所读过的书;去追寻胡适思想的来源、时代与脉络;去追问胡适对杜威(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的了解如何;去细思实验主义所说的是什么?胡适所说的实验主义又是什么?
锐读:您认为:“正由于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于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他的一生正是用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最理想的透视镜。”这样的评价是否有拔高之嫌?
江勇振:我说胡适的这些话绝对不言过其实。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祭酒”、是知识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可以作正反两面的诠释。宗师、巨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霸权、舆论权威的意思。而所谓“霸权”、“权威”也者,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要看读者如何拿捏。
胡适掌握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资源。我在《世变中的史学》的话说过:“作为一代宗师,他订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他根本上是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换句话说,胡适在学术界的龙头地位,让他能够掌控学术资源,让他在学术界扮演了把门、把关的角色。作为当时主要学术、拨款机构的领导人物,他一方面可以安插人事、巩固并扩充地盘;另一方面,他可以决定研究议题、方向与标准。人事权与研究臧否权,两相在握的结果,就是学术霸权的建立。所有这些,都请看我《舍我其谁:胡适》后头的几部。
胡适与鲁迅,没必要帮他们“一争高下”
锐读:您怎么看待胡适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巨人的关系?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胡适与陈独秀同为倡导者与领袖。您觉得两人所起的作用有什么不一样?
江勇振:坦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仔细或系统地想过。但这是我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所必须处理的问题。由于这套胡适新传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希望我在第二部里能够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锐读:胡适与鲁迅被很多大陆学者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您又怎么看待胡适和鲁迅各自的地位和贡献?
江勇振:胡适与鲁迅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巨擘,都各自有他们的地位和贡献。我个人觉得没有扬此抑彼的必要。去争论胡适鲁迅的高下,就好像去争论贝多芬还是柴可夫斯基谁比较伟大一样,是无谓的争论。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都听、都喜欢。我没有必要从中选一,划地自限,无谓地失去我能欣赏优美的音乐的乐趣。天下好文我都欣赏,也都可以拿来作我的注脚;就好像所有此曲只有天上有的天籁,我都想把它们拿来人间听几回。
锐读:但是,中国大陆学界曾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尊鲁贬胡的倾向,1950年代还掀起过批胡运动,直到近年来胡适其人其学才得到了重新评价与更广的传播。您觉得,胡适在大陆和台湾的境遇为何如此不同?
江勇振:毫无疑问,对胡适的评价,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够开放。即使今天学术界对胡适的重新评价,其实未尝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切研究、一切评价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由研究者的出身、性别、学历、身份地位、族群认同等因素所型塑出来的。
锐读:关于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1933年写过回忆文章《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对此,您在书中认为胡适不但不是被“逼上梁山”,而且,即使他是上了“梁山”,那也绝对不是违反初衷,而其实是梦想成真。为什么这么说?
江勇振:毫无疑问,我这段话的目的就在解构胡适自己建构出来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我们不要忘记,胡适这“逼上梁山”的自白,是他功成名就以后、要为自己在历史作定位的《四十自述》里所建构出来的故事。
我们用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里所津津乐道的“历史的方法”的话来说,这历史的方法,就是“祖孙的方法”,就是“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
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胡适的文学革命,我们就必须去追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上英国文学的课,从而自己实地试验,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诗格律来练习写英诗,再从英诗的写作、英诗汉译与汉诗英译的经验里悟出心得与信念,再把这些诗国革命的心得与信念和友朋演练、论战的整个来龙去脉。
从这个历史方法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记者观察——
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胡适的一生是灿烂的。他曾任北大校长,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学术界领导过新文化运动;而在他人生的巅峰,国际是他的舞台。他一生中与之往来唱和,在思想上平起平坐的,是思想上的奥林帕斯巅峰上的众神及其山腰上的众仙;在他的大使任内,往来的冠盖,有美国罗斯福总统、国务卿及其司长、著名大学校长以及显贵富豪的社交圈、各国驻美使节、访美的王公将相等。
几经浮沉后,在其诞辰120年之际,胡适的名字仍是热点。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胡学”真可谓蔚为大观。
至于今天我们重新来研究胡适这个人,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江勇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研究胡适,做得成功,首先就是研究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即“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
其次,就可以了然胡适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天才加努力的结果。孟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相比于“登上过泰山”的胡适,平凡的我们则多半是无缘“泰山”之巅的。但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指标在哪里呢?那就是:平凡的我们即使上不了泰山,即使只有做井底之蛙的宿命,我们还是可以立志做肯读书、能思想的青蛙。那读了书、开了眼界的井底之蛙说不定终究可以不为井底所囿,因为知识与思想有解放的作用。
诚然,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凭借天马行空的思考,便能说出很多天才的口号与思想,其远见卓识也是不容忽视。但是一味拔高胡适的地位,却不能鉴别其思想的幼稚一面,恐怕也非明智之举。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所言,这些天才的口号与思想,由于一棍子打倒或者缺乏严谨的论证的历史环境束缚,往往流于大话空话,破坏多于建设,所以抬杠的成分并不少,有价值的学理探讨倒在其次,尤其需要当代学人的审视。
站在21世纪之初,我们中国人重新审视五四一代启蒙人物,尤其不能跟着他们的尾巴后面,拾人牙慧,而忘了创新。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重新反思的时代必将来临。在这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的古老文化价值正在熠熠生辉,重新崛起,那么中国的民族认同与自豪感也需要重新崛起。
卢欢/文
今天我们对胡适的研究是否又到了一个可以更全面、更客观但又同时对于现实中国更有针对性价值的新阶段?一方面,“回到胡适”的客观真实性由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新史料的发掘整理而更有条件,另一方面在时代思想的撞击中胡适思想的中国意义更鲜明地凸显,胡适研究汇入中国政治与文化前景研究的时代呼唤更显得迫切。
——李公明
我读胡传第一部,有点像在读武侠小说。胡适就像初入江湖的少侠,他广泛的阅读就像到处找人过招,那些读物就像各个门派的武士,武士的功夫有好有坏,读物的水平有高有低,但少侠胡适天赋异禀,他能将每个武士的一技之长,每本读物的一得之见,化为己有,终于练成绝世神技纵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