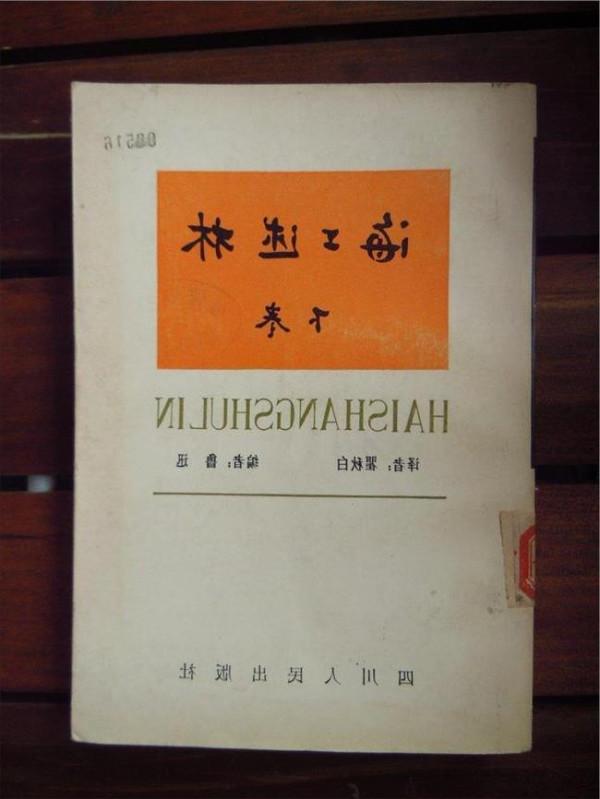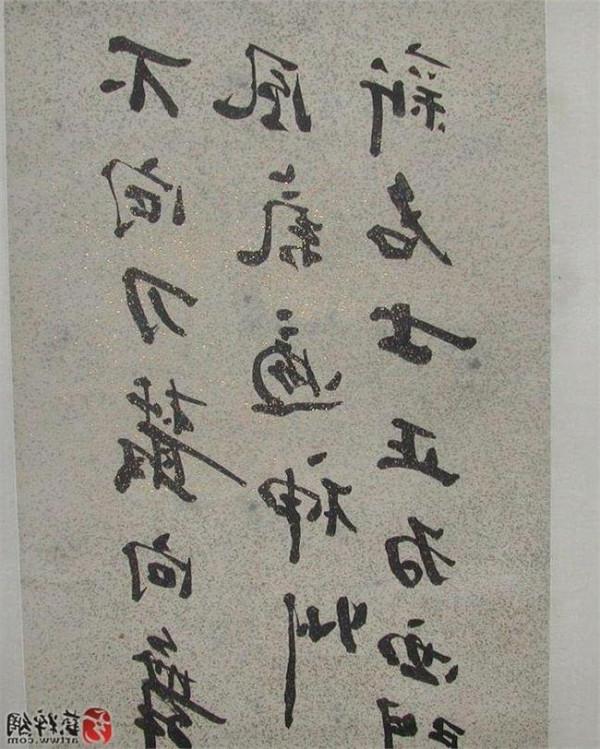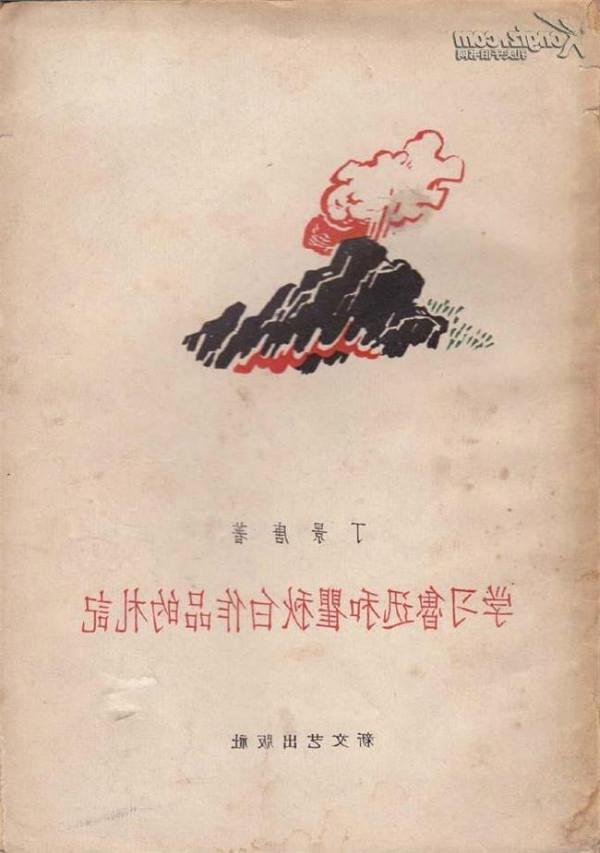瞿秋白鲁迅 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与左联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茅盾对这一决议这样评价:“我以为,这一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步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
”(注: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载《新文学史料》81年第3期,101页。
)这个11月决议是瞿秋白积极参与下由冯雪峰起草的,因此,茅盾又说:“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注: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载《新文学史料》81年第3期,101页。)
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前后,应该说左联形势“大好”,以至于当时不仅左翼文化人,即使是中间派也大谈新兴文艺(无产阶级文学),并争相挂上这个牌号。例如宣扬唯美主义的《金屋》月刊,也追赶时尚来翻译左翼文学。
于是受到邱韵铎的嘲笑:“《金屋》也竟然印行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注:旷新年:《1928年革命文学》,7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在这样有利的舆论环境下,左联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出席的有50多人,济济一堂。左联成立不久,上海的社会科学、戏剧、美术等各界,也相继成立了左翼文化组织。
但形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1930年9月, 国民党中执委下令取缔包括左联在内的一批“反动组织”,查封机关并“缉拿其主谋分子归案究办”,还附了一份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左联盟员名单49人。
(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与此同时,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再次统治了全党。
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在立三路线及稍后的王明路线干扰下,左联受到重创,阵地几乎丢光,人员几乎散尽。
仅1931年10月一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左翼书刊就有228种。(注:缪君奇:《试论左联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 《左联研究资料集》,182页,左联纪念馆编,1991年。
)左联五烈士及林育南等18名中共干部于1931年2月7日被害于上海龙华。茅盾在《关于“左联”》一文中说: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有许多加入盟的联盟员都动摇而退缩,后来就完全消极或竟至右倾了。
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以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注:《左联回忆录》(上),1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而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瞿秋白“重返文坛”。
1931年1月7日,米夫、王明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错误,解除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4月, 茅盾访问了“赋闲”在家的秋白。5月, 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在茅盾家中见到瞿秋白。瞿与茅、冯的见面,意味着他的重返文坛并开始介入了左联的领导。
瞿秋白“花了许多心血”(茅盾语)参加起草的11月决议,是他回归文坛后的第一个重要行动。这个决议之所以被认为是左联“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是由于它体现了反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精神。
首先,11月决议消解了此前左联文件中极左色彩浓重的话语。8 月决议认为:“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 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为完成苏维埃文学运动的伟大斗争任务每个‘左联’的同盟员应该坚决的执行自我批判,和克服逡巡的动摇的倾向,特别是和右倾的倾向作斗争。
”(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 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 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而11月决议则首次出现了反对左倾空谈的提法。决议在分析左联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任务中显得落后的原因时说:“所以然之故即在过去的屡屡陷于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空谈的错误!
”(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虽然在反左倾空谈前仍提反右倾,但在当时左倾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能提及左倾已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与以前左联文件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相比,这个转变可谓是带有根本性的了。
其次,11月决议虽然继续强调左联是政治观点一致的团体,但已开始注意到“在文学领域”内。在决议的第三部份“新的任务”中,前三项都是政治性的,即反帝、反国民党和为苏维埃政权斗争,但在每项任务前,都加上一句限制词:“在文学的领域内”。
(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 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这些提法都与此前文件中“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这类的说法大相径庭。(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第三,11月决议第五部份专门谈了创作问题(包括题材、方法与形式),这在左联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其中除重复了8 月决议中对“作品万能主义”的批评外,还指出“忽视作品”的另一种错误。承认“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在题材上除强调写重大政治斗争题材外,也终于提到要描写“民众生活”,“贫民生活”等等。(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在创作方法上,除指出“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外,还说要“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同时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
(特别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第四,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11月决议则指出除了要和种种欺骗与麻醉民众的“旧大众文艺斗争”外,还要“去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这就等于承认“大众”还是需要启蒙的。
同时又指出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和过去主观论左倾小儿病及观念论机会主义的理论及批评斗争。”(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 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第五,更难能可贵的是,11月决议正面提出要团结和争取更多倾向革命的作家的问题:“不用说,对于进步的作家,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广大的革命化或开始革命化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当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
”(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 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而此前,在8月决议中是要求革命作家“清算文坛的封建关系,手工业式的小团体的组织以至它的意识。”(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 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 110页、111页、 111 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从上述这几点的摘引与对照中,就可以看出11月决议确是“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使左联由此开始摆脱困境走出低谷,逐步进入上升通道,直至蓬勃发展取得反“文化围剿”的很大胜利。左联盟员后来又发展到约400人;左联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除上海外,北平、 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及东京也先后建立了左联组织,左联影响所及还成立了社联,剧联、美联、教联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左联报刊亦多达50种以上,如《萌芽月刊》、《拓荒者》等等。
(注:见《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
在左联的这些胜利中,秋白不仅亲自在理论、翻译、创作上写出了大量重要的作品,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也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是他建议办一个以发表创作为主,并要有非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即《北斗》,是他建议占领《申报·自由谈》这块阵地,是他支持夏衍向电影界进军,支持田汉介入唱片公司等等。
而最重要的是,他参与了11月决议的起草,这一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是使左联转向的关键之举。虽然我们无从知道11月决议中哪些提法是出自秋白的,但我们可以从他在11月决议前写的两篇文章中,看出瞿秋白的思路是与11月决议精神相吻合的。
1931年5—7月(即11月决议前半年左右),瞿秋白写了五篇论文,其中《学阀万岁!》一文中,把新文学的阵营分为五个派别,第一是地方、买办资产阶级文学,如“民族主义文学”;第二是资产阶级文学,如新月派;第三是小资产阶级文学;第四是来自部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第五是无产阶级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小资产阶级文学一分为二,而对第三种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他并不如8 月决议那样要“反对”,而是要提高它的思想水平,改造它的语言,使其表现群众,服务于群众。(注:王铁仙:《瞿秋白文学评传》,145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与11月决议的团结争取倾向革命的作家的精神就相吻合了。
1931年10月,瞿秋白又写了一篇《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中他提倡三种创作题材:为紧张斗争所急需的“鼓动作品”,反映“一般的阶级斗争”的作品和“为着理解阶级制度之下的人生而写的作品”,并认为这第三类作品最应重视,他还说这类题材可以是“民众的私人生活的故事,宗法社会的牺牲,成家立业的破产”(注:王铁仙:《瞿秋白文学评传》,15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等等。 这里对题材选择的宽泛度与多样化,比11月决议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了。(11月决议是提描写“民众生活”)
在创作方法上,《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比之11月决议不仅观点一致,而且阐述得更生动更详尽。他首先明确提出:“普洛大众文艺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虽然他没有正面给“普洛现实主义”下定义,但却对左翼作家在创作中“革命浪漫谛克”的种种表现作了尖锐的批评(这其实也是从反面来论证普洛现实主义的涵意):(一)感情主义。
“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地位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于工人、农民,这也会冒充革命文学。
这种创作里的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普洛文学所不需要的。”(二)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个人忽然像‘飞将军从天而下’,落到苦恼的人间,于是乎演说,于是乎开会,于是乎革命,于是乎成功……”(三)团圆主义。“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有困难一定解决,有错误一定改正,一些百分之百的‘好人’打倒了一些百分之百的‘坏人’。
”(四)脸谱主义。“反革命的一定是只野兽,……而革命的一定是圣贤,……生活不这么简单!
工人,劳动群众所碰见的敌人,友人,同盟者,动摇的‘学生先生’,也不是这样纸剪成的死花样,而是活人。工人农民自己也是活人!反革命的人,一样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注: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30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年。)这种对生活简单化,创作公式化的批评,批得多么酣畅淋漓。
上面列举的写于11月决议前的两篇文章,足可证明11月决议反“左”倾的精神与瞿秋白的思路是吻合的,或者说,瞿秋白把自己对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融铸到11月决议中去了。
瞿秋白何以从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在短短的二、三年后忽然会变成反“左”的呢?
首先涉及的是如何评价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瞿秋白的责任。
与秋白同时为中央常委的李维汉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对此有过论述:“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11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
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28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
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注:丁景唐、丁言模:《瞿秋白印象》,259页,学林出版社,1997 年。
)由于实行全国总暴动的错误策略,导致广州起义失败,许多同志牺牲,这一血的教训以及共产国际九次扩大会议作出批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使秋白对此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有了认识。
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一致拥护国际的决定, 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历时六个月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宣布结束。两个月后,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瞿秋白在作政治报告中,对左倾盲动主义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代表们批评自己。
在会议结束时,瞿秋白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结论时,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
至于后面两次左倾路线,即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则秋白不仅亲眼看到它们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害,而且自己就是受害者,尤其是王明路线对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使他对左倾错误路线有了切肤之痛。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之所以能形成及推行,自然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而成,但就个人主观因素来说无非是两种,一是认识问题,另一就是人品问题了。就此而言,瞿秋白诚如与其相知多年的茅盾所说:始终“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注:丁景唐、丁言模:《瞿秋白印象》,138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谈到秋白的《多余的话》时这样说:“在他就义的前夕,在死囚牢里像解剖自己患肺病的驱壳一样,他已经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注:丁景唐、丁言模:《瞿秋白印象》,157页, 学林出版社,1997年。)
我们再读读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是如何解剖自己的心理和性格的: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
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注: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5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这样的性格、气质未必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但绝对是当不了“左”先锋的。
第三,1931年4月他回到文坛时,第一个接触的是茅盾, 而后是冯雪峰、鲁迅。他和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和谐的合作关系,营造了一个反“左”的小气候(在王明路线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并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左联的领导核心层。
瞿秋白与鲁迅,思想是如此易于沟通,文风也是如此易于互相理解,以至于秋白写的杂文,用鲁迅笔名发表、竟使人鲁、瞿莫辨。“这是这样一种友谊:双方都了解对方的价值和在革命中的贡献和作用,双方都了解对方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忠诚。
也就因为这样,双方都要保护对方免遭敌人的杀害和自己人的攻击,双方都能肝胆相照,患难与共。”深刻的理解,坦诚的相交,这样的友谊只有建立在理念的一致、性格的相近的基础上,才会生长发展,才会相互扶持并肩战斗。事实证明,以秋白、鲁迅为核心的左联领导层,在左联转向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第四,促使瞿秋白转向反“左”,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拉普”的变化——也反起“左”来了。秋白一生与苏联密不可分,有一句话,叫“成也苏联败也苏联”,当初培养秋白成了中共领袖的是苏联,最后把秋白打下去的也是苏联(王明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从秋白的角度来说,苏联是他走上革命的引路人,是他探索中国革命前途的“明灯”,是他从事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唯一楷模,他尊重苏联,学习苏联以至听命苏联,顺从苏联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到后来他被王明玩弄于股掌之时,他对苏共那一套权术已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不过,1931—33年,秋白在左联所推行的反“左”路线,确也受到苏联“拉普”的影响,历史有时也真是巧得很,因为“拉普”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转向”了。
1931年12月6日,秋白写了《斯大林与文学》一文, 转述了“拉普”1931年8月在自己的机关报《文学报》上发表的社论, 社论是对斯大林6月28日的演说:《论经济建设的新任务》的回应。 秋白所介绍的这篇社论与左联11月决议相一致之处有下述几点:
一、左联11月决议提出要“无容情地对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空谈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与社论中所说,要开始一个新的自我批评运动,集中火力打击右倾的危险,同时也要加紧反对左倾的空谈相一致的。
二、11月决议中确认左联是作家组织,强调作家的本位是文学,批评了“忽视作品”的错误等等,是与“拉普”在1925年转向后,把“学习、创作和自我批评”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基本口号是一致的,也与社论下述提法相一致:根据斯大林演说中提出的“面对技术”,“拉普”“应当更加注意那种忽视文艺组织的特殊任务的倾向,纠正那种抄袭非文艺组织的工作方法,要更加注意自己工作的特殊形式和方法。
普联要加紧注意自己的技术——文字学,言语学,以及艺术方面的一切切实的技术。”(重点号为作者瞿秋白所加)
三、如前述,“拉普”在调整方向后,提出“活人论”与“撕下一切假面具”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等创作的重要口号。简单说,“活人论”就是要具体描写人的复杂个性,要写出有血有肉的“活人”来,反对概念化与简单化;“撕下一切假面具”就是要继承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真实地反映现实,反对“粉饰”与“吹嘘”,如此就要有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去观察、分析事物。
在讨论中,也再次提到创作“要表现活的人物,具体的社会个性。
”“必须真正能够用辨证法去观察现实,观察一切运动之中的生长之中的现象。”“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等等。这些在左联11月决议第五部份创作问题的第二点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
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作家“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同时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
(特别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秋白在1931年10月写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对“革命浪漫谛克”四种表现的批评,特别是“团圆主义”、“脸谱主义”,与“活人论”、“撕下一切假面具”的观点,有着更为贴切紧密的关联。
四、11月决议提出团结和争取进步作家,无疑是反“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与“拉普”的转向有密切关系。在写完《斯大林与文学》一个多月后,1932年1月16日, 秋白又写了《苏联文学的新阶段》一文,也是以转述的笔法介绍了“拉普”在1931年9 月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内容。
该次会议作出了三点决议,其中第一点是“同路人和同盟军”,根据斯大林关于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说法,“拉普”承认同路人中的一部份正在转变为文学同盟军,因此对他们既要批评斗争,又要团结教育,这比起过去完全排斥同路人的作法,是个很大的转变。
这与左联前期拒斥进步作家的关门主义,与后期扩大阵线,与各种非左翼作家广泛合作的策略转变,“拉普”也是起了“榜样”作用的。(注: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25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综上所述,瞿秋白在左联时期,积极推行反“左”的文学路线,缘于一,本人的阅历与政治经验,使他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和切肤之痛;二,他那坦荡无私,宽厚温良的品性也使他与偏爱极端,嗜好偏激的极左思想行为难以相容;三,他与以鲁迅为首的左联领导层,有着融洽的合作关系,特别在反“左”上有着共同的认识与一致的步调;四,以“拉普”为核心的第三国际,正处在由“左”向反“左”的转变中,这就为瞿秋白的反“左”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及政策策略的实践经验。
作者介绍:张小红 上海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